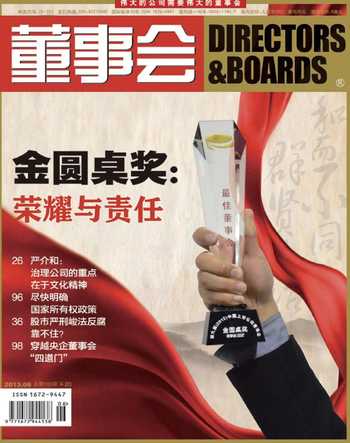“新中間路線”
彭文生
在西方,“新中間路線”是一種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的政治經濟理念的概稱,中心思維是不走左和右兩個極端,既不主張純粹的自由市場,亦不主張過度的福利社會。但這個詞的引用并沒有嚴格的標準和共識,很多人認為北歐的經濟模式是新中間路線的典型,也有人把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維護自由市場價值和保守的財政政策,甚至中國的改革開放、脫離計劃經濟模式歸結為中間路線。
我們用“新中間路線”這個詞,主要是想描述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政策如何在不同的目標或利益格局下有所取舍、取得平衡,從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樣的政策框架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但也不是中庸之道,需要結合短期和長期、局部和整體的利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需要在一系列領域進行深度的改革和政策調整。要突破經濟發展的制度約束,防止經濟增長大幅下滑,改善經濟結構,控制和管理金融風險,需要結構改革和公共政策在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上一代與下一代、金融與實體、供給與需求等方面取得平衡。我們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公平與效率:經濟社會環境和改革開放早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應該把降低貧富差距放在相對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既能增加效率又能促進公平的改革措施,包括降低行業壟斷、增加競爭以改善要素分配,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財稅制度以調節稟賦差異。
政府與市場:糾正公共部門的“越位”和“缺位”,政府主體應該退出競爭性經濟活動,加快要素價格改革,放松管制以及推動利率市場化,但在市場失效的領域應加大公共產品的提供,并營造促進公平競爭的法規環境。在糾正市場失效方面,環境保護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必須切實加大政策干預力度。經濟增長和空氣質量并非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程度,空氣質量等環境指標會持續改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這一方面反映了經濟結構的改善,服務業占比上升而工業占比下降,另一方面的關鍵是政府的介入。
上一代與下一代:人口的不均衡發展帶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經濟影響,這種影響的上半場是紅利,是經濟繁榮的兩大重要因素之一(另一個是經濟體制改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少兒比重下降的同時,我國社會老齡化進程加速。老齡化意味著未來年青一代的撫養負擔將增加,從長遠來看,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促進人口的均衡發展,應盡快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促進生育率提高;在改善同一代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的同時,公共政策還應關注代際的收入轉移問題,包括退休安排機制。
金融與實體:在進一步市場化、促進融資效率的同時,控制房地產泡沫、管理信用(銀行與非銀行)擴張帶來的風險應是平衡實體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著力點。在我國當前的形勢下,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是當務之急。這一方面需要提高影子銀行尤其是金融機構中介的理財產品的透明度,讓監管部門及時全面地把握相關風險敞口的總量和分布,另一方面,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比如一定的比例要求,來控制總量的增長。
需求與供給:以總需求管理為導向的宏觀經濟政策應顧及中長期對供給面的影響,改進財政政策逆周期操作的方式與載體;貨幣政策在平衡增長和通脹目標時,需要關注實體經濟周期和貨幣信用周期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