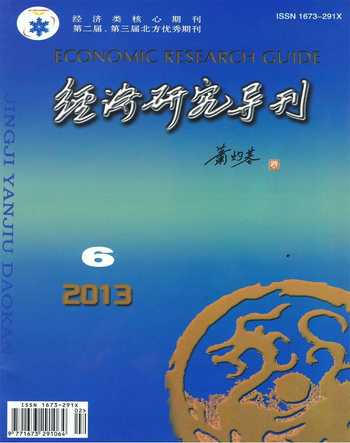數理方法在經濟增長模型中的應用
王貴松 趙麗虹
摘 要:數理方法與經濟研究和計劃工作的關系密不可分,用數理方法對經濟學研究的滲入為切入點,深入分析數理方法在經濟增長模型中的具體應用,最后得出結論:經濟學的全面發展離不開數理方法。
關鍵詞:數理方法;經濟增長模型;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6-0001-02
一、數理方法的滲入
經濟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如果從16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重金主義之間的爭論作為研究經濟現象的開始,經濟學的歷史至今還不到四百年;亞當·斯密的巨著《國富論》,為經濟學的系統研究奠定了基礎,至今也只有兩百多年。任何一門科學都要用到抽象和邏輯的思維方法,但經濟學應用抽象和邏輯的思維方法卻比一般的自然科學格外困難。在20世紀以前,經濟學雖然普遍地使用歸納、比較和分析的方法,但基本上沒有脫離以對歷史現象的陳述和對規律的推測為主的論述方法。直到大約一百年以前,由于自然科學思維方法的巨大成就的影響,經濟學方法開始轉變了。19世紀70年代初期,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和瑞士的瓦爾拉獨立地將微分方法導入經濟學,引起了經濟學方法的邊際革命。最近的一百年來,數學和推理的方法不斷滲入經濟學,形成了研究經濟學的數理方法。
20世紀末以來,在經濟學方面有重大貢獻的大師,幾乎都在數學上有很高的造詣。微觀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馬歇爾畢業于劍橋大學數學系。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奠基人凱恩斯同時又是一位數學家。獲得首屆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庫普曼、康托洛維奇、德布勒等他們本身就是教學家。至1969年頒發的第二十三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中有2/3以上的成果屬于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從這一數字比例足見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說明現代經濟學同數學的聯系已經更加緊密。
二、數理方法在經濟增長模型具體應用
自從哈羅德和多馬在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分別提出各自的經濟增長模型,并最終形成開創性的哈羅德—多馬模型以來,經濟增長理論逐漸被正式納入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并且與經濟中期理論一起成為宏觀經濟學中兩個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中,以三個涵義各不相同的方程分別界定了實際增長率(G)、有保證增長率(Gw)和自然增長率(Gn)三個既有聯系又相區別的概念,從而論述了實現穩定狀態均衡增長和充分就業穩定狀態均衡增長所需具備的條件,以及加速數與乘數相互作用引起的經濟周期繁榮階段的積累性擴張和衰退階段的累積性緊縮。而多馬的增長模型(=σS)則指出,要使社會的資本存量保持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投資增長率()必須等于社會平均投資生產率(σ)與儲蓄傾向(S)的乘積。
從模型的特征來看,哈羅德—多馬模型繼承了凱恩斯有效需求決定均衡國民收入的理論思路,所以在通過模型考察動態均衡的增長問題時,突出強調需求一方在供求雙方相互作用趨向平衡中對供給的作用。在哈羅德—多馬模型中,雖然廣泛涉及到供求雙方在決定經濟增長中的許多主要變量(包括勞動力、資本、儲蓄、消費等),但關于勞動力增長率必須等于儲蓄率與產出資本比的乘積的強假設約束,嚴重地限制了該模型的現實解釋能力。
由于這種建立于凱恩斯消費函數和里昂惕夫生產函數基礎之上的“簡單模型”,在對經濟現實的解釋上存在嚴重的局限性,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一種更加一般化的增長模型。根據這一模型,索洛認為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調整生產中的資本—勞動組合比例,應當能夠實現充分就業的穩定經濟增長狀態。而在長期中,均衡的經濟增長率就是由勞動力增長率與技術進步決定的自然增長率(Gn)。在此后一段時間里,斯旺、米德、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也先后提出了與索洛論點基本一致的經濟增長模型,而這一系列模型又強調了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充分就業的觀點和立場,故而被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
索洛模型的進步的重要一點是他設定了一個與里昂惕夫生產函數不同的綜合生產函數,即:
Y=F(K,N),F1>0,F2>0,F11<0,F22<0
顯而易見,該生產函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資本與勞動力相互之間的可替代性,因此,勞動力資源不會被閑置,也就打破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中對均衡增長的嚴格條件約束。
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經濟的均衡增長條件被歸納為:
sf(k)=nk
由這一條件可以看出,新古典增長模型并沒有簡單的認為公眾的意愿儲蓄與廠商的意愿投資的不一致必然導致積累性緊縮和擴張。相反,在儲蓄率(s)和勞動力增長率(n)給定的條件下,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動和調整,廠商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會選擇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使得與人均資本k相應的人均產量f(k)滿足均衡增長條件。換言之,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從長期看,利率的變動將使儲蓄和投資最終趨于一致并達到充分就業。同時,根據索洛增長模型,不同的儲蓄率會有與之相應的穩定狀態的人均產出和人均資本,其中有一個由特定儲蓄率決定的穩定狀態人均資本會導致人均消費達到極大值的被稱為黃金規則的穩定狀態。
以索洛模型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較之于哈羅德—多馬模型更加貼近于現實,也更加具有解釋力和說服力。但是,索洛模型并沒有從根本上跳出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它和哈羅德—多馬模型一樣,都假設了一個外生給定的儲蓄率。雖然在后來出現的拉姆齊—卡斯—庫普曼模型中這一假設被打破,使內生的儲蓄率為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微觀基礎,然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始終沒有對金融系統在長期的經濟增長中可能發揮的作用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因為從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兩個重要觀點(即資本的邊際產出遞減和經濟增長的唯一內生驅動力是資本積累)外推,在沒有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的情況下,經濟的增長只能是暫時性的。很明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內我們只能發現一些有關金融市場的時隱時現的內容,而無法找到關于金融系統作用的完整軌跡,也就無法有效說明金融系統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當然,這一點并非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唯一缺憾,也不是最重要的缺憾。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證明了技術進步在經濟長期增長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時它卻把這一重要因素設定為外生變量,這就使得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實用價值大打折扣。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學家們開始將技術因素逐步內生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逐漸形成。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模型之一——AK模型由巴羅和里貝羅于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它的基本形式是:y=Ak。
由于這是一個極端簡化的例子,它只表述了單要素的線性生產函數(A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但同時它又打破了約束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限制條件(f′(k)=0),認為當資本存量不斷增加時,其邊際生產力并不會減少為零。因此,AK模型成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又形成了許多分支,各種建立于不同假設前提下的模型使其理論體系不斷地從各個方面得到完善,但是各有側重的各類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又都不約而同地圍繞著有關技術創新的特殊作用和用于研究開發(R&D)的資源的重要性這一中心內容而展開。總的來說,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方向是與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相一致的,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潛力。
但是從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出發,我們卻可以通過適當的演繹和合理的分析來尋找并不屬于該理論核心內容的一些潛在變量關系。以AK模型為基礎,我們研究一個沒有政府部門的封閉經濟體,在該經濟體中,資本積累的方程為:
Kt+1=It+1+(1-δ)Kt
其中,It+1為社會總投資,δ為資本折舊率。
由于已經把研究范圍限定于一個沒有政府部門的簡化的封閉經濟體,資本市場將通過儲蓄與投資在總量上的匹配來達到出清。而在現實中,儲蓄向投資的轉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規模不等的交易費用,也就是說,社會總儲蓄(S=s·Y,s為儲蓄率)并不等于總的投資額,一部分儲蓄會在向投資的轉化過程中“漏出”。所以,在這里我們假設φ為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則1-φ就是因交易費用等因素導致的儲蓄漏損率,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方程就表示為:
φSt=It
綜合以上各方程,我們不難得到經濟的穩態增長率表達式:
g=Aφs-δ
而在該表達式中的儲蓄率s又可以進一步的表示為:
s=
其中,σ表示行為人的跨期消費替代彈性,ρ表示行為人的時間偏好。很明顯,s與跨期消費替代彈性σ正相關,與時間偏好ρ負相關,而s與資本邊際生產率A和折舊率δ的關系則不那么明確,而且這一關系的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σ的取值大小。由s的表達式可以判斷,當σ>δ/(ρ+δ)時,A與s正相關,而當σ<δ/(ρ+δ)時,A與s負相關,兩項相等時A與s不相關。類似的,當σ>1時δ與s負相關,當σ<1時δ與s正相關,而σ=1時δ與s無關。
通過對基于AK模型的演繹和透析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是在側重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仍然包含著對金融因素的潛在依賴,這也就從理論的角度證明了現代經濟增長中金融系統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總結
對于數理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運用,盡管爭論很激烈,但從當前的研究發展趨勢來看,雖然數學的濫用以及數理工具理性的不斷強化,可能會成為經濟學全面發展的桎梏,但從整體來看,經濟學的數理化革命能使經濟學走向成熟和科學,數學方法本身能使經濟理論不斷豐富和深化,同時也增強了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從這種意義上說,經濟學的全面發展離不開數學。“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真正達到了完善的地步。”只有合理地利用數學工具,科學準確地把握經濟事物本質,才能為經濟理論生動直觀地或需要定量地表達提供可能的方式。
[責任編輯 劉嬌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