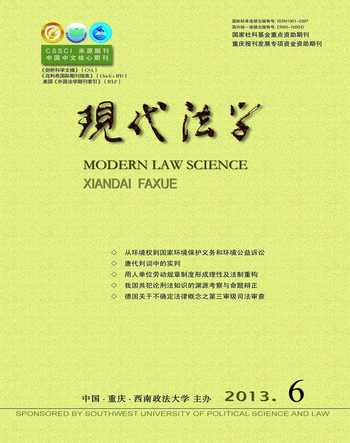德國關于不確定法律概念之第三審級司法審查
盧佩
摘 要:所有在內涵和外延處于不確定狀態的法律概念均可稱之為不確定法律概念。由于不確定法律概念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上具有模糊性的特點,因此對此類概念的法律適用將陷入“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模糊區域。在此模糊區域之中,上下審級法院之間所形成的功能分野陷入困境,下級法院對法律概念的判斷仍應享有一定的自由評價空間,第三審法院對此評價空間應予以尊重。司法判例中所形成的“概念認識錯誤-是否對所有重要性事實審查窮盡-是否違反經驗法則或具有可責問的違反程序性事項”的有限審查及其少數無限審查的例外,共同構成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審查原則。
關鍵詞:不確定法律概念;邏輯區分;司法統一
中圖分類號:DF7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6.12
一、問題的引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民事活動應該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是究竟何為“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過錯”?《民法通則》卻并未做出進一步的詳細界定,此類概念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中的運用可謂比比皆是。由于在立法上并未對其內容和外延予以詳細規定,同時在法學理論界也并未對之積累足夠的經驗,并進而形成法學通說關于德國法學語境下的通說一般理論,可參見:莊加園.教義學視角下私法領域的德國通說[J].北大法律評論,2011,12(2):319-333. ,由此導致法官對于此類概念的審查困難重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等形色各異判決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幾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瀘州遺贈案”便是其典型代表。
在這場圍繞遺囑有效性而展開的大討論中,無論是立于“婚姻道德與財產權利兩種價值觀的沖突”所引發的對不同社會價值和社會訴求的權衡取舍[1],或是立足于現行法律規范體系,以法教義學為分析工具去尋找遺囑成立的規則適用問題[2],都必須依靠《民法通則》第7條中所適用的“社會公德”這一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分析媒介。在法條文意模糊不清的前提之下法官面臨著不同倫理價值的選擇困境,無論其最終的結果選擇何種價值作為其論證的正當性基礎,不確定法律概念終究不能為不同價值觀的論戰提供法律平臺。而在依靠抽象法律概念、原則與制度所架構起來的現行法律規范體系中,只有通過不確定法律概念這一法律技術的引入,緩解抽象規范的普遍適用效果與個案具體差異之間的緊張關系,才能維持法律系統內部的自洽。但遺憾的是,無論是在我國的司法審級制度中,還是在學術討論中,對于一個如此重要的法律分析媒介卻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并相應在審判活動中形成一套專門的審查機制。正如“瀘州遺贈案”,在看似熱鬧非凡的學術大討論過后,“社會公德”這一不確定法律概念依然含混不清,無法對未來的司法審判活動增加司法資源供給。
很顯然在司法實踐中產生此類分歧的并不僅限于“重大過失”和“善良風俗”這兩個概念,“瑕疵”、“誠實信用”、“輕微地妨害”、“善意”等法律概念在司法的適用過程中面臨著同樣的困境,而這類法律概念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不確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e)。如何彌補立法空白,促進法律的正確適用與統一司法,一直是我國司法改革中亟待解決的難題。最高法院作為司法金字塔系統的頂端應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所產生的形式合理性放任各不同判決的存在,還是為此設定統一的審查標準作為保障司法統一的最后一道防線?盡管中國和德國處于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及其法律規范體系下,所面臨的困境及其分析的重點會有所差異,但在兩條路徑的選擇方法上終究是有章可循的。本文通過介紹德國第三審法院對于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審查機制在對相關主題進行深入探討之前,對德國普通法院之四級三審制的法院結構進行簡要介紹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德國法院系統,可分為聯邦法院系統和各州法院系統兩個層次。聯邦法院系統包括聯邦憲法法院、五個最高法院(即聯邦最高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財稅法院、聯邦勞動法院以及聯邦社會法院)、聯邦紀律法院以及聯邦專利法院。除此之外其他所有法院都屬于各州。就其法院主管事項而言,德國法院系統可分為憲法法院、普通法院、專門法院以及其他特殊法院。本文所涉及主題則是立足于普通法院系統內的探討。普通法院分為四級,包括初級法院、州法院、州高等法院以及聯邦最高法院。第一審級法院包括初級法院和州法院兩級,第二審級法院分別為原第一審法院的上一級法院,而第三審級法院則集中于聯邦最高法院。 ,試圖從中總結出一些共通性的規律,如果能夠為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提供有益的啟示與借鑒,那么本文的寫作目的就已達到。
[HS(3] [HTH]二、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發展歷史與界定
[HTSS][HS)]
“不確定法律概念”開始走入國內學術研究的視野,也只不過區區幾年的時間。在為數不多的學術成果中,幾乎所有的學者將其研究的重點都置于行政法領域中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從“依法行政”的角度切入,關注司法機關對“行政主體在將不確定法律概念具體化的過程中所做出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正當性審查。華中科技大學尹建國老師在此領域的研究尤為突出。近年來尹老師以行政法領域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研究主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詳情請參見:尹建國. 行政法中的不確定法律概念釋義[J]. 法學論壇,2009,(1):59-65; 尹建國.不確定法律概念具體化的說明理由[J]. 中外法學,2010,(5):754-769;尹建國.不確定法律概念具體化的模式構建[J]. 法學評論,2010,(5):60-69;等。其他的學者相關主題的論文有:余凌云. 對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予以確定化之途徑[J].法商研究,2009,(2):60-66;王青斌. 論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處罰法定原則的沖突和協調[J]. 法學評論,2011,(1):26-31. 事實上,不僅限于行政法領域,在民法領域也存在著諸如“重大過失”、“善良風俗”等不確定法律概念,盡管不涉及在“行政權與司法權邊界劃分背景下”法官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卻同樣面臨著在“上下審級權限劃分背景下”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自由裁量行為的司法審查問題。很遺憾,筆者并未發現以此為對象的學術研究。相比國內學術界的零星研究狀況,德國針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研究不僅歷史悠久,且范圍涉及概念內涵確定、發展沿革、邊界確定、司法審查等諸多領域,相信筆者所作出的這一針對德國研究脈絡的縱向梳理,對于下一階段司法審查原則的討論有啟示意義。
“不確定法律概念”一詞首先來源于行政法領域,在二戰以前與行政“裁量”(Ermessen)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區分。隨著19世紀歐洲大陸法治國家理念的轉變及三權分立理論的風靡,早期行政裁量學說的研究重點在于劃分行政權與司法權在行政裁量事項上的邊界問題[3],并由此衍生出“行政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兩者的分離。“行政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兩者的分離過程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變遷。最初,邁耶教授(Mayer)在其專著《行政法的原則》中將行政事項劃分為純行政事項和行政爭議事項(streitige und reine Verwaltungssachen)。前者包括行政業務手續的辦理、許可權的授予、行政機關對國家財產的管理、法規制定權的行使等等。在此事項上由行政機關完全依據自身行政權進行自由裁量,相對方不能對此裁量結果提出法律上的抗告。其余則納入行政爭議事項的范疇,一般是指法律適用問題(既包括條文明確的法律條款適用如稅法,也包括一般彈性條款的法律適用),因此屬于羈束性行政,即行政機關裁量權的行使受到一定范圍的限制。邁耶教授關于純行政事項與行政爭議事項的劃分為以后“自由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兩者的分離奠定了理論基礎。(參見:Friedrich F. Mayer, Grundstze des Verwaltungsrechts, Tübingen 1862, S. 453 ff. )隨后特茨納教授(Tezner)關于行政裁量的理論進一步推動兩者的分離。他認為行政裁量是法律賦予行政機關在面對各種不同執行的可能性時自由選擇的權限,這種裁量權限由法律直接授予,且僅由該行政機關自行對其選擇的正確性承擔責任。因此除非存在濫用裁量權限的行為,導致裁量決定明顯錯誤,否則法院不應介入對其進行司法審查。相反他認為,不僅限于不確定法律概念,所有規定行政機關與個體權利義務之間關系的概念,無論其概念內容確定與否,都應受到行政法院的審查。(參見:Horst Ehmke. Ermessen und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 im Verwaltungsrecht[M]. Tübingen 1960, S. 11-18. Stickelbrock, a.a.O. , S. 41-45; Friedrich Tezner, Zur Lehre von dem freien Ermessen der Verwaltungsbehrden als Grund der Unzustndigkeit der Verwaltungsgerichte[M]. Wien 1888, S.13 ff. ders.; Das freie Ermessen der Verwaltungsbehrden[M]. Leipzig, Wien 1924, S. 69 ff.) “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的分離直接關系到行政權與司法權邊界的確定,在“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授權許可的范圍及其司法權對行政權行使的監督界限”這一框架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德國
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及其絕大多數行政法文獻資料認為,行政裁量的前提在于,法律并未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所應采取的具體行政措施,而只是賦予行政機關一種選擇權,且其所選擇的任何行為皆為合法且正確。換言之,如果可供選擇的數項行為中,其中僅有一項為正確行為,其他皆為錯誤的情況下,則并無選擇可言,也就沒有行政機關對其進行裁量的可能性。詳情請參見:Stickelbrock, a.a.O. , S. 105在此學說的基礎之上,聯邦最高行政法院將行政裁量界定為法律效果上的裁量。因為法律要件為法律構成事實,而絕對事實的存在,只有一個唯一的正確答案,因此無法成為裁量的標的,如太陽從東方或西方升起,狗是黑色或白色等等都不能任人裁量。至此行政裁量逐漸在法律要件與法律效果上區分開來,并成為不確定性概念與行政裁量的分界標記,即行政裁量的范圍僅限于法律效果的裁量,而法律要件的裁量則納入“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討論范疇。(參見:翁岳生. 論“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之關系[G] // 翁岳生. 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 臺北:祥新印刷有限公司,1990:27.) 因此“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兩者的界分一直是近百年來行政法領域的熱點問題。具體可以參考如下文獻:Dietrich Jesch,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 und Ermessen in rechtstheoretischer und verfassungsrechtlicher Sicht, AR 82 (1957), S. 163; Hermann Reuss, Der 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 seine Bedeutung und seine Problematik, 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 1953, S. 649-655; Otto Bachof, Beurteilungsspielraum, Ermessen und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 im Verwaltungsrecht, Juristenzeitung 1955, S. 97; Andreas Sethy, Ermessen und unbestimmte Gesetzesbegriffe, Wien 1973; Hans-Joachim Koch, 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e und Ermessensermchtigungen im Verwaltungsrecht, Frankfurt am Main 1979; Francesco D. A. Bertossa, Der Beurteilungsspielraum zur richterlichen Kontrolle von Ermessen und unbestimmten Gesetzesbegriffen im Verwaltungsrecht, Bern 1984; Johann Bader/ Michael Ronellenfitsch, Kommentar zur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15. Aufl. , München 2012, §40.
“司法裁量”這個概念經由行政法中的“行政裁量”而逐漸引入至訴訟法領域。盡管前面所探討的“法院對行政裁量行為的司法監督”的建構原理是否可以依次類推至“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司法裁量行為的監督”仍有待商榷,但司法裁量的理論學說卻與行政裁量有著相似的發展路徑。早期的司法裁量理論主要根據以下兩種標準對“司法裁量”進行類型化區分。如根據法律適用的角度可以將其劃分為“法律構成要件的裁量”和“法律后果的裁量”。該區分標準最先由斯菲爾特教授(Seuffert)提出。前者主要體現在法官對于某些具有多重含義或者含有價值判斷的概念的裁量上具有裁量權(如公序良俗、誠實信用),賦予法官此類司法裁量權,有助于將法律規范從“概念確定化”的負擔中解脫出來,同時使法律規范更具靈活性,隨著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與時俱進地實現其規范功能,防止法律漏洞的產生;后者則主要反映在法官在刑法的量刑以及民法損害賠償額的確定上具有裁量權。(參見:Lothar Seuffert, ber richterliches Ermessen, Gieβen 1880, S. 114.) 隨著司法裁量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其研究重點由之前的類型化討論逐步轉到對其本質的探討上,即法官在將具體案情歸入抽象法律規范的涵攝過程中所進行的判斷,是否具有司法裁量的性質。換言之,“不確定法律概念”的適用是否具有司法裁量的性質。一部分學者認為,法官在對法律構成要件進行判斷時擁有裁量權限,但他在此過程中卻并沒有選擇的可能性。盡管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內容具有多義性和模糊性特點,但法官借助于案件特殊情況及法律精神將其具體化后的內容卻具有唯一性特點,即只有唯一一個正確的涵攝結論,法官并無其他選擇的可能性。(參見:Seuffert, a.a.O. , S. 4 ff; Erich Schwinge, Grundlagen des Revisionsrechts, 2. Aufl. , Bonn 1960, S. 114 ff; Fritz Rittner, Ermessensfreiheit und Billigkeitsspielraum des Zivilrichters im deutschen Recht, in: Arbeiten zur Rechtsvergleichung, Band 24,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1964, S. 21 ff; Peter Sdorra, Ermessen oder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 im Vormundschaftsrecht, Diss. Münster 1991, S. 21 ff.)另一部分學者卻認為,正是因為法官在此過程中并無選擇的可能性,因此法官對法律構成要件的判斷并無裁量權限,即司法裁量的范圍僅限于法律效果的裁量,與行政法領域的結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如今該學說成為民事法領域的主流學說。從上述兩派觀點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出,雙方對于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過程的性質認定并無差異,即立法機關賦予法官自主確定不確定法律概念內涵的權限。但分歧點主要在于,這種權限是否屬于裁量,即司法裁量的本質究竟是法官在可供選擇的數項行為中進行選擇的可能性,還是法官在做出裁判前所擁有的主觀評價的可能性。
(參見:Stickelbrock, a.a.O. , S.248; Tilman Schmidt-Lorenz, Richterliches Ermessen im Zivilporzeβ, Diss. Freiburg 1983, S.42 ff.; Klaus Schiffczyk, Das freie Ermessen des Richters im Zivilprozeβrecht, Diss. Erlangen/Nürnberg 1979, S.29 ff; Helmut Schuhmann, Das Ermessen des Richters im Bereich der Freiwilligen Gerichtsbarkeit, Diss. Tübingen 1968, S. 64 ff. ) 筆者認為,在民事訴訟領域中,司法裁量的本質在于法官在立法授權范圍內的數項合法行為進行選擇的可能性,而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設立,在本質上是立法機關賦予法官將個人主觀評價進行合法化的途徑,德國大部分學者將這種“有別于裁量的自主判斷權限”稱之為“評價空間”(Beurteilungsspielraum)[4]。
通過上述行政法領域與民事法領域中針對“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兩者相互關系的理論發展脈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本質屬性及其在不同領域的發展趨勢。行政法領域探討將其從“裁量”概念中分離出來,其發展趨勢是在限制行政權的背景下不斷擴張法院對其進行審查的范圍。而在民事法領域的探討卻與之相反,發展趨勢是在尊重法官自由評價權限的背景下不斷縮小上級法院對其進行審查的范圍[5]。在理清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裁量之間的關系后,接下來要解決的是如何對其進行定義的問題。
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學者根據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確定程度將法律概念劃分為“確定法律概念”和“不確定法律概念”。前者一般是關于時間和金錢等的能被計算的數字概念,如3個小時、100歐等,后者如善良風俗、危險、黑夜等。單從“不確定法律概念”這個術語的文字表現形式來看,主要由一個名詞“概念”附加兩個定語(“不確定”和“法律”)構成。“概念”具有概念內涵和概念外延兩個基本特征,概念內涵反映所有包含在該概念中的對象的特有屬性,而概念外延則指該概念所反映的對象的范圍。因此明確任何一個概念的邏輯方法在于明確該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對“概念”這一名詞進行的第一個限定性定語為“法律”,目前針對“法律”性質的探討已有諸多論述,但這里分析的側重點在于從適用法律規范的角度探討法律概念的范圍,而無意從法理的角度分析“法律”這個詞源本身所具有的本質屬性。因此為使本論題更加集中且更富有針對性,筆者將“法律概念”界定為所有在現行法律規范的文本中所使用的概念,因為其中的任何概念都可能成為法律適用的對象。也正是基于此,部分學者主張應使用“不確定法律規范概念”(unbestimmter Gesetzesbegriff)這個詞來替代“不確定法律概念”。具體論述請參見:Bachof, a.a.O. , S. 97 ff.; Sethy. Andreas: Ermessen und unbestimmte Gesetzesbegriffe[M]. Wien 1973, S. 18-19; 但也有學者對此持反對意見,參見:Jesch, a.a.O, S. 166 ff.; Lukowsky. Der 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 im Denken des Logikers, des Juristen und des Artzes[M]. Verwaltungsarchiv 1962, S. 31.
第二個限定性定語為“不確定”,顧名思義,即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均屬于不確定狀態。對于這種不確定狀態的描述,學界主要有以下二種解釋學說:其一,赫克教授(Heck)進一步在不確定法律概念中區分出“概念內核”和“概念暈圈”,確定無疑的部分置于前者,而只要判斷出現疑惑的地方,便是“概念暈圈”的起點。如“中午12點”明顯屬于“白天”,但“曙暮時分”是否也屬于“白天”則值得懷疑,便納入“概念暈圈”的范疇。詳情請參見:Philipp Heck. Begriffsbild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M]. Tübingen 1932, S. 52; ders., Gesetzesausleg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AcP 112 (1914), S. 173.其二,耶林納克教授(Jellinek)則認為,一般“確定法律概念”只具有一條明晰的分界線,即能夠確定的判斷出一對象是否屬于該概念,如“成年”,只要滿18周歲即為達到成年年齡;而“不確定法律概念”則具有兩條分界線,即在“屬于”與“不屬于”之間存在一個中間地帶,如“白天”可劃分出3個區域:“確定屬于區”(如中午12點)、“確定不屬于區”(如午夜12點)以及“中間區”(如曙暮時分),“成年”則只能劃分出2個區域“確定屬于區”(如20歲)以及“確定不屬于區”(如13歲)。(參見:Walter Jellinek, Gesetz. Gesetzesanwendung und Zweckm igkeitserwgung[M]. Tübingen 1913, S. 37 ff.) 無論是赫克教授的“概念內核-概念暈圈”理論,或是耶林納克教授的“3區域理論”,都是對于“概念外延”這一不確定現象的具體描述,但其產生根源還是基于該概念在內涵上的不確定狀態。語言表達本身在對社會日常生活的描述上就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再加上通過“立法”這種以最大程度運用表達一般化類別的語詞的方式,以及“司法判例”這種以最小程度運用表達一般化類別的語詞的方式[6],法律概念本身的不確定性無疑會進一步加劇。
綜上所述,“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定義為:在所有現行法律規范的文本中所使用的,其內涵和外延均處于不確定狀態的概念。按照此類標準進行劃分,我們可以看出,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中包含著大量的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確定法律概念所占比例非常少。但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即便是屬于同一不確定法律概念集合內的概念,根據其內容的模糊程度不同,在法律適用的邏輯結構、第三審法院的審查范圍等方面也會呈現較大的差異。如果不加分析簡單套用同一抽象性審查標準,則完全無益于問題的分析解決。
三、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審查
法律的適用過程通常被認為是將邏輯三段論的演繹推理方式在司法過程中的一種應用,亦即“法律之一般的規定是大前提,將具體的生活事實通過涵攝過程,歸屬于法律構成要件底下,形成小前提,然后通過三段論法的推論導出規范系爭法律事實的法律效果”[7]。上述法律推理的過程根據審級建構的原理即越靠近塔頂的程序在制定政策和服務于公共目的方面的功能越強,越靠近塔基的程序在直接解決糾紛和服務于私人目的方面的功能越強。(參見:傅郁林.審級制度的建構原理——從民事程序視角分析[J]. 中國社會科學,2002,(4):87.) 會產生功能上的分野,即“小前提”之中采用日常用語對案件事實進行描述及確認的過程屬于“事實問題”,納入較低審級(在德國為第一審級和第二審級)的審查范圍,而“大前提”之中以抽象的法律語言表述法律構成要件與法律后果,以及“小前提”之中將具體案件所確認的事實歸入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涵攝過程,則屬于“法律問題”,納入較高審級(在德國為第三審級)的審查范圍。正是基于上述推理過程,德國幾乎所有的教科書和法律評注都將第三審程序審查范圍的判斷標準,即“可審查性問題-不可審查性問題”的區分建立于“事實問題-法律問題”的區分基礎之上,認為第三審級法院的審查范圍只能對法律問題進行審查,而所有的事實問題都應排除于審查范圍之外。具體可參考如下文獻:Hans-Joachim Musielak, Grundkurs ZPO[M]. 10 Aufl. , München 2010, S. 355; Jauernig, Hess. Zivilprozessrecht[M]. 30 Aufl. , München 2011, S. 305; Rosenberg, Schwab, 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M]. 17. Aufl. , München 2010, S. 829.
德國第三審級法院對“不確定法律概念”進行司法審查的特殊性在于,不確定法律概念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上具有模糊性的特點,因此在將具體案件所確認的事實歸入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涵攝過程中,涵攝過程的兩端都處于含糊不清晰的狀態:一邊是法律標準的含糊性導致需要對該標準進行解釋,而解釋的立足點在于案件具體事實;另一邊是案件事實的含糊性導致需要結合多項基礎事實進行概括判斷,而判斷的基點在于法律標準,兩者相互交織,形成“事實與法律問題”的模糊區域。在此模糊區域之中,前面所談及的上下審級法院之間所形成的功能分野陷入困境,除“事實描述與確認”這一本源職能之外,下級法院對法律概念的判斷仍應享有一定的自由評價空間,第三審法院對此評價空間應予以尊重。因此在民事法領域,對不確定法律概念進行司法審查的重點在于,如何實現下級法官的自由評價權限與上級法官追尋公共目的之間的平衡。
目前,任何針對不確定概念的法律適用行為絕對排除或者完全納入第三審法院的審查范圍的觀點都過于武斷,已經很少有人再持這種論調了。參見:Rosenberg, Schwab, 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M]. 17. Aufl. , München 2012, §142 Rn. 28. 普維庭教授(Hanns Prütting)是鮮有的仍然堅持持有“毫無限制審查說”的學者,參見:Wieczorek, Schütze, Prütting. Groβkommentar ZPO[M]. 3. Aufl. , Berlin 2005, §546 Rn. 15. 問題的關鍵在于,不確定概念的法律適用過程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第三審法院的審查。總體而言,學界針對此問題基本形成如下共識:第三審法院的審查范圍應局限于第二審法院是否對此概念認識錯誤參見:NJW 1953, 1139; 1990, 2889. 、是否對所有重要性事實審查窮盡參見:NJW 1993, 1066; 1994, 2093. 、是否違反經驗法則或具有可責問的違反程序性事項等等。參見:Hans-Joachim Musielak, Kommentar ZPO, 9. Aufl. , München 2012, §546 Rn. 3; Vorwerk/ Wolf, Beckscher Online-Kommentar, 4. Aufl. , München 2012, §546 Rn. 9; Z?ller Kommentar ZPO, 29. Aufl. , Kln 2012, §546 Rn. 9. 但是上述看似明確的理論審查標準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實際運行過程中卻可能陷入模棱兩可的境地。如何在紛繁復雜的事實萬象之下探求規則所蘊含的精神實質,則是問題的難點所在。本文以下部分的內容則旨在以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為出發點參見:Musielak, a. a. O. , §546 Rn. 3; Münchener Kommentar ZPO, 3. Aufl. , München 2007, §546 Rn. 13. ,逐級分析其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審查標準,并最終得出德國第三審級法院司法審查的終極目標為“司法統一”這一結論。
(一)概念認識錯誤
“概念認識”這一審查事項實際上并不屬于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審查專利,所有的法律概念內容的確認,均屬于法律適用之大前提尋找的題中應有之義,理所當然應納入第三審法院的審查范圍。特殊之處僅在于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但終究與確定法律概念一樣,也具有部分內容相對確定的“概念內核”,即對該概念的判斷形成相對固定的法律認定標準,這類標準并不因其具體案件的特殊情形而改變。如“重大過失”的概念內核為,以超乎尋常的方式違反必要注意義務的行為,而這種必要注意義務是任何人在該既定情形中本該認識到的。NJW 1994, 2093.盡管在具體案例中出現的過失是否達到“重大”的程度屬于事實問題,但如果下級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并未意識到“一般過失”與“重大過失”之間的區別參見:《德國民法典》第276條第2款規定:“疏于盡交易上必要注意的人,即為有過失地實施行為。”第277條規定:“對于只需在自己事務中承擔通常應盡之注意義務的人,并不能免除因重大過失而發生的責任。” 、對“重大過失”的適用范圍認定錯誤、或對“重大過失”的抽象性認定標準認識錯誤等等,皆屬于概念認識錯誤,應列入第三審法院的審查范圍。NJW 1953, 1139.
(二)窮盡審查各項重要性事實
縱然可以從不確定法律概念中抽象出相對確定的概念內核,但終究不是司法審判的實施細則,即便是具備如“法律行為的動機與目的”一樣的概念內涵,在不同的案件中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表現形式。下面筆者
將以《德國民法典》第906條“妨害土地使用的輕微性”這個不確定概念為例進行具體分析。《德國民法典》第906條第1款規定:土地所有人不得禁止煤氣、蒸氣、煙、煤煙子、熱、噪音、震動以及從另一塊土地發出的類似干涉的侵入,但以該干涉不妨害或僅輕微地妨害其土地的適用為限。在通常情況下,法律或法規命令確定的極限值或標準值不被依照這些規定算出和評價的干涉所超出的,即為存在輕微的妨害。依照《聯邦無形侵害防治法》(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第48條頒布并反映技術水平的一般行政法規中的數值,亦同。
第906條的立法目的在于,從消極的層面確定所有權人的容忍義務,即當相鄰所有權人在利用其所有權而對外產生影響時,如果該影響并非重大(第906條第1款)、或該利用行為為當地所通行,且不能通過合理的措施而加以阻止時(第906條第2款),則所有權人依據《德國民法典》第903條和第1004條所享有的權利應受到限制。即對待相鄰關系有兩種判斷標準:如果相鄰方并沒有實質性的侵害,則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的義務。如果相鄰方的行為造成了所有權人的實質性侵害,則應該承擔賠償責任。但如果同時符合法律規定的例外情形,則即便造成實質性侵害,所有權人依然負有容忍的義務,即該侵害行為為當地所通行,并且不能通過合理的措施加以阻止。 立法者通過這種方式劃定所有權人與相鄰所有權人權利義務范圍的合理邊界。顯然,問題的關鍵在于侵害程度的判斷標準問題。
如果侵害的程度可以通過技術性測量而得出,則對侵害重大性的判斷應該依據客觀的判斷標準,即應當遵循法律、行政法規中依據《聯邦無形侵害防止法》第48條規定而確定的極限值或標準值。如果案件中的具體侵害超出這些極限值或標準值的規定,則該侵害一般為重大的妨害。雖然這類侵害的判斷標準已經客觀化,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官在最后確定侵害的程度時必須遵循標準值,在特殊的情況下法官可以結合具體案件中各方利益的考量而對標準值有所浮動。如果侵害的程度并不存在一個可測量的客觀化標準值,則應采用“區分化的主觀性客觀判斷標準”[8]。所謂“客觀判斷標準”,是指侵害是否重大的判斷,應該以一個“來自受侵害地區的一般人”的感受為判斷標準,而并不是以受侵害的鄰居的具體感受為判斷依據。而判例中對其“一般人”的感受判斷標準,已從一個“普通一般人”的感受轉變為一個“理性一般人”的感受。參見: NJW 1993, 925. 正是通過“理性一般人”概念的引入,使得法官在對侵害重大與否問題的衡量上能夠吸收環保法的新理念以及公民環保意識的變化。而在這個“客觀判斷標準”中同時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即要結合當地的生活習慣及其被侵害的不動產的性質、用途來評價侵害程度,即綜合權衡受侵害不動產的實際效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破壞。
人們對該對象的認知往往受到具體環境和價值取向的制約,如前面已經加以具體分析的“農田的負擔程度”、“非重大性妨害”等等,而立法者不可能對所有的法律行為逐條作出界定和定性,這就需要借助于不確定概念來擴大法律涵蓋的社會層面,并不斷吸收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新內容和新價值。這種基于立法技術上的妥協所設立的不確定概念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介乎立法機關的立法活動與法官規則創制活動之間的活動區域,在這一活動區域內賦予法官根據案件具體情形自由進行利益衡量的空間。但這種活動區域并非沒有邊界,司法判例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在其抽象性概念內核項下發展出若干需要考慮的重要性影響因素,如第906條“非重大性妨害”的內核為“技術性標準值”、“理性一般人”、“當地生活習慣”及其“受侵害不動產的性質及其用途”等等。聯邦最高法院審查的對象并不在于各影響因素在具體案件中的裁判結論,而是下級法院在對具體案件
事實進行評價的過程中,是否將所有的影響因素都考慮其中,如果對相關重要性事實有所遺漏,則該裁判結論要受到第三審法院的審查。參見:NJW-RR 1993, 1421.
(三)是否違反經驗法則或其他程序性違法事項
對于含有程度性副詞(如第93條“物的重要組成部分”或第252條“以極大的可能性預測得到的利益”)、帶有強烈感情色彩(如第123條“欺詐或脅迫”)、或融入價值衡量因素(如第253條“公平金錢賠償”)的不確定法律概念該項分類受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 a. O. , §142 Rn. 27-32的啟發。 ,法官享有相對較自由的衡量空間,因此無論是概念的內涵或是重要事實因素的提取,都具有一定的難度。這種個別化的涵攝過程往往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復的特點,對此法官將其審查重點轉移至“邏輯推理過程”上來。這種審查方式在司法判例中由來已久。早在1928年的一份判決中,下級法院認為,當事人在書信中適用“粗暴殘忍”、“缺乏考慮”、“惡意”以及“仇視”等詞匯并不造成對另一方當事人名譽的侵犯。但是德累斯頓州高等法院認為下級法院作出的這個判斷屬于“可審查的破壞法律的行為”,并判定當事人的行為構成德國刑法第185條規定的“侮辱罪”。高等法院的審查并不是立足于“下級法院關于當事人使用惡意等詞語不造成對方當事人名譽侵犯”這一判斷本身,而是涉及到下級法院在作出該判斷的過程中運用推定成立的兩個“假設”,即“粗暴殘忍”、“仇視”等詞語并不涉及到對方名譽的損害,而且當事人對于這種表達會造成名譽損害的后果并不知曉。第三審法院認為,下級法院運用該假定從而得出結論的這個推理過程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即該事實結論源自于不正確的法律推理過程,因此該結論應該受到第三審法院的審查。 從嚴格意義上講,與“概念認識錯誤”一樣,本項也并不屬于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獨有審查原則。下級法院所有的法律適用過程,都應受普遍承認的經驗法則以及合理思維規則的約束,否則法官的自由心證行為將因違反《德國民訴法》第286條而受到第三審法院的審查。參見:NJW 2001, 5; 1999, 3481; 1993, 935; 1987, 1557.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列舉的第三審法院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三個審查事項,并不是不同類別上的劃分,而是一個逐級遞進、相互依存的完整審查體系。簡言之,無論是何種類型的不確定概念,法官首先考察的是下級法院對此概念的認識是否正確,其次審查在其抽象性概念內核項下是否已發展出若干需要考慮的重要性影響因素,下級法院是否將所有的因素納入考量的范疇,最后才是審查所有的邏輯論證體系是否合乎經驗法則及其思維規則,各審查事項自成體系,同時又彼此緊密聯系,環環相扣。
(四)“有限性審查”的例外
在聯邦最高法院對“重大過失”、“重要原因”等大部分不確定法律概念秉承“有限審查”之余,卻也存在少許例外,即對“善良風俗”參見: NJW 1991, 353; 1997, 192; 2003, 2825. 、“誠實信用”參見:BGHZ 45, 258, 266. 、“一般交易條款”參見:NJW 1997, 3022. 等概念,鮮有采取“第三審無限審查”立場。參見:Musielak, a. a. O. , §546 Rn. 12. 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判例立場的改變,下面將以“善良風俗”為例進行分析。
對于“善良風俗”的內涵,聯邦最高法院最初采取的表述是“所有公平公正理念的禮俗”。參見:RGZ 80, 219,221; 97, 253,255; BGHZ 10, 228,232; NJW 1991, 913,914. 但這個概念本身更多的是體現一種法律理念,并不包含有確定的可以直接適用于司法審判的評判細則。因此需要一個客觀標準或者至少要尋求這樣一個標準來判斷,什么樣的行為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理念的禮俗。由于社會生活是不斷發展的,人們的利益需求、思想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但是仍然存在著在某一時期反映整個社會不特定多數人利益的一般道德觀念。當然這里的道德觀念并不要求其符合道德高尚的價值觀,而只需要符合社會的倫理最低標準[9]。因此從司法統一的角度而言,法官必須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確定“善良風俗”的衡量標準,從而為人們未來的行為方式提供指引。毫無疑問,關于“善良風俗”內容的客觀衡量標準的確定問題屬于“法律問題”應列入第三審法院的審查范圍。為減輕其審查難度,《德國民法典》第138條中的“善良風俗”原則并不是從正面去規制法律行為必須符合某種道德倫理標準,而只是進行消極的限制,即將那些嚴重違反社會公德的法律行為設定為無效。從反面去審查“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遠遠比正面審查“符合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要容易的多[10]。
聯邦最高法院早期的判決普遍判定參見:BGH 20, 71ff.; BGH 52,17. ,立遺囑人在遺囑中將遺產指定由情人繼承的行為是無效的,因為這種“情人關系”破壞正常的婚姻關系,違反善良風俗原則,直到1970年才出現重大轉變。聯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作出的一份判決中認為參見:BGHZ 53, 369ff. 關于該經典案例的中文資料可參見:鄭永流. 道德立場與法律技術:中德情婦遺囑案的比較和評析[J]. 中國法學:2008,(4):179-189;邵建東. 德國民法總則編-典型判例17則評析[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217-239. ,立遺囑人在遺囑中將遺產指定由情人繼承的行為,并不必然因“情人關系違反善良風俗原則”而無效,因為第138條善良風俗原則設定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懲罰或制裁當事人的“不道德行為”本身,而在于“該法律行為在性質上是否違反善良風俗原則”,因此衡量的重點是當事人行為的性質在該法律行為的構成上是否起著重大的作用。如果在立遺囑人在遺囑中規定對長期的情人進行資助,其目的僅在于這種性關系的維持或鞏固上、或者是為了對情人的熱情進行獎勵而作出的,則這種遺囑是無效的。但是如果這種資助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情人的生活,并且這種資助充分考慮了自己在道德上對妻子和子女應負的最低的義務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遺囑自由原則處于優先地位,因此該行為不屬于違反善良風俗的情形。由此確立新的“善良風俗”審查標準,即法院在審查一個法律行為是否屬于“違反善良風俗”的情形時,則必須依據該法律行為的內容并結合法律行為雙方的動機和目的進行綜合考量參見:BGHZ 141, 361. ,即在上一個部分所述及的“善良風俗”內容的客觀判斷標準之中加入主觀考量因素。
對此采取“無限審查”原則,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善良風俗”主要反應某一特定時期整個社會不特定多數人的一般道德觀念,其內涵靈活多變且具有高度抽象性,需結合具體案件的整體事實進行綜合評價。相比“重大過失”等其他不確定法律概念而言,幾乎難以從技術上劃清上下級法院之間的審查界限。其二,正因為概念內涵的高度模糊性,導致在司法審判中傾向于通過不同案件不斷類型化的途徑將上述內涵具體化。而類型化的作法無疑需要對第三審法院的審查持有開放性態度,歸納個案中各項重要事實進行一般化處理。“違反善良風俗”情形在日后的發展過程中不斷細化為束縛式合同(Knebelungsvertrag)、濫用優勢地位、顯失公平典型代表是《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規定:“某人利用他人處于急迫情勢、沒有經驗、缺乏判斷力或意志顯著薄弱,以法律行為使該他人就某項給付而向自己或第三人約定或給予與該項給付明顯地不相當的財產利益的,該法律行為尤其無效。” 、賄金約定、違反婚姻家庭秩序等若干類型即是這種方法運用的最佳例證。參見:Rüthers/Stadl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6. Aufl. , München 2009, §26 Rn. 35-41a.
(五)評價
通過上述聯邦最高法院對于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審查方式的詳細考察,一方面固然可以輕易地提煉出“概念內涵-各項重要事實-邏輯思維過程”這一常規有限審查附加少數無限審查的例外,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對這一原則背后所承載的司法理念進行解讀。概念的核心理念、理念項下發展的若干重要事實因素、經驗法則、法律推理的邏輯合理性、甚至是少數概念的類型化區分等等,如此眾多審查角度的切入令人眼花繚亂,繁雜之中卻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目標:所有因素的審查都涉及到個案特殊情形的一般化處理,即將不可復制的案情轉化為一般化的生活案件事實,為未來的其他案件提供指導作用,從而在司法裁判體系內逐漸形成明確統一的規則,而這就是“司法統一”的終極目標所在!解讀至此,“司法統一是不確定法律概念司法審查的風向標”這一結論也就呼之欲出了。
將第三審程序置于歷史發展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1877年《民事訴訟法》中將上告金額作為第三審程序的惟一準入標準,經1950年上告限額制與上告許可制的并存局面,發展至1975年接納上告制的引入,最終至2002年改革中上告許可制的最終確立,經過上百年的發展歷程,案件的原則性意義、發展法律或保障統一司法的需要逐步成為衡量能否進入第三審程序的唯一標準,德國一百多年的民事訴訟立法發展史向我們昭顯著“司法統一的公共利益”在第三審程序的功能設定中的絕對主導地位。由此第三審程序的功能設定與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審查導向趨向于一致。
這種研究方法往往被稱之為功能性的研究徑路,最早為斯溫爾教授(Schwinge)在其著作《第三審程序基本原理》中所倡導[11],主張將第三審程序的功能作為判斷是否具有可審查性的惟一標準,即第三審法院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審查范圍的確定,主要取決于其是否具有司法統一的公共利益,即該具體的個案是否涉及到對典型的或者可以一般化的生活案件事實進行判斷并為未來的其他案件提供指導作用。有趣的是,筆者發現斯溫爾教授在其著作中對不確定法律概念審查原則的分類與上面所總結出來的司法判例審查規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斯溫爾教授將不確定概念的審查區分為以下三類:(1)對于內容包含有抽象的一般性標準的不確定概念,毫無例外應該受到第三審法院的審查。這類不確定性概念主要包括“善良風俗”、“誠實信用”等等。因此當下級法院將“船”歸屬入德國《刑法》第243條“建筑物 ”,將“撿起倒斃的野獸”歸入《刑法》第292條“非法狩獵”中,將“左手的中指”歸入《刑法》第224條 “身體的一個重要肢節”的法律構成要件中時,為實現司法統一,法院應將其涵攝過程納入第三審的審查范圍;(2)第二類不確定概念的內容因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當事人的具體情況而產生差異,因此該類概念內涵的確定就司法統一的角度而言并無太大意義,如“聚眾鬧事 ”、“辱罵性的言語 ”等。聯邦最高法院在此類案件中將該類不確定概念的適用稱之為“重要的事實問題”;(3)第三類不確定概念的法律可審查性取決于具體的案情的性質。雖然無法將這三類與之前所論述的三個具體審查事項一一對應,但是其指導思想一致。而斯溫爾教授作為功能分析學說的首個倡導者,本文第四個部分所做的實例考察也算是對此學說的一個佐證吧。 后經眾多門生斯溫爾教授的博士生隨后針對該主題撰寫博士論文、教授資格論文等,為該功能分析方法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 Klaus Wamser. Die Revisibilitt unbestimmter Begriffe[D]. Dissertation Marburg 1961; Klaus Duske[D]. Die Aufgaben der Revision[D]. Dissertation Marburg 1960; Ernst-Walter Hanack[D]. Der Ausgleich divergierender Entscheidungen in der oberen Gerichtsbarkeit[D]. Hamburg, Berlin 1962. 的推廣,現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支持。
[HS(3]
四、對中國的啟示
(一)必要性分析
由于不確定法律概念在內容和外延上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因此法官在對其進行法律適用的過程中,一方面,在對處于大前提的法律規范尋找的過程中,必須通過法律解釋及其法律補充的方式對其規范內容從深度和廣度上進行拓展。而在對法律規范進行選擇及其具體化的過程中,必須結合將要評價的案件事實。另一方面,未經加工的原始生活事實則必須以法官預先判斷所適用的法條的法律構成要件為依托,才能最終形成完整的案件事實。由此可見,在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的邏輯結構中,我們無法簡單地依托“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區分標準來產生上下級法院之間的職能分野。因此另辟新徑采取功能分析的方法是克服其邏輯困境的唯一選擇。德國一百多年的民事訴訟立法發展史顯示,第三審程序的主要功能在于維護國家對司法統一的利益。因此無論屬于何種類型的不確定概念,其第三審的審查范圍都取決于該具體問題的審核是否具有司法統一的公共利益。當然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邏輯演繹的方法無法最終實現對不確定法律概念具體化過程進行分解的目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對于本主題的討論毫無建樹。在一定程度上,職能分層的審級制度以及“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邏輯區分標準構成實現不確定法律概念功能的“雙駕馬車”。功能上的價值分析以法律適用的邏輯分析模型為基礎,由其勾畫出法規尋找與事實確認的大致分屬區域,輔之于職能分層的審級架構層面的篩選,形成法官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梯級審查體系。
分析至此,即便經過層層論證最終得出這一結論,可能仍然有很多人對此結論產生質疑:這一問題的探討在中國的語境下究竟有何意義,因為在中國目前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設計中根本就不存在第三審程序。這讓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幾個現實問題: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審查是否只能在第三審程序中進行?考慮到“在中國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短期實現審級制度的根本性變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這一基本現實,可否將該審查方式轉移至第二審程序?這種轉移是否有必要?
筆者認為,運用邏輯演繹和功能分析的方法對不確定法律概念進行司法審查,最大的功效在于,依據不同的職能劃分,在不同的審級結構中實現對不確定法律概念具體化過程的逐級分解。至于是否要在第三審程序中進行終極過濾,則依據各國的審級結構設置而有所不同。因此第三審程序的缺失并不足以形成“不確定法律概念審查體系構建”的反對理由。因為無論最終我國是否采用第三審程序的制度框架,在原有的第一審法院和第二審法院之間真正形成職能上的分層都將是司法統一需求下的未來發展趨勢。換句話說,前面部分所闡述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審查,從第三審程序轉移至第二審程序并無理論上的障礙。
(二)本土化改革措施
那么,如何實現該審查原則在中國的本土化改造呢?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 制度背景:職能分層的審級結構框架的建立
從新近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民事訴訟法修正案》內容來看,并未直接涉及審級制度的調整,同時考慮到目前民眾對于法院的公信度、法院人力資源結構以及司法文書規范化等現實因素[12],中國目前所實行的兩審終審的審級結構框架在短期內確實無出現重大變革的可能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完全無所作為。即便在二審終審的制度框架內,我們依然可以寄托于在上下級法院的案件往返之間,形成不同級別法院之間的司法職能分層,在體制內謀求功能上的突破。德國2001年改革后所建立的審級結構框架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第一審程序“糾紛解決”功能的強化。首先通過強制性和解程序前置的設定,過濾掉一部分雙方爭議不大、存在較大和解可能的案件,從源頭上控制進入第一審程序的案件數量,從而實現有限司法資源的效用最大化;其次強化法官對于程序的控制權,完善法官釋明體系,力求使當事人在法官的引導下窮盡其所掌握的重要的攻擊和防御手段,盡可能實現案件在第一審程序得到充分完全的審理,為第二審程序功能的轉變提供理論前提和正當性支撐;最后擴展獨任制法官在州法院的適用范圍,從而實現第一審民事案件原則上由獨任制法官審理的目標,大幅提高訴訟效率,加快訴訟進程。
第二審程序“監督職能”的功能性轉變。2001年改革將第二審程序功能設定為“錯誤監督及其糾正”。為實現這一職能上的轉變,需輔之以兩個措施:其一,只要沒有明確的依據對第一審法院所確定的對判決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的正確性和完整性存有疑慮,則該事實確認對于第二審法院具有拘束力。而“是否存有疑慮”,法官對此享有自由裁量權,因此為避免風險,上訴人應在上訴申請中盡可能詳細地列明理由,促使法官相信,在上訴程序中重新進行證據調查是有必要的。其二,對新的攻擊和防御手段在二審程序的提出進行限制。只有當涉及第一審法院明顯疏忽或認為其不重要的法律觀點由于第一審程序存在瑕疵或非因當事人過失而沒有提出的攻擊和防御方法的情況下,才允許在第二審程序中提出新的攻擊和防御手段。通過這兩項措施,完成對第二審程序的職能改造。
第三審程序“司法統一”功能的實現。所有的上告限額制度都被許可上告制所取代,即上告限額不再作為提起上告程序的準入標準,而案件的原則性意義、發展法律或保障統一司法的需要將成為衡量其能否進入第三審程序的惟一標準。
由此可見,德國“糾紛解決-查漏補缺-司法統一”的三級法院職能結構體系的建立,一方面為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層級司法審查體系提供了功能實現的平臺,另一方面該審查體系所依附的具體個案又為各級別的法院職能分層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兩者互為依托,互為促進。以此為借鑒,若要在我國既有的兩審終審制度框架下實現職能的分層,最為可能的做法是將第二審程序改造為“兼具監督與司法統一”職能的最高級別審級。而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層級司法審查規則的設立無疑是一個絕好的契機。下面將對此展開重點論述。
2. 改革措施:建立以不確定法律概念為媒介的層級司法審查體系
如前所述,一旦在上下兩級法院系統中形成審級功能上的分層,下一步需要做的則是以一系列有代表性意義的個案為依托,形成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審查分級,從而在第二審法院中抽象出能夠促進司法統一意義的“法律問題”。下面筆者仍然以在本文開篇所提及的“瀘州遺贈案”為例進行具體分析。
四川瀘州男子黃某彬生前立下書面遺囑,將其個人財產以遺贈的方式贈與給與其公開同居5年的情人張某英。因實際控制財產的妻子蔣某芳拒絕分配財產,張某英以蔣某芳侵害其財產權為由訴至法院。一審法院認定,遺贈人黃某彬的遺贈行為違反了《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應屬無效行為,故駁回原告張某英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認定,黃某彬基于其與上訴人張某英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訂立遺囑,將其遺產和屬于被上訴人的財產贈與上訴人張某英,以合法形式變相剝奪了被上訴人蔣某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根據《民法通則》第7條和第58條的具體規定,應確認為無效民事行為,故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參見: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1)納溪民初字第561號];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1)瀘民一終字第621號]。
按照筆者在前面部分所介紹的審查方法,那么針對上述案件其審查思路應有如下框架以下針對案件實體問題的分析得益于與賀劍的討論,特此表示感謝。 :
(1)首先是邏輯結構之大前提的尋找:由于涉及到黃某彬生前所立書面遺囑的法律效力問題,因此首先考慮選擇適用的法律規范是《繼承法》第16條的規定《繼承法》第16條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并可以指定遺囑執行人。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指定由法定繼承人的一人或者數人繼承。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 ,以此作為判斷遺贈行為是否有效的直接法律依據。但由于法律適用的邏輯結構之“大前提”的法律規范應為“完全法條”所謂“完全法條”,是指在該類法條中兼具法律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兩個部分,并將該法律效果歸于該法律構成要件之下。而法律規范體系中的大部分條文為“不完全法條”,即不具備法律效果的規定。因此為構成“大前提”,必須通過解釋、補充或者限制等方式將“不完全法條”轉化為“完全法條”。(參見: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127-132.) ,即該法條內容必須能夠單獨構成繼承權發生依據的請求權基礎,因此當直接適用的法律依據不足以構成“大前提”的情形下,必須通過補充或者限制等方式將這種“不完全法條”轉化為“完全法條”,即必須結合《繼承法》第22條的消極生效要件參見:賀劍未發表論文《案例評析的時代精神》。 以及《民法通則》第7條以及第58條關于民事行為無效的一般要件進行綜合判斷。《繼承法》第22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立的遺囑無效。遺囑必須表示遺囑人的真實意思,受脅迫、欺騙所立的遺囑無效。偽造的遺囑無效。遺囑被篡改的,篡改的內容無效。” 此為“法律問題”的范疇。
(2)其次是邏輯結構之小前提的確定,即各項具體事實的查明,其中包括黃某彬所立書面遺囑的事實、與原配妻子之間的婚姻狀況、其與原告張某英的同居關系、遺贈財產的范圍、夫妻共同財產的劃定等等。此為“事實問題”的范疇。
(3)將法官所確認的案件事實歸屬入法律構成要件的涵攝過程,即判斷黃某彬的遺贈行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當我們的分析思路進行至第三個步驟,便立刻能意識到本案的關鍵在于,黃某彬向第三者張某英遺贈財產的行為,是否構成《民法通則》第7條和第58條意義上的“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而該問題即是涵攝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進行至此,“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邏輯區分即已完成其任務,隨后的價值分析則依賴于職能分層的審級制度上的篩選。
通過論文第三部分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出,最高審級法院的終極目標在于,將個案中不可復制的具體案情轉化為一般化的生活案件事實,從中抽象出明確統一的司法審查規則,為未來的其他案件提供指導作用。而“不確定法律概念”不失為一種最為有效的審查媒介。現在我們將關注點再一次聚焦“瀘州遺贈案”。其中所涉及到的“社會公德”正是本文所關注主題“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表現形式之一。立遺囑人黃某彬在病中住院期間,基于其與上訴人張某英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訂立遺囑,將其遺產贈與張某英的行為是否屬于“違反社會公德”的一種具體形式。通過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終審判決書我們可以看出,法院認為黃某彬通過遺囑所形成的贈予行為,侵犯了妻子蔣某芳所享有的合法財產繼承權,且違反了夫妻之間所應遵守的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的婚姻義務,因此該遺囑無效。圍繞“黃某彬與張某英的非法同居關系是否會因其與社會公德之間的沖突,而導致黃某彬通過立遺囑這一行為自由處分自身財產的權利受到限制”,學界各方人士展開大討論。
關于這方面的討論不勝枚舉,筆者無意于在此問題上浪費過多筆墨。被大家所忽略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在于,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審理這一具體案件的管轄法院,同時也是二審終審框架下的最高審級法院,其判決書所承載內容是否只需包含“黃某彬遺產的具體數額確定”、“以遺囑的形式贈予二奶遺產的行為是否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等具體問題的探討。不可否認,司法審判旨在為具體案件提供糾紛解決的途徑,理所應當側重于個案中具體案情細節的探討以及是否能夠將其成功涵攝入相應法律規范的判斷。但作為司法審級制度“金字塔”頂端的終審法院,將糾紛解決所涉及的具體問題探討列入其惟一審判目的則值得商榷。因此就“瀘州遺贈案”而言,討論的重點不應僅限于黃某彬的贈予行為是否違反“社會公德”,更為重要的是,在其個案的判斷過程中,法院所據以考量的具體因素是什么,當事人行為的性質是否會對該法律行為的效力產生影響。由此才能抽象出對于“社會公德”這一不確定法律概念的一般審查標準,為未來的其他案件提供指導作用,并最終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司法統一”這一終極目標。
無獨有偶,四十年前的德國也曾出現過類似“瀘州遺贈案”的判例(具體案情筆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有限審查的例外”中進行過詳細闡述),暫且不論由于不同價值取向的選擇所導致審判結果上的差異,即便是在合理性論證階段,由于在對不確定法律概念進行司法審查所采取方法論上的差異,其二者
所達成的抽象性司法審查規則也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德國最高法院判例認為,善良風俗原則設定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懲罰或制裁當事人的“不道德行為”本身,而在于“該法律行為在性質上是否違反善良風俗原則”,因此衡量的重點是當事人行為的性質在該法律行為的構成上是否起著重大的作用。由此確立新的“善良風俗”審查標準,即法院在審查一個法律行為是否屬于“違反善良風俗”的情形時,必須依據該法律行為的內容并結合法律行為雙方的動機和目的進行綜合考量,即在上一個部分所述及的“善良風俗”內容的客觀判斷標準之中加入主觀考量因素。但縱觀我國“瀘州遺贈案”的一審和二審判決書內容,盡管在遺贈無效的法律依據上有所差異,但其審查的角度與方式沒有太大的差別,且將大量的筆墨花在遺贈財產范圍的確定以及不同位階法律規定之間的適用關系等等。而對于“社會公德”的內涵確定,卻僅以“只能通過不同歷史時期法律具體規定所體現的基本社會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加以確定”而一筆帶過,但這種“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究竟為何依然一團混亂。
經過上述邏輯與功能的雙層分析工具進行剖析后,本案的分析路徑則可清晰地歸為四類:大前提之法律適用規則的尋找,此層面的探討無疑必須具備民法教義學的學術功底;小前提之具體事實的確認,則集中于各項證據規則的適用與事實確認技術的運用;小前提之涵攝過程的判斷,則以司法統一為其發展導向,逐級抽象出不確定概念中具有典型意義的判斷規則;最后才是立足于這個體系之外價值探討,如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婚姻道德與財產權利之間的價值沖突等等。四種不同分析路徑自成體系,擁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及其價值取向,如果不加以區分隨意混淆,不僅無法自證其說,也將缺失學術交流的平等語境,從而陷入“各人自說自話”的境地,學術價值也就相應大打折扣。
依照中國目前所實行的“四級兩審終審制”的法律框架,在短期內實行審級制度的根本性變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在此現實下,只能寄托于在上下級法院的案件往返之間,形成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分層,在體制內謀求功能上的突破。由于上述舉措在形式上并未突破兩審終審的制度框架,因此在我國的審級制度改革中,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具體化的審查”為突破口,即在第一審程序中,以法律適用的邏輯分析模型為基礎,由其勾畫出法規尋找與事實確認的大致分屬區域,同時在第二審程序中,以“概念認識錯誤-是否對所有重要性事實審查窮盡-是否違反經驗法則或具有可責問的違反程序性事項”為線索,分離出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一般審查原則,為未來的其他案件提供指導作用。只要成功構建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審查制度,第三審程序的設立也就指日可待了。
[HS(3] [HTH]五、結語
[HTSS][HS)]
回復至上述德國第三審法院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審查過程來看,司法統一的需求迫使聯邦最高法院不可能放棄其在不確定法律概念這一領域的司法審查權,因為這一需求必須借助于審級框架這個媒介,將各地的法律適用信息由下至上反饋至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然后再將其統一適用標準由上至下涵蓋至國家的整個領域,由此形成職能分層的金字塔型審級建構體系。但同時這種司法上乃至政治上的向心力又是司法統一的最強推力,最高法院通過對適用同一不確定法律概念的不同案件數次循環往復的篩選,采用功能分析法對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進行區分,逐漸過濾出抽象化一般化的對該不確定法律概念進行判斷的通行標準,從而為未來的其他案件提供指導。
誠然,本文所詳細介紹的對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技術性探討可能仍然無法解決“瀘州遺贈案”中婚姻道德與財產權利兩種價值觀的沖突,更無助于普適社會價值觀的建立,但至少能夠在這種個案糾紛解決中創設出普遍適用規則,為爭議性案件提供形式合法性,而這卻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信任危機中最為迫切需要的司法權威的重要來源。ML
參考文獻:
[1]何海波. 何以合法?——對“二奶繼承案”的追問[J]. 中外法學,2009,(3):438-456.
[2]黃卉. 論法學通說[J].北大法律評論,2011,12(2):334-382.
[3]Barbara Stickelbrock. Inhalt und Grenzen richterlichen Ermessens im Zivilprozeβ[M]. Kln 2002, S. 30-32.
[4]Hans-Martin Ruff. Grundfragen der heutigen Verwaltungsrechtslehre[M]. 2. Aufl., Tübingen 1991, S. 181.
[5]Lothar Seuffert. ber richterliches Ermessen[M]. Gieβen 1880, S. 3, 10.
[6]陳景輝. “開放結構”的諸層次——反省哈特的法律推理理論[J].中外法學,2011,(4):666.
[7]黃茂榮. 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181.
[8]Reinhard Gai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G]//Band 6 Sachenrecht, §§ 854-1296, 5. Aufl., Nrdlingen 2009, S. 829.
[9]Othmar Jauernig.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M]. 13. Aufl., München 2009, S. 90.
[10]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M]. Zweiter Band: Das Rechtsgeschft, 3. Aufl., Würzburg, S. 365.
[11]Erich Schwinge. Grundlagen des Revisionsrechts[M]. 2. Aufl. , Bonn 1960, S. 26-38.
[12]陳杭平. 比較法視野中的中國民事審級制度改革[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2,(4):126.
本文責任編輯:李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