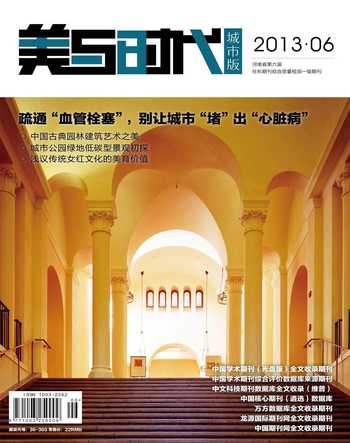淺論東方審美文化對紫砂藝術的影響
經利群
整個東方審美文化,以中國、印度的文化為代表,顯示著與西方不同的特色。由于印度的佛學具有獨自的古老思辨形態,并且印度的美學學科基本上被統馭在佛教的影響之下,其思維方式就與西方基督教及西方的推理方式甚為接近。而真正體現東方意識的審美追求和思維特色的,是在中國保存下來的儒、道、禪學傳統及其融聚生成的新學。儒、道、禪從生成到融合是東方審美意識演化的本質反映。而這種本質反映所呈現出的特點,則可以落實到具體的東方文化產物上。
宜興紫砂藝術便是反映意識文化的產物,傳統的東方審美取向,是宜興紫砂長盛不衰的生命所在。縱觀宜興紫砂藝術發展的歷史脈絡和演繹軌跡,從明清以來,經歷了由粗到精、由大到小、由簡到繁,進而返璞歸真的過程,無一不留下不同時代審美品位的印記。從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看,紫砂壺無論是造型、底蘊、題材,還是表現方面,都深深貫穿著東方文化的精髓,無處不透露著東方審美文化的氣韻。它以包容性的特質,貼近藝術與文化的距離,打造出獨特的美感和生命力。然而作為源頭文化與藝術產物,影響是主動的,接受是被動的。紫砂藝術正是在這種審美文化的影響和推動下,發展成為帶有地域文化特點的藝術形式。而通過對東方審美文化的特點分析,可以發現其對紫砂藝術的具體影響。
第一,東方審美追求普遍體現了人類的審美愿望和理想,以其對現實生活的滲透,左右著紫砂藝術表現題材的廣泛性和生活形。
紫砂壺是一門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卻又貼近生活的藝術,它強大的表現力來源于豐富多彩的題材,而題材的選擇則來源于人類生活的靈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在我們本民族的審美氛圍里,已經形成了由個人的審美體驗和人格境界所肯定的關于美的觀念尺度和范型模式。這即是由生活所無法滿足的精神追求轉化而來的期許與渴望。應景而生的紫砂壺便是這種期許與渴望的寄托。例如由人心趨吉所形成的吉祥文化,便被廣泛用于紫砂藝術的創作中。《福壺》以蝙蝠嵌鈕,通過諧音的巧合來寄托求福的希望,壺體則扁平而鼓腹,以飽滿的姿態彰顯對理想的進取與追逐。“如意”這一傳統吉祥紋樣,則更為普遍地出現在各類題材的紫砂作品中,或以靈芝為形,或以云朵為狀,麗而不俗,多以精致的浮雕形式繞壺腹一周,不僅增添了悅目怡情的趣味,更傳遞出心愿得償的美好祝福。至于桃、竹、月季等寓意長壽或美德的圖案,更是屢見不鮮,由此可見,人們對吉祥美好的渴望,已經深入及輻射到了紫砂藝術的深度和廣度上。
第二,東方審美文化有著宏深的哲學基礎,以其充滿自信的踐行表達,生發了紫砂藝術無限的創作思維和創作動力。
對心靈、人格的極度推崇,乃是東方審美意識的集中體現,它強調從感應中獲得主動之心,不以物我分割為前提,卻以心象含物為機緣,使自然的素樸存在被觀念巧妙織入情性之網,將物體人格化、心靈化。紫砂藝術無疑深受這一哲學思想的影響。它的創作以物為客觀基礎,但并不以物為主觀指導,其藝術的形成與架構完全來自于藝人們思想上或情感上的領悟,再由此生發為各具形態的藝術體。它的創作多半來自于可感性自然的延伸,比如對花鳥蟲魚、樹木叢林等自然物象的感受,皆可在藝術中得以靈動而出彩的完美表現。如蔣蓉大師的《青蛙荷花壺》,取意于夏日的荷塘,鮮明樸素,盛開的荷花瓣嵌滿整個茶壺,荷葉卷曲,包裹起壺流與壺把,一只青蛙臥坐于壺蓋上,轉著靈動的眼珠凝視著遠方,雖以靜態處之,卻覺一股生機冥冥流出,不僅是有感于眼前客觀的形體,更是被這些美好景致所締造出的意境深深觸動。“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在這種靜靜的觀照中,凝結的其實是一種向往隱逸,向往自然的澄澈心懷。
第三,東方審美文化具有既張揚個性又具備內斂而含蓄的氣質,充盈了紫砂藝術的品味與內涵。
與西方開放且崇高的審美不同,東方審美更多的講究內斂和含蓄,突出獨到的個性,即是忽略外在的修飾與裝點,而以塑造內蘊為根本。紫砂藝術原本就受到儒家推崇主題心靈學說的影響,因而在創作方面更加注重對于作品思想表達的提煉和完善。從外在形式上看,拙樸是紫砂一貫的風格,保持原滋原味的沉雄古韻,天然去雕飾。而其內蘊則通過藝人們細致的體悟審查,心性陶冶,通過對細節的玩味與塑造,將個人對藝術的觀照融入到作品中去。肩線的圓滑流轉,壺壁的交接挺括,浮雕的立體形象,流把的對稱蜿蜒,看似普通的細節,實則一分一毫都是內在美的提煉因素。再華麗的外表也是虛浮,而內在的氣質則會愈久愈綿長,紫砂選擇將文化溶解在骨髓中的生存方式,無疑成為了它永恒藝術價值的體現。
從服務于人們使用功能的角度出發,紫砂壺處處充滿著人文的關懷,從藝術特色的視野展望,它又處處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和東方審美文化的魅力。藝術是文化的產物,也是文化的具象表現,是文化的客體寄托,因而在文化的影響下,紫砂以獨特的東方語言,給人以賞心悅目的藝術享受,延伸著人類社會的審美體驗。所以我們相信,東方審美文化所閃現出的心性修煉、生存智慧,一定會持續著對紫砂藝術的滲透,從而在以后久遠的文化生活中,展現出獨特而永恒的價值和魅力。
【作者單位:宜興紫砂工藝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