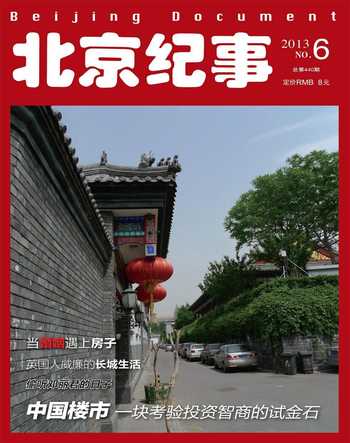陳俊杰:裘派,雄踞凈首
麻雯
十凈九裘。裘派魅力何在?陳俊杰用一生體味著其中的奧妙。
第一次知道“裘派”是在1976年。“文革”剛結束,樣板戲一枝獨秀的年代終于一去不返,傳統戲逐漸恢復,如同一股甘泉滋潤著人們貧乏的精神世界。一天,陳俊杰在老師的收音機里聽到一段《打龍袍》,一個高亮醇厚的嗓音牢牢地抓住了陳俊杰,“簡直迷得不得了”。如今想來,用“渾然天成、美不勝收”描述并不為過,但當時的他只是一個勁兒地嘟囔:“哎呀,還有這么好聽的聲音,還有這么好聽的聲音……”向老師請教,才知道裘盛戎這個名字,從此之后,他便與裘派結下不解之緣。
情帶聲,氣為本
著名戲曲作家、理論家翁偶虹先生曾這樣評價裘盛戎的唱腔——“腔雖老而因裘則新”;“旱香瓜——另個味兒”。他一改舊時花臉直腔直調的唱法,進行大量板式的創新,極大豐富了花臉的聲腔表現力,對京劇的貢獻有口皆碑。
在陳俊杰心里,裘盛戎先生的唱腔無可挑剔,“他的發聲方法和共鳴非常科學,韻腔技巧講究‘提、挑、彈、蹦、滑……,在唱腔中注入了濃厚的感情色彩。”他想盡各種辦法,收集了裘先生大量演出的資料,并用心學習裘派弟子方榮翔、李欣等老師的新劇目,粗淺地了解了一些“裘派的皮毛”。
1991年,陳俊杰有幸拜在裘派傳人李長春先生門下,在老師的指點下,大有“茅塞頓開”之感。他對裘派藝術的領悟也日益深刻,“光是李長春老師的一個出場,我便學了多少年。看似簡單的動作卻體現出深厚的內在積累,以及對舞臺節奏和心理節奏的準確把握。”
京劇凈行最早講究聲宏激越,如金少山先生,其一開口便聲震屋瓦、氣勢磅礴。而裘先生則在繼承的基礎上,形成了更為圓熟含蓄的特點。與此同時,增加了“柔”的一面,如《將相和》《除三害》等,而在《趙氏孤兒》中則吸收傳統劇目《七擒孟獲》的漢調唱腔,創造了“漢調二黃”,可謂膾炙人口。
“有句老話叫作‘千金話白四兩唱,強調了念白的重要性。”陳俊杰介紹,“裘盛戎先生最大特點是‘口甜,含有笑音。晚期則趨于蒼勁,像《將相和》中的大段獨白,感染力非常強。”
裘盛戎先生經常說:“氣是聲之本,萬音氣為尊。嗓子再好,唱得再好,若氣口運用得不好,也是立不住的。”氣口安排得合理與否是唱腔成敗的關鍵,裘派對于明暗氣口的運用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越是經典的唱段,越能考驗演員的功力。大家耳熟能詳的《秦香蓮》中的唱段不到一百個字,但慷慨激昂,令人回味無窮:
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駙馬爺近前看端詳,上寫著秦香蓮她三十二歲,狀告當朝駙馬郎,欺君王,藐皇上,悔婚男兒招東床,殺妻滅子良心喪,逼死韓琪在廟堂。將狀紙押至在了爺的大堂上,咬定了牙關你為哪樁?
這是一段西皮導板原板轉流水,陳俊杰無數次觀摩前輩的演唱,并結合自己的嗓音條件,設計了9個氣口。如今,每每唱到這一段,行云流水、收放自如的表演總是贏來滿堂喝彩。
完整的藝術
“裘盛戎先生之所以能自成一派,而且傳承這么多年,桃李滿天下,是因為他的藝術非常完整。不單單是唱,京劇的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全面發展,將銅錘和架子花臉融為一體,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聽震撼。此外,裘先生不是為唱而唱,為舞而舞,而是嚴格地從生活出發,運用高超的藝術手法來描繪劇中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陳俊杰對此深有感觸,裘先生塑造的包拯、魏絳、姚期、竇爾敦、單雄信等鮮明的人物形象是他心中的高峰,難以企及。
裘盛戎先生的代表劇目眾多,但《姚期》可以說是代表作中的佼佼者。“《姚期》是裘先生自創的,將花臉藝術推向了極致。通過精湛的唱腔、道白、身段和表演,將姚期這個人物由內而外地刻畫出來。無論到哪兒,這都是打炮的戲,對演員各方面要求極高,非一般人能演。短短的1小時20分鐘凝聚了裘先生一生的智慧。”陳俊杰感慨道。
可以說,《姚期》之于裘盛戎相當于《紅樓夢》之于曹雪芹。姚期這樣一個封建社會的忠良將領的坎坷命運被裘先生演繹得有血有肉。裘盛戎在設計姚期這一人物形象時的精彩表演至今無人能及,該劇堪稱代表20世紀京劇凈行水平的經典之作。
“裘先生武功基礎特別棒,好過一般的架子花臉,腳底功漂亮極了。”在跟隨李長春老師學習《大探二》的過程中,陳俊杰觀察到,雖然老師演繹的是徐彥昭銅錘花臉,但他身上的韻律和氣勢遠遠超出了這個范疇。“身上猶如風擺荷葉,欲進則退。”他細細品味著這份獨特之美。正是裘盛戎先生把若干年來凈角銅錘和架子、文與武兩門界限打破,統兼二者,不但擅演銅錘的徐彥昭、包公,架子的曹操、嚴嵩、劉謹也不在話下,甚至可以演武二花的張飛。
就陳俊杰個人而言,他最喜歡《秦香蓮》中的包公形象。包公出場的身段他曾反反復復地琢磨了許久,日夜思考,整個人都有些癡了。他在追求一種感覺,“像一陣風,突然一停,太陽出來了。” 裘盛戎先生塑造的包公形象深入人心,有著“活包公”的美譽。
裘盛戎博采眾家之長,吸收了郝、侯兩派的精華,豐富自己刻畫人物的手段,同時彌補自己身材瘦小的不利條件,在臉譜、腿裝和舞臺的調度上下功夫。值得一提的是,裘盛戎先生演繹的包公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下場,“所有的裘派弟子都以此為高度”。這個下場繼承了麒派的特點,“一轉身之后,腰一涮,整身轉”。陳俊杰介紹,當年,麒麟童(周信芳)來北京演出的時候,富連成科班是不讓學生觀看的。但只有裘盛戎和袁世海倆人跳墻溜出去,跑到戲院看了個夠。“麒派在這兩位藝術家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跡,舞臺上那種詼諧、瀟灑、突然發力均源于此。”
裘派還有一個特征,其塑造的大多是忠厚老實的正面人物,思想性、教育性較強。在《趙氏孤兒》這出戲中,一次,裘先生曾扮演了屠岸賈這個角色,但他自己并不認可:“我怎么演怎么不像壞人。”此后,便不再涉及,專心塑造忠臣魏絳。他跟著名琴師李慕良共同設計了《趙氏孤兒》的一個唱段,流傳至今,久唱不衰——我魏絳聞此言如夢方醒,卻原來這內中還有隱情。公孫兄為救孤喪了性命, 老程嬰為救孤你舍了親生。
“京劇是需要反復欣賞的藝術。若喜歡一部戲,喜歡一個演員,觀眾可以連看十場都不膩。京劇界的粉絲跟其他圈子不一樣,我們叫‘鋼絲。京劇圈子小,戲迷圈子也不大,大多都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和人生閱歷的人。京劇與戲迷一生相伴,永遠聽不完、說不完、看不完。”陳俊杰坦言,京劇給了自己太多榮譽、社會地位和光環,他始終虛懷若谷。而裘派藝術則像一座高山,需要用一生去探索、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