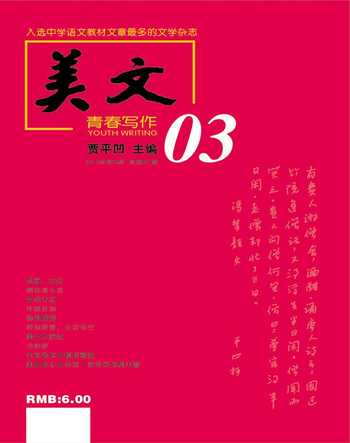花海
黎炘
關于花海這個詞匯,我從不愿輕易說出。就如新采擷的花每在跌宕的時間里曝露一分,它的香氣便會銷蝕一分。知道嗎?我曾想過屬于我們的回憶都隨著雨水下落在這片花海,躲過我們,在花朵與花朵的罅隙間閃著它們自己的光。
花海的北邊,是一條切割了地平線的鐵軌。起風的季節,灑落的花瓣就能將它掩埋,你便不會想到在或粉或白的花海下還隱藏著一條深褐色的軌跡。緩慢駛過的火車浮在花海之上,那場景,美得可以晃出眼淚來。我想若是風肯陪著它旅行,它們會去你說過的遠方。
——題記
四月份的梅雨,我棲息在江南小鎮某處潮濕的屋檐下。對面檐頭青色的瓦菲間不住地綻開細碎的水花,在檐角緩緩籠起一層清淡的煙霧,絮語著一些難于言說的溫柔。我索性光腳循著青石街走進巷弄,濡濕的發絲柔軟地滑過眼簾,心中覺得連惆悵也仿佛是旅途中尋獲的工藝品般精巧。
許多年后的如今,在這個被歲月反復拓寫得不溫不火的水鄉古鎮,我開始狂熱地懷念記憶里一點點淡出的那片花海。
那個夏天,因為響起花開的聲音而明媚。安坐在一堆草里遠望著花海哼著歌。他目光閃動,燦爛得如同那些花開,而我在一旁不解地問他:“你真的就這樣退學了嗎?”
安把一棵草銜在嘴角,眨著眼,“不是真的還是煮的?”他有著男生少有的大眼睛和酒窩,我看著他的臉,覺得花朵讓他的臉上染出純真美好的光暈。
我坐到他身邊,從一片浮花軟草里隨意地挑了一株野花在手中擺弄,“你的成績很好,再考慮一下吧,我覺得你會后悔的”。
安仰面嘆了一口氣,接著很大聲地笑,“就讓以后去后悔好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些事你不馬上做,那么,你就老了”。
“可是……”我本打算說話,安用手勢示意我停止。他把身上的藍白色校服外套脫下高高丟開,校服張揚地躍過落日,隨風滑落那抹看不清輪廓與邊際的花的海洋。消失。像一只鳥。
“我……終于……自由了!”
聲音在花骨朵里碰撞,產生孱弱的共鳴,我們聽見花海中疏疏落落的回音同遠處流轉的山嵐中燃起了的濃白煙霧一樣,緩慢得如同凝固。
看著安揮著雙手的背影在日暮里涂上艷彩,心中倏然有了異樣的情緒。那抹背影在我的眼前被慢慢推移,越來越遠,在我面前追不到的地方晃成一個真切的虛點。
我開始明白,安就像一只鳥。而我缺少了灑脫的翅膀。
曾經不止一次地和我描述他的愿望:在黃昏轉向傍晚時寫詩,寫很多的詩,直至集結成一本厚厚的詩集發表。我問這個愿望會實現嗎?他笑,搖搖頭:難,很難的。但是安終于還是把我一個人扔在學校里,朝著那個愿望一騎絕塵地狂奔。
沒有安的教室僅僅發生空出了一個座位這樣的變化,高考的逼近早已經使我們無暇顧及其他事物。唯獨班主任在安退學后的那一個月里喋喋不休地用尖刻的語調說安這孩子腦袋有問題,將來有他哭的時候。他反復說著那樣的話,而始終,我都皺著眉頭似笑非笑。
當安不和我一起上學以后,我只好一個人過幾條街去吃難以下咽的面條;一個人在老舊的借閱室寫細密潦草的筆記;一個人去反復地算三百多天后必將到來的日子;一個人被迫無奈地完成誓師大會的演講。
那場誓師大會之前,我們只花了三分鐘就把被曝曬到閃著白光的空操場填滿,班主任滿含期待地將稿子塞給我,我胸悶氣短地宣讀著。而那時我突然用眼角瞥見人群中一張張漲成豬肝色的臉,在煞白燥熱的日光里異常突兀。接著聽見稀疏的掌聲,淚水就失控地涌出眼底。我在心里想安才是對的,此刻他一定靜靜地坐在斑斕的花海深處,用指尖點過每一片花瓣,然后隨意寫下一個句子便可以輕巧地叩開心門。汗水一層一層地滲出劣質的校服襯衫,看著那些木然的臉,我想如果我停止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只是大聲喊出:我很累了、很無助、很迷茫。他們還有安就會訝異地回過神,然后認真地為我鼓掌。我甚至想著就這樣對著把我圍在升旗臺上的人們大哭一場,淚水會像雨水一樣澆滅這個過分響亮的夏天,讓它學會安靜下來。
我也知道我不會有這樣的勇氣。那些句子從我的嘴巴里變成無意義的咿咿呀呀,在我做完了所有的發聲練習后,誓師大會宣告結束。會后,操場遺留下來雜亂不堪的垃圾,班主任拍著我的肩膀稱贊我演講感情真摯,很好。
我在幾天后發現安的座位空了下來之后,我右邊的視線變得非常開闊。我會長時間地透過窗子看教室外的那棵樹,即使是上課也如此。那棵樹的葉子總是比周圍的葉子黃一點,我真擔心它會枯死,不知道會不會因為我的目光的期盼而茂盛起來。我不厭其煩地看著樹冠在下午兩點滿是陳舊感的陽光里起伏顫抖,或許那就是那片遼闊的花海某一朵花兒對著風輕巧搖曳的樣子吧。
其實窗戶前還有個女孩,叫晴。當陽光款款飄進來,她逆著光的側臉像一束梔子花般安恬。一個為微醺的下午,我透過窗子張望那棵樹時發現她在看我,而后我漸漸習慣在看樹的時候也去看她,或者,我只是在看她。
一次,晴突然走到我的座位邊。
“哎,你怎么上課時總是看我?”
“是嗎?沒、沒有吧”。
“沒有才怪呢!”晴小聲嘟囔。
接著我看見晴翹起嘴角,露出好看的微笑。然后我跟著笑,她看著我笑得更為燦爛。
我們從此在一起了,我覺得晴的笑是一株沾著雨水的茉莉花。
假日里,起風,沒有云。我騎單車路過花海,安如約等在那里,像是在等某片天空里不期而遇的飛鳥。
我問:“嗨,最近還好嗎?”安取出他那個灰色封面的硬皮筆記本,說:“看吧。”安的字跡清秀,連刪改的圈點都做得很工整,顯得尤為精致。看得出,這就是安想要的。“校園生活過得怎么樣?”安問我。“你走了以后班主任一直在罵你”。
我翻看他寫的詩,答非所問地說。安聽后哈哈大笑。
我想到了一些似乎很重要的問題要問他,“安,我真的不明白你為什么要寫詩呢?必須要棄學嗎?還有,什么樣的句子才會被稱作成詩?”
安轉過臉認真地看著我,我相信這些問題安一定反復思考過了,現在完全可以對答如流。
“你有沒有想過,海子為什么要自殺?而且選擇了臥軌這樣的方式?”
“是……是因為所謂的死亡意象嗎?”這突兀的問題使我無從回答,下意識地,我看了一眼被花兒小心地隱藏起來的鐵軌。
“不是,因為寫詩主要是精神的一種寄托形式。而當這種形式超脫了一定范疇,也就是可以引起世人共鳴的時候,這個作者本人的精神與現實會產生隔閡”。
“你沒有發現往往許多詩人的感情生活都是不幸的嗎?只有海子可以聽見雪吃草的聲音,只有他的心中永遠有一個春暖花開的地方……所以這個世界還是不能把他留下來”。
安說,薩福是如此;茨維塔耶娃是如此;普拉斯,更是如此。
“也許詩人天生有敏感的神經,和所有人一起陷入沼澤的時候他會最先找到一片花海”。安的話使我頗有感觸。
他點了一下頭,“你知道嗎?我一直都幻想著地圖上的某一個角落肯定標注著一個開遍花的島嶼,這片花海就是它的一個碎片。那里的飛絮與落花可以將你的存在給吞沒,你甚至能夠在天空中俯瞰到蔚藍里的一抹繽紛的色彩,就是因為它。你可以把它以外的地方都定義為塵世,可以沒有負擔地在那里生活好久好久,連時間也會純粹得如同永恒不變”。
從這一刻起,我完全地接受了安是“詩人”的身份。當他像是問我又或是問自己存在那樣的島時,火車驀然從遠處駛過,驚悸的天空將一聲鳥鳴的痕跡無限的拉長。
這里是一片浮在花上的海域,它在藍天下溫柔的燃燒著,而晴在初次來這里的時候便對我說她很喜歡。我想這也許并不奇怪,因為晴就像花一樣的女孩。我用許許多多的花兒形容她,以至于想去種許許多多的花,讓每種花兒的花期相接續使得一年四季都不顯得寂寞。我想一定是她的名字帶有神奇的魔力,仿佛和她在一起時總是晴好且聞見花香的天氣。好吧,雖然后來醒悟是因為在雨天里我們的傘上會叩響滴滴答答的節律,晴的雨靴走過積滿水的落葉林,輕得不留下一絲聲音令我不再因下雨而不安。
晴穿著及至腳踝的連衣裙和我分別走在兩條鐵軌上,那些花朵這時又仿佛是開在岸邊,晴彎下身花朵就會擦過她的臉頰。我們就這樣走著,走過花海和木屋,走過草地和溪流。就像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如此:花都開好了,我們一直走著。
晴一邊聞著花的香氣一邊問我:“你為什么會喜歡上我啊?”
“因為我收買了你的好朋友啊,她說你初中時很喜歡一個男孩子后來卻迫于家長的壓力而分開了。我想我也許會讓你快樂起來也說不定呢”。
她用訝異的眼神看著我好一會兒。半晌她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樣說:“我們說好了永遠在一起好嗎?其實我真的很怕,很怕我們會重復我的上一次的經歷。事情總是在偶然的狀況下變得無序和糟糕,未來不是誰也不能預料的嗎?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永遠在一起……”
“相信我,好嗎?”我走過去輕拍她的肩膀,嘲笑女孩子天生的多心。
天邊有云朵的影子在搖晃,琥珀色的黃昏恣意流散。
但或許晴說的是對的,事情的發展從來不是我們可以意料的。高三的時候我們居住的小鎮將被行政改制的消息已經傳遍,遠處高高低低的起吊機撐著灰霧迷蒙的天,空氣變臟,夾雜著土腥味和水泥石灰的粉屑。有大批的房屋被拆遷,而原先火車軌道邊的花海及周圍的大片土地未來將是某大型化工廠的建設用地。安想到這些難過與憤懣就無從發泄,已有一些從我們記事起便存在的樓房陸續被清除,塵埃高高的揚起,包裹著我們住的世界搖搖欲墜。安說:“我以為我們是不會變的,我以為我們生活的地方也是不會變的。”但也許人類已經有如此能力,抹去一處幾十年的存在容易至極。而另一方面,班主任終于找到了更加值得喋喋不休的話題:他試圖用行政改制后的種種好處,及將要投入建設的大型化工廠能為鎮上創收的效益,闡釋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富強。我聽著,已經非常厭惡去笑了。
當挖掘機肆無忌憚地開始殘酷的工作時,我們以為的花海原來脆弱渺小得可憐。死去的殘朵在地表升騰起巨大的香氣,我知道,彼此呼吸的是那些花兒積蓄在血脈里的芬芳與悲痛。
安告訴我們他要外出旅行生活,我對他總是突然作出的決定不滿。在他離開小鎮的前一天,安、我還有晴開始了一次“遺失風景一日游”,我們去了彼此小時候的幼兒園、父母工作的工廠或破辦公樓還有一個掉在廢墟里快要找不到的公園。那座公園里生銹的秋千只有晴依然可以坐在上面,這使得我和安有些無奈。安一直用很老式的相機拍著所有建筑物,它們中大部分要被拆除,而幸得保留的另一部分只是延遲到未來的某一天了推倒重建。也許我們真的應該聽時間的話,認同那些不留痕跡的消失。
我們繞著小鎮轉了大半圈,安說他還要整理行李便先回去了。我和晴漫無目的的地走了一路,竟然在已成為荒地的花海停下。那是下午五點,天光晦澀。太陽的光劃刻下粗糙的痕跡,像玻璃窗上慢慢淌下來的雨滴。我們在暗處看不清彼此,冰冷的空氣傳遞給臉頰輕微疼痛的觸覺。突然,晴語調極淺地說:“我想我們還是分手吧。”我以為是自己觸景傷懷的幻聽,笑著問,什么?“分手”。她說完就再不愿意開口了。我問為什么?因為無法容許自己所謂的愛情這樣地無疾?我用盡各種言辭去盤問,一直到晴哭出了聲時我也喪失了所有力氣……
我失去知覺地站在那,麻木地看著那些花已變成暗褐色枯莖,它們最終會腐爛,滲入大地。所有畫面全都不對了,那個被我無比珍視無比炫耀的青春以如此荒謬的方式義無反顧地離棄我。
安在古鎮的巷弄深處安靜的走著,雨點如針腳織在他灰色的大衣上。我走到了天井邊,四周忽而變亮,院角一株花樹發出簌簌響聲。安在經歷了很多波折后算是真正成為了詩人,經常會在各大雜志上發表新作并且小有轟動。我在處理完工作時會同他去很多地方旅行,我們偶爾還是會聊到晴,她此時已經是兩歲小女孩的媽媽,我們保持著朋友范疇的聯系。
經歷了太多時間的跌宕后我們開始不懼承擔這種變遷。當我的嘴邊的青苔更深了,我甚至欣然接受它在我的身上鑿刻出年老的印跡。
因為當年過于悲憤和突兀的心緒遠去了后,安和我同時找到了那座島——它棲居在心的幽避處,只要閉上眼,花香便漫過臉頰,如一道又一道淺淺的浪淹沒我們。
還有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