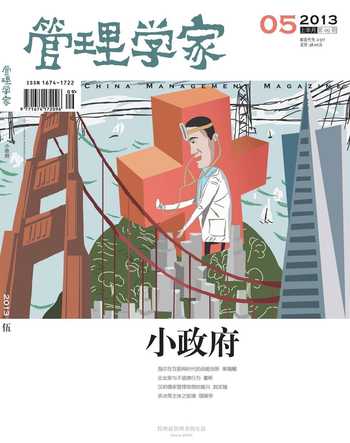中國古代“小政府”辨析
中國古代的政府,擁有一切權力,卻在社會職能上以消極應對顯示出小政府的某些特征,在不危及統治的地方可以實現社會自治,也許以現代眼光看,中國古代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小政府”,然而,實際并非如此
在公共管理領域,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近些年,學界一直在倡導“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模式,由此而引發了對古代政府的探究。中國古代的政府是小還是大,經常被人們拿來議論。有意思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自相沖突的言說,而且這兩種言說的影響都比較大。一種言說強調中國古代的小政府傳統,主要依據是歷代政府的官員數量,無論是網絡還是正規論文,都有人不斷說歷代王朝的官員數量如何少,以襯托出當今官員數量之多。另一種言說強調中國古代的大政府本質,反復指出古代國家的邊界如何大,蠶食鯨吞了社會的地盤,政府龐大而社會弱小,阻斷了社會自我治理的可能性。這兩種說法在邏輯上是相悖的,更要命的是,兩種說法有時還會出現在同一人之口,冰炭相容,倒也是一種奇葩。
當然,讀者不難理解,所有這些言說,不過是以古人之陳釀,澆當今之塊壘,大可不必較真。然而,這種不較真,又會在無意之中滋生出對歷史的輕慢,把本該嚴肅古板的歷史真的當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旦滋生出對歷史的輕慢或者把歷史隨心所欲扭成麻花,危害更大。所以,考辯歷史上政府的大小,本來屬于學者書齋中的小眾營生,不得不拿到大眾場合以正視聽。正如孟老夫子所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政府的大小,應該有而且必須有評判的尺度。大體上,這種尺度起碼要包括兩方面的指標:一是人數多少和規模大小,二是權力高低和職能邊界。
古代政府的人數與規模
經常見到關于古代政府官員人數的說法,尤其是古代的官民比例,往往給人比較強烈的視覺刺激。例如,報刊和網絡上有這樣一組數字:中國官民比例漢代為1∶7948,唐代為1∶3927,明代為1∶2299,清代為1∶911,民國為1∶294,當今為1∶30。筆者至今不知道這種比例是怎么算出來的,但是,當這種數字被人大代表在很莊嚴的場所講述、在很權威的報刊引用時,就需要略加考證。
這組數字肯定是依據某種資料計算得出的,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是,有四點需要提請注意:
第一,凡是說古代官員數量之少者,必須注意到古代的官員數量往往只包括官而不包括吏,如果考慮到任何政府結構都是金字塔型,上面的官員之下肯定存在一個龐大的基座,贊許古代官少者就要反問自己,是不是站得太高了點,把金字塔的基座忽視了?
第二,這種數字往往來自史籍中的志書記載,而稍有點常識就知道,相關志書多數記載的不過是一種“編制”數據,編制之外還有很大空間,時至今日,編外問題和臨時工問題依然十分突出,我們不要想當然地認為古代的編制限制就那么可靠。
第三,即便是編制數量,也有相當大的彈性。例如,正史《職官志》在敘述某個官職時,有不少官職下面寫的是“無員”。不要以為無員就是沒有人,其準確含義是不受編制限制,職數可多可少。
第四,有些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算進官吏隊伍,如明清的師爺、長隨,他們雖無官身卻從事官務,官場離不開他們,就人數而言,師爺和長隨的數量,要遠遠大于官員數量。鑒于這幾個因素,按照史籍編制人數核算的政府規模,只能作為參考。
以漢代為例,所謂漢代官民比例將近一比八千的說法,估計是從《漢書 · 百官公卿表》中“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的記載中計算出來的。而這個數據的問題在于沒有包括大量掾屬(下級小吏,相當于今之科長科員),而漢代所有掾屬都由行政長官自行聘任,根本不在朝廷的掌握之列。據《續漢書 · 百官五》注引《漢官》的數據,東漢的河南尹和洛陽縣下屬員吏為:“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有秩三十五人,官屬掾史五人,四部督郵史部掾二十六人,案獄仁恕三人,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干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洛陽縣“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史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官掾史、干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一個郡有員吏近千,一個縣有員吏近八百,恐怕規模不算小,但朝廷掌握的,不過寥寥十幾人。考古出土的尹灣漢簡,也有漢代一個鄉員吏編制三四十人的記錄,而史書所載鄉官,不過三四個而已。更重要的是上述河南尹和洛陽縣的員吏數據,還僅僅是編制數據,實際人數多有超編現象。
關于超編,這是歷朝歷代都無法根絕的頑癥。秦漢時期的超編很難找到具體史料,而明清的超編則有大量記載。根據《光緒會典》,清朝全國地方各級衙門共有編制書吏(稱為經制吏)共31276人,一個縣衙不過十幾人,但實際上在順治年間一縣的經制吏就已經達到百人左右。有研究者對光緒年間四川巴縣的吏胥數量進行過詳細統計,即便是給朝廷上報的經過裁汰的書吏數字,也在87-269人之間變化(李榮忠《清代巴縣衙門書吏與差役》),而實際數量則可能超出許多。清朝衙役的數量,從道光以后基本上規定不能超出80人,但據周保明統計,吳江等七縣一州衙門,大致每個縣衙的經制衙役數量在141-224之間,而且還是裁汰后的上報數字。至于州縣吏胥的實際數量,是一筆無法確認具體數字的糊涂賬。有一個官員的奏疏中說:“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游百川《請懲治貪殘吏胥疏》)可見,編外人員和聘任臨時工自古有之,不過當時的叫法是“貼寫”、“幫差”、“白役”等等。最離譜的,莫過于道光年間曾任四川巴縣知縣的劉衡所言,他上任時,有衙役7000人,經他手遣散了6780人。有人懷疑劉衡有所夸張,但一縣衙役動輒上千毫無可疑,有大量資料可以佐證。顯然,計算古代官民比例,忽略這種超編現象,所得數據就失去意義。
至于編制本身就規定的“無員”,則無法以固定數據計入官民比例。如《漢書 · 百官公卿表》在九卿之首的“郎中令”之下列舉屬官有大夫、郎、謁者,而大夫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只有謁者編制明確,“員七十人”。漢代有大量關于“無員”之郎官數量巨大的描述,可資參考。計算官員數量,不能不考慮這種“無員”的伸縮性。
至于明確不是官吏也不計入官吏數據的,各朝都有,在王朝晚期尤為明顯。明清時期,官員自行聘請的師爺,隨身帶來的長隨,不可能列入官府的計算范圍。他們的身份是私人,但他們的做為在官府。師爺是官員聘請的私人顧問,不能上大堂,不能進簽押房(處理公文的辦公室);長隨是老爺的私人跟班,同官府無關,只為老爺提供私人服務。然而,師爺和長隨,其人雖在官府之外,其事卻無論如何也不屬于“社會”。師爺的正式稱謂是幕友,“掌守令司道督撫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韓振《幕友論》);“長隨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徐棟輯《牧令書》)。算官民比例時,這些人是“民”;看所作所為時,這些人在“官”。論證官民比例,必須考慮這種現實。所以,不加考證,隨意拿史書中的某個數字就來大談古代官民比例,不但有失嚴謹,而且會適得其反。以靠不住的數據去批評某件事情的荒唐,反而會使這件事情更加荒唐。總體來看,中國古代在人員規模上是否存在“小政府”,大有可疑。
古代政府的權力與職能
關于政府的權力,實際涉及兩個緯度,一是政治系統內部的權力配置,二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分割。各種史書,往往對前一種權力配置有較為詳細的記載,而對后一種權力分割幾乎沒有說明。必須指出,國家與社會的對應關系,本是西方政治學形成的分析框架,放在中國不一定合適。也許正是中國傳統中缺乏國家與社會的分野,所以才導致史籍不載二者之間的權力分割。在中國歷史上,政治既是國家事務,也是社會事務,不過是古代不用“社會”這一詞匯罷了。從國家的角度講,政治架構為王朝,而從政治的使命講,王朝的統治指向天下。所以,中國古代的政府,其本質是“全能政府”。所謂全能,不是說政府什么都能干,而是說政府權力無邊界,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從秦始皇到處刻石的記載來看,王朝體制是一種無所不管的體制,“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芝罘刻石語),所謀求的統治效果是一種官方決定的社會秩序,“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碣石刻石語)。此后盡管秦朝很快滅亡,但歷朝歷代承繼了秦朝建立的這種全能體制。
秦朝以后,中國歷史上國家與社會的對立,不是權力分割造成的,而是一統天下造成的。相比而言,西方歷史上國家和社會的對立,是權力兩分造成的。中國的全能政府,只要有可能,其統治就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西方的諸侯林立,城市自治,使王權的觸角受到較多限制。中國的分權,是政治系統的內部分權,如宰相之間的制衡,衙門之間的掣肘,官吏群體之間的派系黨爭等等。西方的分權,是權力主體各行其是,如王室和諸侯、諸侯和自治城市等等。代表西方國家的王權,在其成長過程中未能把社會全部納入自己的麾下,這與中國傳統的王朝等于天下大不相同。
然而,秦始皇的理想并未實現,強大的國家機器榨干了有限的社會資源,王朝因之易主。因此,從漢代開始,各個朝代都在不斷試錯中調整國家的權力和職能,以防止對社會資源的過度汲取而導致王朝崩潰。但是,又未能像西方那樣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劃出一條較為清晰的界線,所以,即便按照西方式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敘事框架,也無法找出與西方類似的對應表現。比如,西方中世紀的自治城市,一旦獲得自治權,無論是國王還是諸侯,都不能再任意干預城市事務。而中國的廣大鄉村,在國家無為而治時,可以形成豪族鄉紳的自治狀態,而國家一旦有強化控制的需要,就可以把自己的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鄉紳無力阻擋。所以,即便中國古代有鄉紳自治,那也是一種不同于歐洲的治理模式。
總體上看,中國古代的政府,不論是允許社會自治還是不允許社會自治,都會把政府權力擴張到極致。天子代天牧民,理論上無所不管,朝廷治理天下,壟斷了一切權力。允許社會自治時,名義權力仍然屬于朝廷,不過是朝廷認為由社會自行運作對王朝更有利而已。所以,即便是公認為社會自治比較發達的時期,“社會”也是不享有法定權力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不是放權于民間,而是施恩于天下。在民與官之間,權力官家獨占,民眾只能服從。官方放水養魚,并不等于分權,而是改善魚的生存條件,以保證能夠滋生出更多更大的魚。明清時期,老百姓都知道一個俗語:“滅門的知府,破家的縣令”。官方不找百姓的麻煩,是官方的明智,而不是說官方沒有這種權力。
所以,中國不能形成“國王不能進”的私域,民眾的財產乃至性命,都屬于朝廷。朝廷一旦需要,可以隨時索取和支配。例如,當朝廷覺得地方豪強有可能妨礙政權運行時,會毫不猶豫地打擊削弱他們的力量。遷徙和移民,不僅是平抑社會資源的手段,更是制服豪強的利器。漢代就曾多次遷徙關東豪族于諸陵邑,明朝山西大槐樹下的移民也有不少是被掃地出門的富戶。據說,明初大富豪沈萬三就是因為太過顯擺,竟然要用自己的錢財替皇帝犒軍,惹得朱元璋大怒,將其發配云南充軍。有人考證沈萬三之事不實,然而,類似的舉措在歷史上卻屢見不鮮。可以說,從權力角度看,中國傳統不是小政府,而是典型的全能政府。
全能政府存在極大的弊端。一旦政府開足馬力,百姓就會疲于奔命。所以,漢代以后,不管信奉何種治國思想,總以不擾民、不生事作為從政的基本原則。顧炎武的《日知錄》專有《省官》一文,稱“省官之故,緣于少事”,并引用晉代荀勖之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由此出發,逐漸形成官府的基本格局:在官僚系統的自身管理上,以控制而非激勵為第一要務;在與社會打交道的“親民官”(即州縣長官)管理上,以消極而非怠工為首要準則。地方官府的基本運行規則是行政司法合一,而且司法重于行政。以致有專家認為,與其說州縣官是以行政兼理司法,還不如說是以司法兼理行政。行政與司法的一個重大差別就是行政積極,司法消極。行政需要主動行為,而司法一概不告不理。這樣一來,即便政府的權力無邊,卻多半不會主動出擊,甚至在制度上形成了慣例,凡是州縣新長官到任,多數要頒發告示,禁止吏員衙役下鄉,以防擾民;一到農忙季節,除非賊命要案,普通民間糾紛,均不受理,停止審案數月(一般是農歷四到七月);民間的田土婚財糾紛,不提倡訴訟解決,以無訟為最高境界;諸如此類,把州縣的“全能”轉變為“不能”,既擁有無所不管的權力,卻采用什么都不管的方式來顯示出權力的存在。有人認為中國古代政府小而不大,從職能角度看,正是由其裁判功能而非建設功能出發的。明清對地方官員的評價標準,很接近于近代所說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這一思想。有贊揚好官的民謠為證:“門子不上堂,書手不進房,皂隸不下鄉。”(蔣廷璧《璞山蔣公政訓》)門子不上堂是指不以私人干涉公務,書手不進房是指處理公文要遵循嚴格的規范程序,皂隸不下鄉是指盡可能防范擾民害民。一旦政府無為,叫做小政府就有其道理。
政府大小的尺度
之所以對古代政府大小產生不同認識,是因為衡量標尺不一樣。用政府職能來衡量,以司法為首要職責,就是小政府無疑。當然,古代政府并不僅僅限于司法,教化民眾,征收賦稅,都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不是過份的橫征暴斂,民眾也不會抗拒。從行政角度看,古代對政府好壞的判斷,以不與民爭利為尺度。所謂不與民爭利,就是政府不事產業。孟子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這句話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就是統治者不能從事經濟活動,“國退民進”。
雖然孟子本意或許不是如此,然而,統治者如果經營產業,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府可以憑借手中的權力,侵占各種利源,把民眾逼仄到難以維持生產的邊緣。歷史上,凡是這個邊界把握較好的王朝,其統治也就較為穩定長久。視這種政府為小政府,當然未嘗不可。在中國歷史上,多數時期政府沒有越過這一界線,或者雖然有所越界但不太嚴重。明顯超越這一邊界的如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等等,其負面作用極大。
換一個角度,如果從政府規模來衡量,中國古代的政府就大之又大。從政府人員的實際數量來看,中國古代并不是需要多少人就用多少人,而是能養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前面說過政府的超編問題,編制數量有嚴格控制,是因為編制內人員“吃財政”。要控制政府的開支,就得壓縮編制數量。然而,古代政府的權力是沒有邊界的。對于當政者來說,從國庫開支可能肉痛,不花國家錢財的事情則十分樂意。這也正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之類的主張往往能夠打動皇帝的原因之一。當政府無錢而不能支付時,權力就會蠢蠢欲動。編外人員之所以那么多,就是因為編外是“自籌經費”,不需要財政列支。
古代政府有一個經久不衰的法寶,沒錢可以給政策,沒政策可以默許,不默許可以視而不見,見到濫施權力可以開恩不罰。于是,權力在謀取官員自身利益上大打擦邊球,各種明的暗的收費捐納花樣百出,由此而把民力用到極限。這種極限以不激起強烈反抗為邊界,用現在語言說就是“考慮到民眾的承受能力”。所以,政府規模通常都會達到不能再大的地步。當然,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這種規模之大也是有客觀限制的,但絕不是小政府。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古代的政府不是做事的,而是養人的。掌握這一點,才可透視到政府大小的實質。
總體上,中國古代的政府,擁有一切權力,卻在社會職能上以消極應對顯示出小政府的某些特征,在不危及統治的地方可以放手而社會自發運行,然而一旦可能對統治產生不利影響,政府本來就有的權力可以迅速運行打壓社會。由此,社會的自治,是以不冒犯政府權威為前提的,而且多數要同政府形成共謀即依附于政府。這種政府,在職能與規模上沒有線性關系。盡管以現代眼光看,政府管事的多少同規模的大小相關,然而在中國古代不是這樣,常見的情況是不論政府管事多少,人數都會擴展到民眾可以承受的上限,并由此而顯示出大政府的各種弊端。表面上,政府規模與職能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個方向,內在邏輯上,這兩個方向的本質高度一致。
由于古代的政府建立在官民對立的基礎上,所以,在政府職能方面,需要收斂到不破壞社會經濟整體運行的范圍,但絕不放棄權力;在政府規模方面,需要把擴張的幅度控制在民眾能夠負擔的范圍,但不會消除擴張的沖動。社會的自治以遵從官家權力為條件,官府的膨脹以不把民眾逼上絕路為條件。二者的平衡,是國權和民生的平衡。在古代的王朝條件下,無法做到國權回歸民權,所以這個矛盾無解,最杰出的統治者,也不過是找到雙方容忍的平衡點而已。辛亥革命后,國權開始向民權回歸,為解決這一問題開始破冰。然而,歷史的遺傳和慣習,依然或隱或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