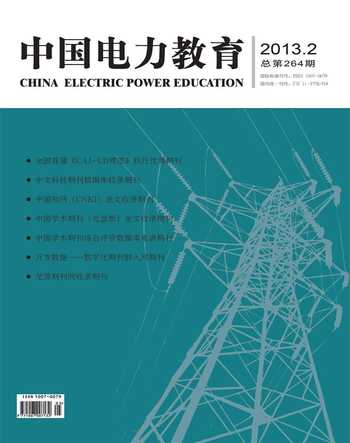傳播學視域下的譯者主體性探究
鄒利民?何芳?何苗
摘要:傳播學在翻譯中的應用為研究譯者主體性提供了新的角度。以《西風頌》兩譯本為例,從傳播學角度討論譯者處于“中介”的位置,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受到各個傳播要素的影響,包括原作者的創(chuàng)作目的、原文傳播目的、譯者的傳播目的、譯文的傳播效果等。
關鍵詞:譯者主體性;傳播學;西風頌
作者簡介:鄒利民(1985-),女,湖南衡陽人,衡陽師范學院外語系,助教;何芳(1975-),女,湖南衡陽人,衡陽師范學院外語系,講師。(湖南 衡陽 421000)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05-0143-02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開始進行譯者主體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德國翻譯理論家沃爾夫拉姆·威爾斯在《翻譯學: 問題與方法》(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一書中指出,過去的研究“迫使翻譯學科研究忽視了翻譯本身的許多特點,特別是有關信息傳遞性質(zhì)的那些特點”。“翻譯是與語言行為和抉擇密切相關的一種語際信息傳遞的特殊方式”。[10]傳播學在翻譯中的應用為研究譯者主體性提供了新的角度。
一、傳播學與譯者主體性
1999年,曾濤在通訊系統(tǒng)模型的啟發(fā)下,建立了翻譯傳播模型:原作者—編碼—文本—譯者—解碼—目標語讀者。[1]拉斯韋爾在1948年提出傳播學中5W傳播模式:who—say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2]呂俊教授在《翻譯學—傳播學的一個特殊領域》中完善了5W模式:誰傳播,傳播什么,通過什么模式傳播,向誰傳播,傳播的目的是什么,傳播在什么場合下進行,傳播的效果如何。[3]這七個因素概括了翻譯活動的過程,并且七個因素互相制約、互相聯(lián)系。翻譯活動是一個整體,參與其中的每個要素都會影響其他因素。
譯者在翻譯這樣一種信息傳播的過程中處于中介地位,既是接受者又是傳播者,既是解碼者又是編碼者。參與傳播的各個要素的地位平等,都對信息的解碼和編碼產(chǎn)生影響。
二、《西風頌》兩譯本中的譯者主體性
傳播學強調(diào)傳播過程各因素的相互影響、相互聯(lián)系。作為原文本讀者,譯者對原文有個人的理解,在對原文本傳播的信息進行解碼的過程中會受到原文作者、原文本以及原文傳播目的等要素的影響。作為譯者,將原文本翻譯成譯本,這是另外一個傳播過程,譯者在這個過程中是作為傳播者進行編碼的。編碼的過程會受到翻譯目的、譯文讀者、翻譯效果等要素的影響。
1.作為解碼者的譯者主體性
(1)原文作者影響下的譯者主體性。譯者對文章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但是譯者對于原作者的喜好、個性、文字風格的揣摩直接影響到譯者能否做到“忠實”地表達原文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原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觀點。
以《西風頌》的兩譯本為例,第一節(jié)中“l(fā)eaves dead”,雪萊筆下的“秋風掃落葉”突出了“西風”對舊世界強大的破壞力。詩中激情澎湃,洋溢著樂觀主義的精神,飽含雪萊對未來和革命必勝的信念。查良錚在翻譯“l(fā)eaves dead”時保留了原文的字面意象,因為“落葉”本身已經(jīng)是沒有生命的,腐朽、沒落,詩人借它來比喻英國的反動階級。這是一個穩(wěn)定意象,在東西方文化中人們都有這一心理認同,無須轉(zhuǎn)換。而江楓將這一意象“l(fā)eaves dead”轉(zhuǎn)換為“萬木蕭疏”,給人們營造的是一種秋天的肅殺景象,意境是悲涼的。縱然“萬木蕭疏”也是“秋風掃落葉”的一種結(jié)果,但雪萊筆下的“秋風掃落葉”是突出了“西風”對舊世界的強大的破壞力,表達了詩人對革命到來的一種熱切的渴望之情而不是一種悲涼的心境。此處查良錚翻譯較“忠實”地傳達了原文的信息。
(2)原文傳播目的影響下的譯者主體性。原作者的創(chuàng)作目的直接影響譯者的翻譯選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首先應該了解原文的創(chuàng)作目的,這樣才能站在原作者的立場上忠實地再現(xiàn)原文表達的觀點和感情。《西風頌》全詩氣勢磅礴,目的在于激發(fā)革命者反抗黑暗、向往光明的激情。
《西風頌》中的“wild west wind”和“Wild Spirit”,江楓分別譯成“狂野的西風”和“不羈的精靈”,查良錚則譯成“狂暴的西風”和“不羈的精靈阿”都表達出了原文的語氣和強烈的情感。對于“My spirit! Be thou me,impetuous one”,查良錚譯成“奮勇者呵,讓我們合一”,語言簡練,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而江楓的譯本“竟是我的魂魄,我能成為剽悍的你”,則感情色彩相對弱一些。1958年查良錚在翻譯《西風頌》時的境遇與雪萊創(chuàng)作原詩的背景十分相似,在翻譯本詩的過程中譯者能感同身受地把握住原文的傳播目的,與作者達到共鳴。
(3)原文本影響下的譯者主體性。原文本是譯者翻譯的根本,也是譯者翻譯的源泉。從翻譯操作層面來看,譯者對文本的解讀是一個傾聽文本聲音,并和文本不斷對話的過程。[4]《西風頌》是一首典型的舊體詩,各有五小段,意思相互連貫。雪萊在他的十四行詩中運用了抑揚格,三行一旋廻,韻式是ABA BCB CDC DED EE。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是完全自由的,總是會受到這種或那種因素的限制。譯者的受動性首先來自于原作者。一個好的譯者必須把原文放在最首要位置。江楓和查良錚在翻譯《西風頌》時精挑細選詞語力爭符合原詩的韻式。譯文和原韻都較為接近,表現(xiàn)了原詩的激情和氣勢,頓數(shù)、字數(shù)大致相等,詩行整齊。節(jié)奏起伏有效,緊隨原詩,時而激昂熱烈,時而淺唱低吟。
2.作為編碼者的譯者主體性
(1)譯文讀者影響下的譯者主體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除了受到原作者、原文本的影響外,譯文的讀者也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因素。“翻譯的最終目的是要讓讀者接受譯作。這是翻譯的最后環(huán)節(jié),也是翻譯活動能被接受的關鍵。”[5]“比如同樣一篇文章,譯文是供學者研究還是供一般讀者欣賞,采用的方法就有所不同,貼近原文的直譯更受研究者的青睞,而語言順暢的意譯更受一般讀者的歡迎。”[3]42
江楓認為雪萊的抒情詩形象生動、語言清新、音韻優(yōu)美、感情真摯而充沛,閃耀著崇高的思想光輝。在進行詩歌翻譯時,江楓認為譯詩應該力求形神皆似,形似而后神似。例如譯文中的語氣詞翻譯和顏色詞翻譯,江楓仔細斟酌詞語意義,賦予詞語以原詩的抒情色彩和情緒;同時四字結(jié)構(gòu)的使用也使行文鏗鏘有力。此外,對句式的變換使用使譯作內(nèi)容豐富,排比的運用也恰到好處的再現(xiàn)了原詩的意象,如“不羈的精靈”、“四合的夜幕”等。江譯的《西風頌》再現(xiàn)了原詩的風格和情緒,具有濃厚的詩意和流暢的藝術(shù)美。
在查良錚所處的時代,國內(nèi)政治動蕩不安,他自己也生活在人生的谷底。為了鼓勵受苦受難的同胞,他把詩歌當做武器直抒胸臆,他選擇強有力的西風形象去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和改革動力,因此他的譯本用詞充滿了力量。在簡短的句式、平實而有感染力的詞語中,讀者能感受到西風狂掃落葉的氣勢和力量。譯者善用短小的詞語組合增強譯詩的節(jié)奏感,如“你無形,但枯死的落葉被你橫掃”,“黑暗的冬床上,它們就躺在那里/像是墓中的死穴,冰冷,深藏,低賤”,“這被歲月的重軛所制服的生命/原是和你一樣:驕傲、輕捷而不馴”。譯詩第二部分的第一節(jié),“沒入你的急流,當高空一片混亂/流云象大地的枯葉一樣被撕扯/脫離天空和海洋的糾纏的枝干”,一系列動詞的使用使讀者仿佛身臨其境,仿佛親眼看到雪萊筆下的西風是如何改造天地萬物,破壞而又創(chuàng)造著這個世界的。最后一部分中,“呵,但愿你給予我/狂暴的精神!奮勇者呵,讓我們合一”,流暢自然的語言有力地表達了作者希望擁有勇者的力量以奮起反抗現(xiàn)實的壓迫。由此可見,不同譯者預設的讀者不同,決定了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影響到了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
(2)譯文傳播目的影響下的譯者主體性。目的論指出,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是有目的的,翻譯也是如此。[6]翻譯的目的直接影響著翻譯的過程和翻譯的文本。目的不同,同一個文本、不同的譯者也會譯出不同的版本。在傳播學中,傳播的目的是傳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接影響到翻譯的效果,因此在傳播學視角下研究譯者的主體性,必然要分析傳播目的對傳播者的影響。例如:
Even from the dim verge.
Of the horizon to the zenith' sheight,
The locks of the approaching storm.
查譯:從天穹最遙遠而模糊的邊沿直抵九霄的中天,到處都在搖曳,欲來雷雨的卷發(fā)(“直抵”、“搖曳”、“欲來雷雨”用詞充滿了力量)。[8]
江譯:從那茫茫地平線陰暗的邊緣,直到蒼穹的絕頂,到處散布著迫切的暴風雨飄搖翻騰的發(fā)卷(增加了“飄搖翻騰”的修飾)。[7]
查良錚翻譯《西風頌》是為了鼓勵受苦受難的同胞,他把詩歌當做武器直抒胸臆,因此他的譯本用詞充滿了力量。如“狂暴”、“橫掃”、“紛紛逃避”等詞都生動的表達了這種情感。江楓在翻譯《西風頌》時,文學性多過政治性,所以他的措辭會更加優(yōu)美和講究。如“枯萎的思緒”、“播送宇宙”、“驅(qū)遣落葉催促新的生命”、“颮出”、“蔫黃,魆黑,蒼白,潮紅”等。
(3)翻譯效果影響下的譯者主體性。傳播效果是傳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翻譯作為文化傳播的一種特殊形式,讀者能否接受譯本,譯本是否能夠達到相應的傳播效果,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傳播效果位于翻譯傳播的最后階段,它是諸多傳播要素相互作用的集合,是一切翻譯傳播活動的試金石。”[9]
江楓用典雅、準確、傳神的詞語傳達出原文的思想內(nèi)容,譯出了許多佳句。“蔫黃,魆黑,蒼白,潮紅”(yellow,and black,and pale,and hectic red),色彩鮮明,對比強烈;此外,許多詞語的翻譯,準確而又富于詩意,如“漂流奔瀉”(leave are shed),“在你清虛的波濤表面”(on the blue surface of thine airy surge),“蒼穹的絕頂”(the zenithsheight)等。
查良錚準確把握了原詩的精神,所譯的作品準確而貼切,較好地傳達了原作的革命精神。在這首詩里,他沒有刻意去追求文采藻飾,也沒有一點俗膩,讀來平直順暢,嚴謹而又不失自然。查良錚翻譯的《西風頌》的最大特點是貼切、準確、順暢。
傳播效果是翻譯傳播的最后階段,在譯者追求不同的翻譯效果的過程中,譯者具體一定的創(chuàng)造性。
三、結(jié)束語
翻譯就是一種跨文化的傳播,傳播過程的各個參與要素都對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原作者的創(chuàng)作目的、原文傳播目的、譯者的傳播目的、譯文的傳播效果等。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該全面考慮各個因素,挖掘原文深層次的含義,體會原文作者的寫作目的,充分發(fā)揮譯者的能動作用,從而使譯文能夠全面、真實地傳達原文的信息。
參考文獻:
[1]曾濤.現(xiàn)代信息傳遞理論與翻譯實踐[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1999,15(3):103.
[2]路春艷,張洪忠.大眾傳播學教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
[3]呂俊.翻譯學——傳播學的一個特殊領域[J].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1997,(2).
[4]劉華.對譯者主體性及其制約因素的思考[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8(4):126-127.
[5]仲偉和,周靜.譯者的極限與底線[J].中國科技翻譯,2006,(1):35-37.
[6]趙建華.《老殘游記》兩譯本看譯者主體性[D].蘭州:蘭州大學,
2010:16-17.
[7]江楓.雪萊詩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8]查良錚.雪萊抒情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9]孟偉根.關于建立翻譯傳播學理論的構(gòu)想[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4(2):86-90.
[10] 沃爾夫拉姆·威爾斯.翻譯學:問題與方法[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孫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