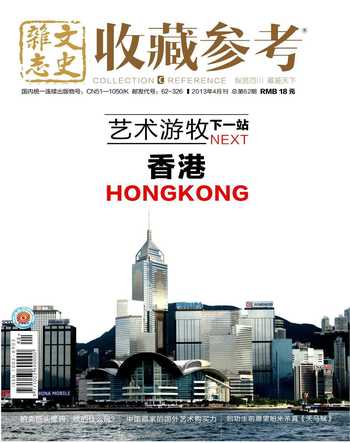如是我讀書畫家沈亮
許步書
讀書如讀人,因人不同,感悟不一。
案頭,擺著一位比我年長的朋友、著名書畫家沈亮的書畫結集:
《沈亮山水畫集》(福建美術出版社,1994年5月);
《沈亮花鳥畫集》(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1年2月);
《沈亮書法作品集》(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2年2月);
《中國山水畫導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年3月);
《芳蹤覓韻——沈亮四季百花圖譜》(時代出版社,2012年4月)。
我的目光時時落在這些書本上,已經翻閱好幾天了,卻又迷戀得不愿離開。我企望走近她們、親近她們,可總有些不安。這些結集,像夢中的麗人只能用感覺和心智去撫摸。后來,我終于想到了兩個字,也許能概括出畫家近七十年來癡迷于藝術創作的精神。那就是“至誠”。
這位出生于書香門第的福州師范高材生,藝術成就和他的勤奮治學、至誠奉獻分不開的。他和書法家林健同是當代著名畫家陳子奮的“入室弟子”,經歷一定的人生磨難和繁重的藝術創作勞動,是位辛勤耕耘的美術園丁。他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從事兒童畫的啟蒙輔導工作,輔導的學生畫作漂洋過海,參加西班牙、希臘、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展出,榮獲過國家教委、國家文化部等六家授予的“全國校外教育先進工作者”嘉獎。《福建日報》、《福建電視臺》等多家媒體,為他的至誠于中國畫藝術創作做過專題報導。
站在“至誠奉獻”藝術長河前沿的沈亮,沒有喧嘩、也沒有高調。在這五部作品里,我時常感覺到他像蜜蜂那樣,默默地采蜜、默默地奉獻,給受眾以最美最甜的精神食糧。
淡泊的沈亮,然而他的心里卻沸騰著滿腔的生活激情,手里的那枝久經磨礪的筆,時時撥動出時代的主旋律,歌頌大千世界、歌頌祖國大好山河、歌頌新時代新生活。他不斷地耕作,至今已有上萬幅作品被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鐘愛者、被各地美術館、博物館收藏。這種“至誠”奉獻藝術的精神,令人敬佩。
沈亮多才多藝,詩、書、畫項項優秀,山水、人物、花
鳥,科科投入,樣樣出精品。我與他神交多年。當我在任海峽姐妹雜志社副總編時,就欣賞過他那些筆墨恣肆、敷彩沉穩、結體奇倔的書畫作品。后來,又陸續在報刊、展廳讀到他的一批花鳥、山水畫;再后來,又一連收到他出版的書畫集。他的多產,不得不讓我佩服他的智慧和勤奮。在我的印象里,不少畫家和藝術的相遇往往帶些“宿命論”的緣分。沈亮在這方面沒有傳奇的情節,但有一點他從小就沐浴在良好的藝術氛圍中。父親是位書畫愛好者,與著名畫家陳子奮交友深。所以,耳濡目染的大都與中國畫藝術有關的東西。潛移默化,小學時沈亮的畫作就在市里展出,一
鳴驚人,受到專家的好評。從此,在中學、在大學,他像餓慌牛犢,一頭扎進藝術天地,貪婪地汲取中西文化藝術,豐富了自己的藝術語言,形成了個性鮮明的繪畫風格。
應該說,是繪畫藝術本身誘惑致使沈亮至誠地投身于藝術創作,并時時撞擊出創作的靈感,使得有許多人的掌聲和鮮花獻給他。但與當代一些年輕的畫家比,沈亮這一代畫家可能更多地是付出了常人難能理解的辛苦,甚至是寶貴的青春時光。藝術畢竟是誘人的,問題在于在當今那有點急功近利的浮躁畫風中,你要以什么態度去選擇,或者說以什么精神去對付。
沈亮對這個問題回答得很完美。他對生活是熱愛的,對藝術是投入的。但他不會輕易地放棄任何一點攪亂他進入藝術的意象。他始終擁抱著一種心智和熱情:繼承與創新。
正如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著名美術史論家王伯敏先生稱贊他:
“沈亮的繪畫,從構思到落筆用墨,都在圖新求變,別具風貌。‘蒼茫為其繪畫藝術的特色,明顯地體現在他的墨色上。看他用墨,似乎心無定法,卻又是規矩法度在其中。所以他在繪畫中的‘蒼茫是極為自然的。沈亮繪畫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大筆飽蘸水墨,由遠而近,畫出山川的大氣……”
我以為王教授評點極為中肯。因為,雖然沈亮的筆墨是傳統的,但是他沒有隨便放棄求新的語言方陣。在他作書繪畫美學領域中,追求的是詩情和畫意的境界。正是如此,所有高雅、大氣、雄闊、優美、亮麗,都能夠進入他的視野,從而被他的繪畫所駕馭。
其實,中國繪畫傳統,向來講究氣、韻、勢。所謂氣韻的生動,包含著“勢”,畫出的山川江河、花草樹木、飛禽走獸才能生動、秀麗。其實,這也是畫家的生命氣象和學識的表現。沈亮在這方面做得很出色,這無疑來自畫家對中國畫史論的研究,來自對西畫的學習和探索,來自對大自然的熱愛和感受。
無疑,沈亮已獲得了自己對藝術生活的一種詩意的感悟。他為長城放歌、為泰山賦詩、為大自然的花花草草、為古城的一磚一塔、為歷史的蹤跡、為現代化的新面貌,釋放心中的贊歌和美的旋律。似乎他所有的生活征途上,都可以在他的心海里繪下一幅幅藝術燈塔。或許,這就是沈亮的創作靈感和記憶。這種靈感時常在新與舊、繼承和創新中夾雜著個性很濃的“蒼茫”味。這便是沈亮國畫的一個重要特征。他的許多花鳥畫往往韻多于氣,氣多于勢。他對作品的要求以及對市場的走勢,不會有太多的追問和講究。新時期文化藝術的大發展,使得一些中青年人加入美術行列。而沈亮是在他的藝術造詣成熟期與時俱進,這多少意味著他這一代畫家有一種時勢造名家的環境支撐。我們高興地看到了他的藝術影響力,為自己的表述方式找到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天地。
正如福建省師大美術系教授、著名山水畫家楊啟輿先生贊譽沈亮的山水畫創作:
“……學古而不泥于古,師造化而不拘于造化。……其畫風,融匯中西,技藝嫻熟,執著于抒寫胸中意趣,落筆揮灑淋漓,清新華滋,獨成自家面目。”
啟輿先生那經典般的論述,清晰地再現了沈亮的國畫作品所處的一種典型的畫風位置,能夠在畫壇保持著自己的統一框架和一席之地。沈亮的成功在于他明白自己的創作形式,明白自己的藝術感覺,明白自己的美學追求。他已經不會在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所謂“時髦畫風”沖擊下左右搖擺,走出了自己的畫路,成就了屬于自己的繪畫語言和線條秩序。
沈亮國畫創作,在當代畫壇獨領風騷的又一個支撐,是他的書法藝術。有人說過詩是畫作的靈魂,書法是畫作的骨架,畫作才是形象的東西。可見書法在國畫中的重要性。福建省美協原主席、著名書法家丁仃稱贊:“沈亮的山水畫得益于筆墨的熔鑄。他早年注重書法的歷練,即‘引書入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畫是講究筆墨的,他以書法來滋養自己的筆墨,提升了繪畫語言的審美含量,終于有了自己面目的山水畫作品問世。”
省委常委、秘書長、文人書畫家葉雙瑜在祝賀沈亮《芳蹤覓韻》書畫集出版時,題詞“得山水清氣,極天地大觀”,更道出了畫家作品的主流本質。
可見,大家很了解沈亮,評論他的作品時都能一針見質。的確,沈亮把自己筆下的作品當作只是沈亮的面目,連書法也只是自己的面目。從表面上看,多少有些矯情的意味。但或許因為在他創作時筆下流露的全是他自己心中激蕩的東西,放飛的是自己心中的感覺和智慧。然而,正是這些東西才觸動了讀者。
在《沈亮書法作品集》后記中,我讀到了這樣的一段經驗之談:
“……我們提倡學習書法,應該打開思維之窗盡可能更多地去汲取各種經典筆法的養料,而不是盯著一兩家,作繭自縛。我在編寫這本教材中也深深體會到,各種書體的技法都不是固定不變的,歷代都有創新的書法出現,才演繹成目前面貌的書法大觀。”
這似乎就是沈亮的書法創作心態。
他的書法似漢簡而非漢簡,古樸厚重,靈動鮮亮,用筆的輕重頓挫,用墨的干濕濃淡,都把握得恰如其分,說明書家的創作心態好,有自己的“面目”。有這樣書法“面目”題款在有自己“面目”的畫作上,當然會成為畫壇上一道亮麗風景。我以為沈亮的藝術作品“面目”是“蒼茫、豐厚、靈動”。我相信在同藝術溝通中,沈亮有自己的“面目”;在同讀者溝通中,留有自己的“面目”;在與未來的溝通中,還將留下自己的“面目”。
蒼茫、豐厚、靈動的面目,是沈亮對于藝術創作靈魂的堅守。
如是我讀沈亮。
作者:作家、美術評論家、編審、《海峽姐妹》雜志社原副總編,現為福建《書畫藝苑》主編、《收藏參考》雜志社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