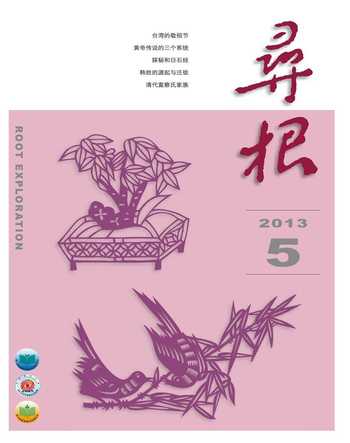從《福熙自述》透視民國時期徽商的命運
何建木
關于徽州商人的研究,就徽商群體而言,學術界已取得深入進展,但就徽商個案(生活史)的研究則少之又少。
2004年年底,筆者為撰寫博士論文到上海圖書館譜牒部查閱資料,意外發現了一冊不分卷的民國38年(1949年)“詹福綏堂”鈔本《慶源詹氏家譜》,在此譜卷最末附有一篇十分珍貴的3000字自傳體人物傳記:《福熙自述》。此傳記講述了作者一生的創業史尤其是抗日戰爭之前的坎坷經歷,內容包括家庭生活的辛酸、創業的艱難、收獲的喜悅以及人事的更迭與浮沉。本文即以《福熙自述》為中心闡述以詹福熙(1887 1970)為代表的民國時期上海徽商的經營及其生活世界。
學徒生涯甘受苦
1887年3月13日,詹福熙出生于徽州府婺源縣(今婺源東北部)的段莘鄉慶源村,為婺源詹氏第40世傳人。
徽商在上海一帶從事商業經營的歷史,可上溯至明代中后期。道光年問上海開埠后,旅滬徽商人數更盛,經營行當更趨多元化,但是除少數有名的巨商大賈外,在上海創業的徽商,其經營狀況和規模均屬一般。徽州婺源人在上海的主要經營行當是茶業、木業、墨業,兼其他百貨業。慶源詹福熙出生時其父詹良盛因身在崇明縣,未曾見到這位新生兒,且出生甫四月,詹良盛即因病逝世于崇明縣邦鎮(今浜鎮)四盛南貨店。該店系其祖父詹廷蛟(1831~1869)與族人合伙開設的小百貨商店。
1898年,詹福熙十二歲,離開慶源,外出謀生。他先走105華里山路后,翻過五龍山,到達當時重要的商業市鎮屯溪,再轉乘客船,在悶艙里沿著新安江水路過了七天七夜后到達淳安、杭州;然后再轉道到上海。晚清民國時期,很多婺源的茶商、墨商及其他各種小生意人在十里洋場開展經營,由于徽商的經營具有家族性和同鄉特征,所以詹福熙得以通過親戚和同鄉關系,先由其姑父的堂侄汪再喜介紹到同順昌氈毯店當半年學徒,然后由同鄉余五坤介紹到生元絲莊當學徒而后成為店員,一晃就是十年。
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普遍缺乏職業技術教育,因此學徒制對于民生有著重要意義:一是減輕貧困家庭的經濟負擔;二是為青少年培訓得以謀生的職業能力。《福熙自述》中并沒有指明其學徒生活的具體情況,但在其晚年曾詳細向其三子詹永年敘述:除了要跟老板跑三江六碼頭,要照看店里生意外,“還要做家務——倒尿壺、生煤球爐、幫老板娘抱孩子等”。可見,其待遇工資、生活狀況并不理想。有諸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表明學徒學藝年限一般行業都執行“三年為滿,出一進一”的條規,不過詹福熙似乎超出了三年的年限,其年限競長達十年,不過前段是學徒,后段正式成為店員。
1898~1906年,詹福熙在擔任學徒和店員的期間,只在1904年回過一趟婺源老家,完成了訂婚大事。到1906年,詹福熙方才“回家迎娶”,在老家逗留了很短時間,就“事畢返申”。
據現代著名學者胡適在《胡適口述自傳》中稱:“我們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歲時便到城市里去學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長輩或親戚的店鋪里當學徒。在歷時三年的學徒期間,他們是沒有薪金的;其后則稍有報酬。直至學徒(和實習)期滿,至二十一二歲時,他們可以享有帶薪婚假三個月,還鄉結婚。婚假期滿,他們又只身返回原來店鋪,繼續經商。自此以后,他們每三年便有三個月的帶薪假期,返鄉探親。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話,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說,一對夫婦的婚后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一輩子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者三年半。”以胡適的口述文字證諸徽商詹福熙的婚姻生活,十分相符。
營商時代多變動
1906年,詹福熙從婺源婚假回上海,其家庭及其所服務的店業經歷了諸多變故,不得不另謀出路。同年詹福熙脫離絲綢絨線行當,轉而進入中西藥業,此后從事藥業經營達20年之久。晚清以來,隨著近代社會的變遷、人口流動的加強、職業分類的復雜化,從事商業的人際關系也越發復雜:師生、商界朋友、中外朋友、兄弟姐妹、鄉親等復雜關系,均需從商者加以調和處理。此前,詹福熙的業師周玉麟,為人寬厚,對他照顧有加,也由于詹福熙生性老實本分、能吃苦、肯學習,因此對生意精熟,待人接物老道,還精通算盤,深得業師器重。
不過,從詹福熙1906~1910年在中西大藥房開封支店擔任外跑的經營生涯來看,并沒有什么精彩之處。1910年詹福熙離開開封請假回鄉時,家庭再次遭遇巨大變故:首先是其長兄詹渙渫已離開中西大藥房,在里成瓜街開了問藥店(里成瓜街、外成瓜街的路名,如今依然存在,當時是上海藥業集散地,清光緒年問在此設有參業公所,頗為有名);其次是業師周玉麟已去世;再次是1910年8月13日,母親王氏去世,年僅五十三歲,去世時兩個兒子因為在滬經營藥店而未能返回婺源親自送柩出殯。
1910~1913年,是詹福熙在開封擔任“華英藥房”幫辦(相當于今副經理)的階段。
1914年,開封華英藥房因遭火災而倒閉,同年詹福熙也被項松茂調回五洲大藥房上海總行,1915年升任五洲大藥房延安中路分店經理。
1924年,詹福熙因為要幫朋友下里彌吉的忙,離開五洲大藥房,改行從事照相器材生意,擔任千代洋行買辦。《福熙自述》第七段簡要闡述了白創生意的這一重要階段:“余與項君同事將近十載,感情甚洽。后因日友下里彌吉系業照相材料,管理乏人,來與余商,托謀管理之人,余允其緩緩代訪適當人選,惟下里每日來催,不得已,余允暫幫其忙,當將詳情商之項君,蒙允余請,當將五洲分莊主任辭去,專辦千代洋行照相材料。不十年,而經營業務已遍全中國矣。不幸,“九一八事變”發生,因國際關系,不得不脫離千代而自謀,即創設華昌,專營照相材料,于勞合路白克路恒清里,專做批發。一年后,設門市部于山東近南京路口。民國廿六年全部遷至南京東路四七一號,經營至民國卅八年,將店務交大兒永匡管理。1915~1924年,因為總經理項松茂的賞識和器重,詹福熙在五洲大藥房獲得經營的大發展,開啟了創業過程中的第一次輝煌時代。當時的藥店不同于現在的藥店,它在同一柜臺還可以經營其他貨色,五洲大藥房延安中路分店也賣照相器材、膠卷、卡紙、顯影藥水等。因為兼營照相器材的緣故,詹福熙認識了日本人、上海南京路“千代洋行”老板下里彌吉。以進出口業務為主的千代洋行創始于1910年,是上海最早經營照相機的洋行,也是經營照相器材最著名的洋行。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該年底,詹福熙離開千代洋行,自創“華昌照相材料行”,寄寓中華民族昌盛之意,地址在南京東路山東路口,成為當時中國最早自營照相器材的商號之一。本來上海許多照相器材都來自日本,但這時候詹福熙寧可少賺點錢、麻煩點,都進德國、英國、美國的照相材料而拒絕進日貨,體現了一個愛國商人應有的民族氣節。
1934年4月,華昌照相材料行在漢口成立分店后,由詹福熙的族侄、愛國商人詹勵吾(1904~1982)擔任經理,不久又在長沙、南昌開設分行,由詹勵吾弟弟詹新吾等擔任經理。鑒于“在偌大的一個華中區,競沒有一個定期的攝影讀物,來溝通攝影消息,交換攝影知識;使初習攝影者得些自學的經驗,使一般攝影作家也得些觀摩之益”,1935年10月,華昌照相材料行漢口分店出版發行了攝影雜志《華昌攝影月刊》,后改名《華昌影刊》,至1937年6月出刊21期,16開本,用道林紙印刷。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后,上海被日軍占領,長江航運中斷,華昌照相材料行的貨運通道變得十分困難,生意受到一定影響。后經由著名愛國商人、婺源人孫友樵介紹、安排和幫助,詹福熙發現了從臨安、于潛、昌化、昱嶺關、三陽坑、歙縣到達屯溪的徽杭古道比較便利于貨物運輸,于是通過這條徽杭古驛道,把貨物從上海經杭州運往屯溪,再從屯溪運往內地各大城市的華昌分店。為了便利于從上海發往屯溪的貨物中轉和資金結算,詹福熙買下了屯溪市民族路41號店鋪,開設了“祥大布店”,其商業經營范圍得到進一步拓展。
在詹福熙的苦心經營下,上海華昌照相材料行生意日隆,成為當時上海最著名的批零兼營照相器材商店,抗日戰爭期間在南京、武漢、南昌、成都、重慶、長沙、昆明等地陸續開設分店。此外,抗日戰爭勝利后,詹福熙還以其三個兒子命名,在上海西藏北路開封路口、熱河路、老城隍廟三牌樓分別開設了永康、永茂、永炎等三家典當行,在江西樂平還開設有天元布行,商業經營范圍進一步擴大。
1947年,上海華昌照相材料行從山東路近南京路口遷至南京路471號,業務獲得更大發展。1949年,詹福熙決定退休,將店務交給大兒子詹永匡。新中國成立后,詹福熙從上海搬到杭州安度晚年,直至去世。
縱觀民國時期詹福熙的商業經營歷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階段:一是在上海五洲大藥房擔任延安中路分店經理,二是自己創辦華昌照相器材行。這是其創業生涯中的兩個輝煌時期,成就了一位傳統愛國商人在時代的夾縫里如何創造商業財富的傳奇。
傳統與現代相交錯
舉族經商、熱心公益、熱愛學習、一心向善、醉心風水、纂修家譜、精通岐黃等特點,都體現了徽州商業氛圍下的傳統文化,即便是在中國傳統近現代之交僑寓并定居上海的徽商,詹福熙還是保留有明清時期以來徽商應有的傳統品質,依然帶有區域人群“婺源朝奉”的某些特點。
第一,詹福熙的社會關系網絡主要來自同鄉關系,帶有徽州區域社會濃厚的人文特征,這一點強烈影響著詹福熙一生的為人行事。《福熙自述》在詳盡闡述了與項松茂的商業交往和自創華昌照相材料行的經歷后,最末尾一段就一句話:“上述者,希我后裔永志勿忘。”至此,《福熙自述》戛然而止。詹福熙希望其子孫能夠銘記他兒時的家庭苦難、學徒時代的甘苦、創業時期的艱難,也希望能夠記住婺源同鄉的真摯友誼。
通觀詹福熙的交際人群,有一大部分是其同鄉婺源商人,比如當學徒的介紹人和業師都是婺源同鄉,而在五洲大藥房擔任幫辦和經理期間,幸運地遇到了三位在他看來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益友”,也都是婺源人:一是回峰汪惠成,二是上溪頭程質文,三是理田李鑒賢。這三個人所在村落與詹福熙的家鄉慶源村距離都甚近。汪惠成與程質文均精通堪輿和岐黃術,這正是徽州區域社會最突出的人文特征。程質文曾經擔任詹福熙華昌照相材料行重慶支店經理,精通堪輿術,詹福熙慶源老家的宅居“福綏堂”、兩位妻子的墓室選址,均為程質文所勘定;李鑒賢字味齋,與詹福熙同時期經營鐘表業、百貨業,新中國成立前夕與同鄉詹勵吾等人一起遷居僑寓巴西,后來成為熱心公益事業的佛教居士和慈善人士,精通醫術。這說明,詹福熙沐浴在徽州區域社會濃厚的人文氛圍之中,尤其重視傳統醫學和風水術。
第二,熱心于家鄉和僑寓地的各種公益慈善事業。由于明清以來僑寓各大中城市的徽商人數眾多,因此在徽商僑寓地大都設有徽州義冢、婺源義阡等,用以安妥那些未能回鄉的亡魂,上海徽寧思恭堂即為上海最重要的徽州善堂。民國14年(1925年)《婺源縣志》末尾的《捐助修志銜名》記載有“北四區詹福熙捐洋五十元”。可見,詹福熙雖然身在上海,依然心系婺源。這種對于故鄉執著的眷戀,是徽州區域社會另一個重要的人文特征。
抗日戰爭時期,兵荒馬亂,詹福熙就經常接濟有困難的同鄉、親友和客戶,按照他自己的話講,叫做“共渡國難”。當時在僑寓地的徽商之間,與其他業界的徽州人之間,都有所來往、互相接濟,這種人際往來是維系僑寓地桑梓鄉情的最佳途徑。
第三,重視傳統教育。徽商最重要的特質是“賈而好儒”,這一點學術界已經取得共識。詹福熙在經商之余,十分熱衷于傳統儒學教育。正如永年介紹,“父親生平沒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喜歡喝點酒。三五同好邀在一起觥籌交錯,或交流貿易心得,或暢談故里舊情,相談甚歡…一因為吃過沒文化的苦,父親和所有徽商一樣,都很重視教育,這是他們的一大傳統…一像所有徽商一樣,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小時候我們除了學文化,也要上柜臺,學待人接物,學做生意。”正是因為重視傳統教育的緣故,1946年,詹福熙曾經在屯溪隆阜雙渠口買下一處房地產,捐給紫陽小學作為校址(今黃山市屯溪區隆阜小學,2010年改名為戴震小學),該學校生源多為農村貧困學生。
當然,除了具有徽商的傳統特質外,詹福熙也體現了近代以來徽商的若干轉型。徽商之間的地緣和血緣關系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牢固,同時這種牢固的商幫內部結合反過來又強化了徽州區域社會的血緣和地緣關系。隨著近代以來各種社會關系的調整,徽州商幫這種性質有所改變,表現為血緣和地緣關系是明清直至民國時期徽商經營中一直保存的重要特點,同時隨著近代社會的變遷,徽商的社會網絡也有所拓展,這一點在詹福熙和俞仁耀的商業生涯中都可找到印證,這種拓展主要是突破了地緣和血緣的限制,而從更多層面上尋求適合、有助于其自身商業經營的社會資源。比如,促成詹福熙人生第一次輝煌的商業巨子項松茂,并非來自徽州而是來自寧波商幫,這就說明近代以來,隨著職業經理人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徽商連同其他商幫一起,在職業選擇和商業經營上已突破地域限制。再以木商俞仁耀收納的幾個學徒為例,其中孫開濟、王茂林、孫開趣、王鑒湖、俞開創等人是婺源宗親或戚友,而吳烈華為浙江平湖人,錢云清為江蘇無錫人,戴昌龍則為浙江寧波人。
近代以來徽商社會網絡拓展的另外一個表現在于,隨著時代的推進,其婚姻范圍已經更進一步突破了狹隘籍貫地域。詹福熙娶妻“莘源汪小棠公之長女閏諱湶好”,而繼娶側室則為“江蘇吳縣曹寶壽公之女閨諱多智”,“繼娶三室,浙江鎮海縣柴橋鎮曹謂勛公之女閨諱福智,生于光緒乙巳正月廿七戌時,生子一,日培集。繼子培芳、培芬。培芳生于民國癸丑八月十七卯時,娶回峰汪氏。培芬生于民國壬戌正月十五子時,娶淇源王氏。培集生于民國丙子三月初丑申時。”從這一點看來,詹福熙及其兒子的婚姻范圍徘徊于徽州家鄉與僑寓地之間。時代的推進導致徽商及其家庭社會網絡的拓展,這是現代化進程在人際關系網絡上所表現出來的重要特征。
(題圖:晨嵐中的慶源春景)
作者單位:上海市浦東新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