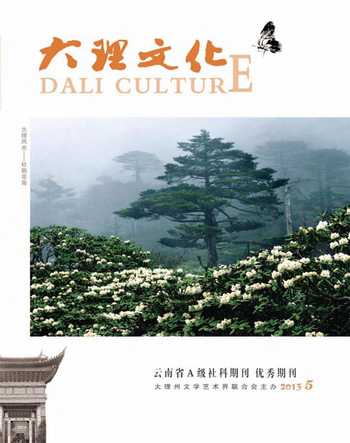關于生產隊的那些記憶
李超
生產隊解散已有三十年之久的今天。作為曾經在生產隊勞動和生活過的人,當時的青少年如今已經成為中老年人,當時的中年人如今已經成為耄耋老人,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已經逝去。
生產隊,是我步入社會的第一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舞臺。是影響我一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一個曾經讓我希望離開的地方,一個離開后又讓我時常想起的地方!在那里,我親眼目睹了鄉親們在計劃經濟的桎梏中頑強生存、希望改善生產生活現狀的種種努力,也親身品嘗到了那個年代農民的種種艱辛。從上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存在了長達二十多年之久。作為那個年代農村經濟的基層核算單位,當時全國數億農民全部生活于其中,他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都與其息息相關。
我所在的生產隊,是原大理縣城郊公社龍龕大隊第二生產隊,今大理市大理鎮龍龕村委會第二村民小組。生產隊所在的下龍龕下登村,是一個白族聚居的村落。白族是一個較早接受漢文化熏陶的少數民族,重視教育、善于學習、胸襟開闊、精于耕作、生活節儉、講究衛生,還特別重視住房,與各民族相處也非常融洽。我們村座落于大理古城東邊的洱海之濱,土地肥沃、水利方便,農業生產條件優越。我出生的1957年10月,正好處于農業生產高級合作社階段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醞釀階段。和那個年代的許多小孩一樣,我從十歲左右就在讀書之余開始為生產隊放馬、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從三個工分開始為家里掙工分。我于1972年9月考上大理一中離開生產隊。1974年7月高中畢業回生產隊。1978年3月考上云南大學再次離開生產隊。在回鄉期間,我開始代過課,次年起擔任生產隊會計,過了一年又改任生產隊政治指導員。應該說,我經歷了生產隊的大部分階段,但是。對生產隊有一個比較全面了解的還是我高中畢業至上大學的那個時期
我們生產隊,當時有四十多戶人家。二百二十人左右,全勞力占人口的一半左右。老人、小孩也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輕微的集體生產勞動。這部分人當時稱之為半勞力。真正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只有那些十歲以下的小孩和六十歲以上真的干不動農活的老人。在四十多戶人家中,沾親帶故的比較多。有的同屬一個家族;有的在解放初還是一家,后來弟兄分家變成幾戶;還有的有這樣那樣的親戚關系。但是,由家族把持生產隊的現象并沒有發生。在四十多戶人家中,家庭成分為地主的四戶(其中兩戶由解放時的一戶分家)、富農的二戶,其他均為貧下中農(包括貧農、下中農、中農、上中農);個人成分為地主分子的2人,富農分子的2人;比較特殊的有歸宗立嗣2戶,城市下放1戶,下鄉知青1人,右派問題處理回家1人,刑滿釋放人員1人還帶回了妻子及其兩個女兒。從民族構成來說,在四十多戶人家當中,除了城市下放1戶4人、下鄉知青1人、娶進來的3個漢族媳婦和隨遷子女2人,其余都是白族。娶進來的漢族媳婦和隨遷子女,后來也慢慢隨了白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改說白族話。
工分
工分起源于互助組時期,完善于生產隊時期。工分是生產隊時期用來計算社員勞動量和勞動報酬的一種尺度,是社員參與生產隊產品分配和價值分配的重要依據。按工分的計算形式劃分,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計時工分,一種是計量工分。
社員因為年齡、身體和體力的原因,各人的勞動能力是有很大差異的。為了體現多勞多得,調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生產隊還對社員進行評分,將社員分為全勞力和半勞力。身體好、能參加正常勞動的成年人為全勞力,可拿十成工分;老人、未成年人和體力差一些的成年人為半勞力,可拿三成到七八成工分。
計時工分,又稱為點工。以天為單位,每天八個小時左右,以全勞力為例,每天10個工分。每天又大概分為三段:上午八點多到十一點多。下午一點多到四點左右,下午四點多到太陽落山后。有時為了給社員留點時間管護自留地。下午就不再分段,太陽落山前收工。社員工分也相應地實行分段計算。計時工分,只管勞動時間,不管勞動量,大多適用于不便計算勞動量的工種。
計量工分,又稱包工。凡是便于計算勞動量的工種,為了調動社員勞動積極性。提高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我們都盡量實行包工,實行多勞多得。包工又分集體包工和個人包工。比如,播種、栽種、薅鋤、收割等需要大家合作共同完成任務的工種,實行的是集體包工,按畝計分。路途遠的適當加分。所得工分按各人的評分成數又分到參與勞動的社員;將肥料運到田間、將農產品運回打場、上蒼山積肥、去下關積肥、交售公余糧等可由個人獨立完成任務的工種,實行的是個人包工。與個人評分成數無關,純粹按每挑重量(積肥還要看質量)計分,路途遠的適當加分,工分直接計算到個人。
如同考分是今天學生學習的指揮棒一樣。工分是那個年代社員勞動的指揮棒。社員為了多拿工分,就得多出工、多出力、多吃苦。家里有事一般不輕易缺工,輕微病痛也不愿意缺工,自留地、家務事盡量利用出工前、收工后的時間和晚上的時間起早貪黑地去做。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懷孕婦女,挺著大肚子直到臨產前幾天都在參加挑東西之類的重活。每每想起這個情景,一方面讓我為農村婦女的吃苦耐勞精神感動不已。一方面又讓我為那個年代農村婦女所經歷的艱難困苦感到陣陣心酸。這是今天的人們無法想象的。讓我們永遠不要忘了她們,永遠不要忘了那個年代!
社員掙工分的途徑。除了主要依靠出工,還有一個途徑就是給生產隊交肥料。又要滿足自留地用肥,又要給隊里交肥換工分,社員就千方百計增加廄肥。增加廄肥除了多養豬,還得要有更多墊廄的草。在麥子收割后的那段時間,各家各戶就動員家里的老人、小孩到麥田拔麥桿根,把麥桿根拔得一干二凈,統統挑回家用于墊廄。廄肥按質量評定等級,以每百斤計分。勞動工分加交肥工分就構成一家人的總工分。
工分,在生產隊時期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即隊內的支付功能。社員在隊內請工,不用付錢,只需給工分,即將自己的工分通過記分員劃撥給對方即可。
公余糧
在生產隊時期,交售給國家的部分。一般包括公糧和余糧。公糧和余糧的交售數量是國家在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時候核定的。雖然生產隊的人口在不斷增加,但是公余糧的交售任務一直沒有改變。公余糧征購的品種因各地情況而定,像我們生產隊征購的品種包括稻谷、小麥、蠶豆,有時也征購洋芋,不過洋芋5斤才能折抵1斤稻谷。當時,國家下達給我們隊的糧食征購任務是24338公斤,其中:公糧是6000多公斤;余糧是18000多公斤。糧食征購任務畝均負擔近140公斤,人均負擔約110公斤。公糧屬于國家以實物形式征收的農業稅,是完全無償的。社員們認為公糧是皇糧國稅,向國家交公糧是天經地義的,是心甘情愿的。余糧,顧名思義,應當是吃和用以外余下的糧食。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也許在1960年代初確定余糧征購基數時,征購的確實是社員吃和用以外余下的糧食,但是,經過十多年的時間。糧食產量沒有大的增長。而人口卻有了大幅增長,余糧不再名副其實。因此,社員對交售余糧是有抵觸的,社員們常說,余糧、余糧,有余才交,吃的都不夠還有什么余糧可交!盡管想不通,還是交了。余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以實物形式征收的農業稅。因為余糧的征購是強制的,而且征購的價格是很低的。比如稻谷,上等0.103元/市斤、中等0.096元/市斤,洋芋0.02元/市斤。以稻谷和洋芋為例,1市斤稻谷折算為大米0.7市斤,大米的征購均價相當于0.14元/市斤。扣除米糠價值。大米的實際征購均價不到0.14元/市斤。而當時大米的市場價約為每市斤1元;洋芋的市場價約為每市斤0.1元多。可見,征購價是大大低于市場價的。
最讓社員有意見的是,除了交售公余糧。有時候上級還要動員交售超購糧。記得有一年秋冬季節,縣里給我們大隊派了一個工作組。任務之一就是動員我們交售超購糧。可能因為認為我年紀輕好做工作的原因,工作組把我作為重點對象,三番五次找我談話。希望我做做隊里其他干部的工作。多交一點超購糧,為其他生產隊做個榜樣。還說,如果來年口糧真的不夠,可以給我們供應返銷糧。做工作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們家的口糧都不夠,我怎么能答應呢?先交后返,那不是放屁脫褲子嗎?交了返不了。我怎么向社員交待?
時至今日,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還是農村的經歷,農民情結始終與我如影相隨。我生于農村,長于農村,有著濃厚的農民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