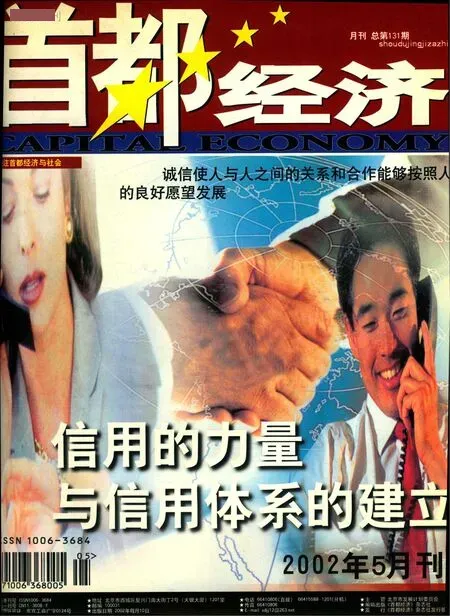改善環境和促進增長如何有效統一
劉培林
北京霧霾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霧霾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人把主要原因歸結為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政策。但不能否認的是,北京雖然是現代化水平比較高的城市,但仍然需要進一步持續地發展經濟。那么,保護環境和促進增長兩者能否有效統一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兩難抉擇。從更廣泛的角度看,這個兩難其實是關乎人類社會的普遍性問題,北京如此,整個中國如此,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此,發達國家亦如此。
破解兩難的根本出路是技術進步。比如,節能技術、碳捕獲和封存技術、徹底不依賴于碳氫化合物燃料的清潔可再生能源技術、減排技術、深度高比例的資源循環利用的革命性產品設計和制造工藝、新材料技術等等。
這些技術突破能實現環境友好的目標,而且,其研發和推廣過程本身就構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技術在大面積推廣進而成為社會主流平臺之后,上述兩難基本上得到解決,屆時可以期待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不以環境損害或只以很小的環境損害為代價。
但是,如何促進這些技術進步?如何在這些技術進步變為現實之前就盡可能地破解上述兩難?一個可能的思路是優化稅源結構。
目前各國課稅對象主要是好的行為(goods),比如,對人們的勞動和經營所得征稅,對人們滿足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消費行為和財產保有行為征稅,對企業創造的新財富(即增加值)征稅。雖然經濟學理論早已證明,征稅必定對這些好行為產生抑制作用,帶來福利凈損失,但由于市場自發力量難以充分地足量地提供另外一些公共產品,如國防、公共教育、市政基礎設施等,也由于市場自發力量無法解決貧困問題,所以,任何政府都收稅。也就是說,目前的稅源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們的好行為,這是一種扭曲。
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甚至在當今的發達國家跨入現代化行列的大部分時間內,這些國家自身乃至全球的環境容量相對而言是充足的,因此環境問題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兩難關系并不突出。但是,近一個世紀以來,隨著全球人口規模的空前增長和越來越多國家的快速發展,這一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保護環境和促進增長的兩難成了全人類共同的難題。從政策角度看,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沒有要求居民和企業對于其生產和消費活動對環境產生的不利影響付出足夠的經濟代價,比如,沒有繳納足夠的稅收或規費。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行為主體對環境的負外部性沒有內部化,或者說行為主體實際承擔的私人成本小于其行為所帶來的包括環境影響在內的全部社會成本。對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實際上是一種“壞行為”(bads)。目前政策體系沒有對“壞行為”足額征收稅收或規費,等價于對“壞行為”提供了激勵,使之過度發生,這是另外一種扭曲,也是環境問題的經濟學性質之所在。
如上所述,人類現在面臨著保護環境和促進增長的兩難選擇。而目前普遍的稅源結構又帶來兩種扭曲:抑制好行為,鼓勵“壞行為”。從中不難看出,解決兩難問題的一個原則性思路就是優化稅源結構,減少對好行為的抑制效果,同時減少對“壞行為”的鼓勵效果,即減少對好行為的課稅,同時增加對“壞行為”的課稅。這樣,既有利于保護環境,也有利于促進增長,同時消除或減緩了前面兩種扭曲,收到一箭雙雕之效。
這種意義上的稅源結構調整,完全可以在不提高社會整體稅負水平和政府稅收規模的前提下付諸實施。其基本原則是,根據從排污、排碳、耗能等行為中征收的稅收規模,等額削減對收入和消費等好行為的稅收;而且,很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可以更大幅度地削減對好行為的稅收,這是因為目前對好行為的稅收中有相當部分是用于修復“壞行為”造成的環境損失,而一旦對“壞行為”直接征稅,那么,“壞行為”的環境損失從一開始就會縮小。
當然,調整稅源結構以矯正雙重扭曲的目標,也可以通過其他政策工具組合來實現。比如,可以把對“壞行為”的稅收轉化為拍賣機制,即政府規定一定時期內全社會的排放總額,之后向社會各類主體拍賣排放配額,根據政府在拍賣中獲得的收入總額,等額削減對收入和消費等好行為的稅收。
這樣的政策調整,從短期看,可以立即起到抑制“壞行為”和鼓勵“好行為”、保護環境和促進增長的效果;從長期看,將對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技術進步提供充分的長效激勵,從而推動人類社會邁向更高的文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