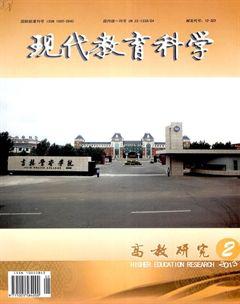臺灣公民教育的三種路徑建構
陳先哲
[摘要]作為臺灣公民社會成長歷程的標志性人物龍應臺為探索臺灣公民教育的路徑建構作出了重要貢獻。龍應臺主要從學校、社會和家庭三大路徑探索和引導臺灣公民教育的建構:不僅在學校的顯性課程和隱性課程中尋找一切可用于實施公民教育的機會,還指導民眾如何在臺灣社會政治生活的觀察和參與中獲取公民教育,更善于從家庭教育的瑣碎和細節中發掘公民教育。
[關鍵詞]龍應臺 臺灣 公民教育 路徑建構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3)02-0102-05
公民教育對于公民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已被學界反復地討論和強調。但應當通過何種路徑實施有效的公民教育,還一直是令人困擾的問題,盡管近年來臺灣、香港學界的研究早已指出:除學校系統外,家庭系統和社會系統都是實施公民教育的很好路徑。研究者們都很清楚:僅靠學校教育一途來達成公民教育,幾無可能。沒有家庭系統和社會系統的的共同參與,從學校系統獲得的公民教育最多只能讓人記住教科書的只言片語,而失去行動系統的支持。因此學校、家庭和社會三個系統都是實施公民教育的有力路徑,三位一體,不可偏廢。但盡管如此,仍少有研究者能在這三種實施路徑上給出具體建言,即便有,也多是把重心放在學校系統之上。
上述實施公民教育的三種路徑,卻在臺灣作家龍應臺的系列作品中有很好的詮釋。龍應臺并不是以一個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公民教育,但卻絲毫不妨礙她成為這個領域的先知和積極的推動者。她的《野火集》(1985),可謂臺灣民眾公民意識的啟蒙讀本,甚至對推動臺灣解嚴也起到相當的作用。早在20世紀80年代龍應臺就已意識到,公民教育并非僅靠幾堂公民課就能見功效,而必須由學校、家庭和社會三大系統共同發力,公民教育方能覓到出路,公民社會成長才有希望。其后20余年,龍應臺作品更是一直緊扣此三大系統,直觸公民教育核心。她的作品多年來一直影響著臺灣民眾對公民教育的認識。因此,作為臺灣公民社會成長歷程的標志性人物龍應臺應當是研究臺灣公民教育不可遺漏的名字,其作品亦應成為研究臺灣公民教育的重要文本和寶貴素材。
一、公民教育的學校路徑
學校系統的公民教育可歸結為顯性課程和隱性課程兩種路徑。杰克遜在他的《班級生活》(1968)中首先使用了隱性課程一詞。他分析了教室中的團體生活、報償體系和權威結構等特征,認為這些不明顯的學校特征形成了獨特的學校氣氛,從而構成了隱性課程。隱性課程應與顯性課程(正式課程)同樣重要,但“在歷來的課程研究中都受到忽視”。
龍應臺并非教育研究者,學校系統的公民教育并非其發力重點,但每一發力,便是一針見血。在20世紀80年代,她便通過《幼稚園大學》、《機器人中學》、《不會“鬧事”的一代——給大學生》、《又是公假》等系列文章,探討學校系統應當如何實施公民教育。其中無論通過顯性課程還是隱性課程實施公民教育,她都有獨到見解。
(一)顯性課程的路徑
在《不會“鬧事”的一代——給大學生》一文中,龍應臺回憶讀高三時上公民課“三民主義”,對課本中“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這句話產生質疑,但課本顯然將此當成斬釘截鐵的結論,毫無解釋引證。當她問老師“為什么”,老師還很驚訝,回答:“課本這么寫,你背起來就是。聯考不會問你為什么。”龍應臺認為這并非“公民教育”而是“臣民教育”:“基本上,課本編者與授課老師并不認為學生有自己作判斷、下結論的能力,所以才會有這種你別問為什么,記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態度。他們因此所剝奪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權利與獨立判斷的能力。”
洪泉湖曾梳理過臺灣公民教育的進程,認為臺灣直到80年代,三民主義課程才“較能去除意識形態色彩,偏重社會科學之學習”。龍應臺高三之時所處的60年代,其公民課顯然“意識形態色彩”仍較重。于是她不禁要質疑這種顯性課程,是否只打著“公民教育”的幌子。正如杜威所說:“一個課程計劃必須考慮課程能適應現在社會生活的需要;選材時必須以改進我們的共同生活為目的,使將來比過去更美好。”三民主義屬于過去的一種美好,但是否永遠美好而毋庸置疑?其后臺灣幾十年的變局已為龍應臺當年的質疑提供了有力的證明。
進入新世紀后,龍應臺更是在游歷西方多年的基礎上開始著意比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民教育課程。比如,在關注兒子安德烈就讀的德國學校如何實施公民教育后她發現,德國的公民教育不僅僅是在公民課里,而是把公民教育滲透進入所有學科里,實可為臺灣公民教育課程所借鑒。
她曾談到安德烈高二時在德文課上讀布萊希特的一個劇本《伽利略》,老師是怎么教、怎么組織討論的事。布萊希特的劇本寫的是伽利略發現了地球的原理,但是這個原理是教會所不容的。而課堂討論到最后的核心就是個人跟群體之間的關系問題,面對教廷或國家這種巨大的機器,個人什么時候要抗爭、要犧牲,什么時候是可以妥協、可以退讓的。德國公民教育在各學科中的滲透程度讓龍應臺震驚,“這群17歲孩子是這樣在上語文課嗎?個人面對國家機器如何自處,不正是公民教育最核心的題目嗎?”
(二)隱性課程的路徑
如前所述,隱性課程是容易被忽視的課程,但在龍應臺筆下,其對公民教育的意義甚至還要重于顯性課程。在《機器人中學》一文中,她極力反對當時臺灣學校的高壓性管訓教育,認為教育者所不自覺的矛盾是:“他們在智育上希望學生像野兔一樣往前沖刺(當然也有為人師者希望學生在智育上也如烏龜);在所謂‘德育上,卻拼命把學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她認為這兩者并存是一種幻想,并且一針見血地戳破了這種幻想,“我們如果一心一意要培養規矩順從聽話的‘乖學生,就不要夢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馬行空的優秀人才。‘庸才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杜威曾尖銳地批判學校教育的不民主,指出傳統學校教學以靜聽為主,學生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教室如同牢獄,兒童如同囚犯,教師如同看守,書本如同刑具。他的矛頭實則指向隱性課程,認為必須要改變這種權威結構,“兒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種措施應圍繞他們而組織起來”。如杜威一樣,龍應臺眼光犀利,就連上課點名、規定學生穿著這些小事,她也能揪出這些隱性課程對公民教育的傷害:“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么?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她更看到隱性課程中一切可用于公民教育的機會,在《不會“鬧事”的一代》中疾呼:“學生對學校措施有所不滿而投書、開會、抗議的時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機會,幫助學生學習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決問題,為什么我們反而以記過處分作為……的手段?為了表面的安靜穩定而扼殺年輕人的正義感,代價是否太高了一點?敢于表達意見、敢于行動的學生在一次兩次的申誡記過之后,當然也學會了保護自己;他發覺,這個社會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氣或正義感。”
龍應臺并非專業教育研究者,但也許正是如此,才不囿于“專業”,反而挖掘出影響臺灣公民教育實施路徑的更深藏的因素。她認為公民教育的顯性課程要以理服人,引發思考;也不能單純寄望于一門公民課,而應融公民教育于各種課程之中;更加重要的是,不要讓隱性課程中的“規訓與懲罰”成為公民教育的傷害者,而應在隱性課程中尋找一切可用于公民教育的機會。
二、公民教育的社會路徑
亞里士多德曾強調:“真正的公民必定在于參與行政統治,共同分享城邦的利益。”亞氏主張公民身份的主要標志就是作為城邦這個公民自治團體的一員,公民享有參與城邦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利,城邦中一切重大事務必須由公民集體討論決定。參與城邦事務既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龍應臺在臺灣社會的不同時期,便采取了不同的路徑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并藉此影響臺灣民眾。
(一)公民社會啟蒙期的抗爭路徑
20世紀80年代,臺灣尚未解嚴,公民社會仍如鏡中水月,龍應臺采取了一種抗爭的路徑來進行臺灣公民教育的啟蒙。當時她從美國留學回到臺灣,對當時之威權體制及順民社會處處不適應。因此她早期的作品,便主要是選擇社會系統為批判對象,采取抗爭路徑來宣揚公民教育。《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是她在被“醬缸文化”浸泡的臺灣社會燒起的第一把野火。接著,又陸續發表《生氣,沒有用嗎?》、《不要遮住我的陽光》、《不一樣的自由》、《歐威爾的臺灣》等文章,迅速引起臺灣社會的強烈反響。1985年,這些文章結集成的《野火集》出版,21天再版24次,創下出版界紀錄,野火已成燎原之勢。
龍應臺在這個時期的作品往往選擇教育、環保、交通、消費、治安等切實可改的方面去努力,采取讓普通民眾可接受和操作的方法來宣揚公民意識。她選擇一種抗爭但非革命的務實路徑,不求“畢其功于一役”,而把改變社會狀況的希望寄托在民眾身上,希望喚醒民眾對不良社會現象的抗爭意識并推動社會變革。正因為她選擇的這種路徑,使她的作品在當時的威權體制下釋放了最大能量。她告誡臺灣民眾,不是生氣沒有用,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氣的人太少。“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于是,很多人不再繼續做“沉默的大多數”,臺灣民眾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可以說,《野火集》對喚醒、培養臺灣民眾的公民意識,推動解嚴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二)公民教育發展期的傳教路徑
1987年臺灣宣布解嚴后,臺灣社會開啟民主化進程,尤其是1996年實現總統直接民選和2000年政黨輪替首度實現,標志著臺灣社會趨向自由化和多元化,已進入公民社會發展期。在這個時期,龍應臺也因應變化,寫作方式從原先“野火”式的言辭犀利變得更為娓娓道來。她認識到:處于公民社會發展期的臺灣,更需要一種傳教式的路徑去推動社會共識的形成;這個階段的臺灣民眾,也更需要一位公民教育的傳教士而不是斗士。
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龍應臺都是旅居國外,但她并沒有放棄對臺灣公民社會發展的關注,反而站在“地球村”公民的高度,將臺灣的社會問題、社會現象納入國際社會的大背景中去觀察。她依然想念那個“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強韌的地方”,并且看得更加深遠:“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
1999年,龍應臺回到臺灣任臺北市文化局長。2003年卸任,她更是立言不減,且更有意識地融公民教育于臺灣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她認為臺灣的公民教育,是活生生的公民教育,是每天生活里的公民教育。馬英九的特別機要費案、陳水扁的賄案等,都被她當作給臺灣人民最好的公民課教材。
如她在《我怎么上“陳水扁”這一課》中便寫道:“最該被快斗的對象,不是這個任期不到二十個月、威望不到膝蓋高的總統,而是培養了他這種人物而且容許他茍延殘喘的整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人民自己腦里的文化思維。……打倒一個人,只需要熱情和憤怒;革新制度、提升文化,抽絲剝繭地厘清問題所在,看準了問題下手,需要的卻是極度、極度的冷靜,深刻的思辨能力,長程的眼光,宏大的器識,鍥而不舍的精神。”
臺灣社會任何一個重要事件,她都希望通過言論和社會討論來推動公民教育。她認為真理越辯越明: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后,才能得出共識,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就沒有公民社會。她始終篤信民主便在生活里,而并非選舉投票、國會爭執之類的表演構成的“小方格”里。她相信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民主會成為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和呼吸的空氣:“民主并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回轉的空間。”而事實上,解嚴后的臺灣,社會民主運動蓬勃發展,臺灣民眾也更懂得如何在這些社會政治生活中獲取公民教育,從而大大推進了臺灣公民社會的進程。
三、公民教育的家庭路徑
家庭是最小的組織,但在這個最小的組織里實施公民教育,實現民主、自由和平等,卻是最困難的。杜威認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應“相信平等,這是民主信條中的一個因素。……每一個人都同樣是一個人;每一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機會來發展他自己的才能,無論這些才能的范圍是大是小”。此話自然也適用于家庭。而家庭由于代際關系的存在,恰恰最容易成為不平等組織。尤其是中華文化的“禮”“孝”傳統,使得父母總天然地處于權力掌控者的位置,這是非常不利于公民教育的實施的。因此,即便很多專治公民教育的專家,一回到家里,扮演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的角色的時候,也甚少再思考如何通過這個系統來進行公民教育。就算有思考,但實施起來也是難之又難。在這方面,龍應臺還是能通過其文字和身體力行,探討如何在這個最小組織內實現民主、自由和平等。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臺灣公民社會,已進入更為成熟的發展階段,因此,龍應臺轉由家庭教育之路徑來探討公民教育,看似無心插柳,卻又再度起到了啟蒙和引領作用。
龍應臺關注家庭系統的公民教育是從結婚生子后開始的。她育有二子,《孩子你慢慢來》和《親愛的安德烈》兩書便是孩子成長過程及母子之間心靈對話的記錄。尤其是《親愛的安德烈》一書,看似是與走向成年的兒子之間的家庭教育,但公民教育的思想卻無時無刻不滲透其中。
在此書中,她與大兒子安德烈探討理想和人生、親子關系、自由與責任、民族和國家、民主和公民、公平與正義等問題。他們有兩代人的價值觀,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相互間也充滿追問、反詰、質疑和交鋒,但最重要的是,這本書讓人看到了家庭成員之間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代際關系中只有年齡上的差距,沒有絕對的對錯和高低。安德烈在質疑母親權威,在闡述自己觀念的時候,毫不遜色,毫不退避。一個沒有公民教育信念的家庭,是無法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和交流的。在公民理念主導下的家庭教育,并不是單向度的灌輸和接受,而是雙向度的交流和相互教育。正是雙方骨子里的公民理念,所以龍應臺認為:“我這個1950年代在臺灣成長的母親和1990年代德國的兒子之間,竟然有了對話的歷史基礎。”這句話也足以概括此書對公民教育的意義所在。
在《親愛的安德烈》一書中流傳最廣的篇章——《給河馬刷牙》里寫到一段凌晨三點的母子對話:
兒子安德烈說:“媽,你要清楚接受一個事實,就是,你有一個極其平庸的兒子。”并問,“你會失望嗎?”
我們無法得知龍應臺是否“失望”,但且看她是如何回應兒子的:
“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樂。……假定說,橫在你眼前的選擇是到華爾街做銀行經理或者到動物園做照顧獅子河馬的管理員,而你是一個喜歡動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認為銀行經理比較有成就,或者獅子河馬的管理員‘平庸。每天為錢的數字起伏而緊張而斗爭,很可能不如每天給大象洗澡,給河馬刷牙。……我們最終極的負責對象,安德烈,千山萬水走到最后,還是‘自己二字。因此,你當然更沒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為了符合上一代對你的想象而活。”
龍應臺和兒子的對話,超越了世間許多母子間不痛不癢的問侯,成為了一種彼此深入的了解和尊重。家庭系統中的公民教育,最難得的是對彼此價值觀的尊重,而非“望子成龍”般的價值觀強加。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和互相尊重,是公民社會形成的根基。尤其是長幼之間,長輩不必總是扮演權威,在這方面中西方社會有著顯著差別,龍應臺的書中,就記錄了小兒子菲利普對此方面的觀察。
15歲的菲利普和她說:當他見到媽媽的華人朋友的時候,媽媽的朋友明知道他會講中文,還是會看著他媽媽問“他幾歲了”,而不直接地對著他說“你幾歲了”。因此他認為在這方面歐洲人和華人的差別在于:“歐洲人是看年齡的,譬如在德國學校里,你只要滿十四歲了,老師便要用‘您來稱呼學生。但是,中國人看的不是年齡,而是輩分,不管你幾歲,只要你站在你媽或爸身邊,你就是‘小孩,你就沒有身份,沒有聲音,不是他講話的對象。所以,他才會眼睛盯著你的媽或爸發問,由‘大人來為你代言。”
作為著名社會觀察家的龍應臺,聽到兒子的分析,竟也“傻了”。她寫道:“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邊的孩子只有醬油瓶子那么高,我也會彎下腰去和他說話。”
家庭系統和親子關系中充滿了瑣碎和細節,然而,教育的品質總會從這些瑣碎和細節中穿透出來。是民主、平等的公民教育,還是權威、尊卑的臣民教育,就隱藏在這些瑣碎和細節之中。龍應臺最善于從細節中發現問題并發人深省,其作品總是另辟蹊徑,表面寫的是家庭系統中的瑣碎和細節,然而公民教育的灼灼之光卻總力透紙背。她關注家庭的幾部作品,曾被眾多評論者和媒體解讀為轉型之作。但實際上,轉型的只是她的寫作方式,公民教育仍是其不變的情懷。這些作品,不僅再度為臺灣公民教育的建構提供新的路徑指南,甚至還影響到了更為廣泛的華人地區。
在臺灣公民社會成長的過程中,龍應臺一直以其作品引領著臺灣公民教育的前進方向:公民教育應該成為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公民教育并非只是公民課上的“思想正確”,它還存在于“規訓與懲罰”的一切隱性課程中,它還布滿在一切社會政治生活中,它更隱藏在家庭關系的瑣碎和細節中。近30年來,龍應臺一直致力于從學校、社會和家庭三大系統中探索公民教育的路徑建構,為臺灣公民教育建設起到了啟蒙與指南的重要作用。當然,由于并非專業研究者,龍應臺自然也有不少局限之處:她對公民教育的言論,散見于各個時期的文章之中,并無系統之專論;且她的寫作方式,多以融入個人情感的方式來宣揚公民教育,有些言論難免有失偏頗。另外,龍應臺最常被人詬病之處在于“破多立少”,龍應臺在擔任臺北文化局長時便也不得不坦陳“大立實在要比大破難上百倍”,因為建設遠比破壞困難,批評比做事容易,公民教育的路徑建構亦是如此。如今,龍應臺又二度為官,2012年春正式接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主任委員,并于同年5月隨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而成為臺灣首任文化部長。只不知,再度為官的龍應臺是否會因官員身份和經歷而改變以往關于公民教育之認知——她對臺灣公民教育的路徑建構的種種言說,究竟只是作家龍應臺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自說自話,還是也會成為官員龍應臺將臺灣引領到更高層次公民社會的施政方針?龍應臺尚需證明,臺灣社會亦拭目以待。
(責任編輯:趙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