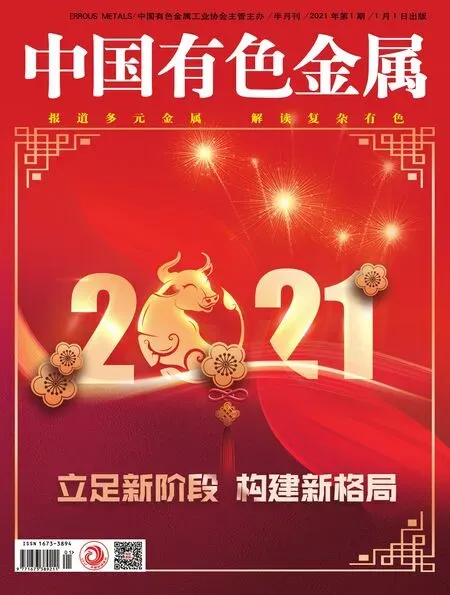深化好融合 對標找差距
——提升金鼎鋅業現代化治理體系能力
陳青|文
要積極搶抓有利機遇,強化“超越自我、跑贏大盤、追求卓越”績效導向,持續深化整合融合,全面對標找差距,不斷提升現代化治理體系能力,通過用好用活“對標工具”,追求效率和效益,不斷提高金鼎鋅業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重大戰略部署,要求完善黨領導各項事業的具體制度,把黨的領導落實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各個方面。對國有企業而言,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按照兩個“一以貫之”的要求,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推動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
2019年1月24日,金鼎鋅業股權變動,四川宏達股份股權退出,金鼎鋅業正式進入中國銅業,成為中鋁大家庭的一員,這是金鼎鋅業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立足于云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陳豪“打造世界一流的綠色礦山、千億鉛鋅的雙百基地、鉛鋅技術的標桿企業、央地合作的共贏典范”戰略定位和中國銅業“一平臺、兩基地、三千億”戰略平臺,金鼎鋅業確定了“11211”戰略目標,公司的發展定位進一步清晰、發展資源進一步豐富、發展基礎進一步夯實、抗御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這為推動和實踐金鼎鋅業高質量發展帶來了難得機遇。我們要積極搶抓有利機遇,強化“超越自我、跑贏大盤、追求卓越”績效導向,持續深化整合融合,全面對標找差距,不斷提升現代化治理體系能力,通過用好用活“對標工具”,追求效率和效益,不斷提高金鼎鋅業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推進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金鼎鋅業實現“11211”戰略目標的根本途徑。按照中鋁集團年度工作會提出的“強化三個導向,開展全要素對標”“通過對標,比效率、比效益,而不是比投資、比規模,最終提升公司競爭力”的整體要求,和中國銅業2020年工作會提出的“深改革 全對標好融合 多盈利”的年度工作主線。金鼎鋅業與中國銅業內的先進企業相比,在安全環保、內部管理等領域尚有較大差距,主要體現在“一多、一低、兩薄弱”,即:歷史遺留問題多,勞動生產率低,安全環保基礎薄弱、內部管理薄弱,這些短板導致公司競爭力、控制力、創新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不強。
在此基礎上,金鼎鋅業必須加快在思維觀念、經營思想、管理模式、文化理念上的整合融合步伐,全面融入中國銅業管理體系,促進中國銅業盡快形成“三個千億”的規模效應,促進企業整體價值最大化,最終實現增強“五力”的目標,具體通過“三個著力”實現。
健全完善管控架構 著力提升治理體系能力
隨著進入央企,金鼎鋅業的管理定位同步發生改變,加快構建適應新發展需要的管控架構是當務之急。金鼎鋅業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充分發揮黨在治理體系中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作用,堅定不移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在公司治理的全過程和各環節,不折不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按照生產經營層功能定位,適應性地調整了原來的13 個生產、輔助生產單位和14 個職能部門,重新優化設置為8 個部門、4個中心、9 個生產廠,職能科室、生產車間從137 個精簡至88 個,精干剝離生產單位人員750 人到經營服務中心,大幅度精簡壓縮機構,優化人力資源結構,構建三級精干高效的扁平化組織機構。按照“統一標準、統一規則、統一文化、分層分責”的要求,積極構建以公司章程為核心的內部管理制度體系,建立了涵蓋全面業務的分權授權手冊,規范了各層級、各業務系統和員工的職責權限、決策流程和權利義務。通過健全完善管控架構,不斷提升公司的治理體系能力。

健全市場化運作機制 著力提升改革創新能力
企業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主要目的就是通過改革讓企業提高市場化適應能力。在當前金鼎鋅業工藝、人員、生產組織模式全面改革的過程中,主要是通過健全和優化市場化運作機制,圍繞企業價值提升,以《全要素對標指標體系》編制及落地為抓手,以機制創新引導資源高效配置。一是通過移植、共享中國銅業組織管理體系,推動金鼎鋅業管理變革和流程再造,提升管理效能。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按照“多勞多得、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的總體要求,探索建立薪酬績效激勵機制,從組織績效、個人績效、述職表現、德能勤績廉、民主測評全方位考評,將考評結果運用于個人成長的剛性條件,充分發揮考核激勵作用、導向作用和監督作用,更好地發揮績效考核的“指揮棒”功能,逐步實現“工資總額與效益掛鉤,員工工資與崗位掛鉤,骨干員工與業績掛鉤,收入與績效掛鉤”的目標,提振干部職工擔當實干精神,激發干事創業干勁,提高企業活力和效率。三是持續推進冗余人員勞動服務中心改革和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推動企業輕裝上陣。四是堅持效率優先,加快推進老姆井尾礦庫等在建項目建設,系統解決“采選排”不匹配、冶煉廠產能不平衡問題,提升生產線運行效率。五是按照“世界一流的綠色礦山、千億鉛鋅的雙百基地、鉛鋅技術的標桿企業、央地合作的共贏典范”的戰略定位,加速推進環保治理項目。一方面按照“保守、務實,不貪大求洋”的要求加快氧硫混合礦綜合選冶技術研究,盡快打通氧化礦綜合回收暨環保治理項目流程,從技術上解決庫存氧化礦消耗問題;另一方面按照“科學環保、合理環保”的要求,加快實施“四個一批”19 個生態環境治理項目,力爭2022年實現采、選300 萬噸/年轉型升級。六是堅持從嚴治黨,盯緊“關鍵少數”,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力度,嚴格執行“三重一大”決策程序不走樣,抓班子強核心、帶隊伍固根本,打造一支思想、作風過硬隊伍,提高公司抗風險能力。
建立對標找差體系 著力持續提升競爭能力
全面對標找差,是強化目標導向、問題導向、結果導向的具體體現,是補短板、強弱項的有效抓手,既要有宏觀治理能力“面”上的躍升,更要有微觀關鍵指標“點”上的突破。“通過對標實現提效和降本,通過對標提出具體、可實現的量化措施和趕超目標,最終提升企業的發展和競爭能力。”隨著整合融合的深入推進,金鼎鋅業要根據《中國銅業全要素對標管理工作指引(試行)》的要求,對產品完全成本進行依次分析,在材料成本、動力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費用、外包費用、金屬損失、三項費用、副產品收益、其他收益等方面建立健全與兄弟企業的對標找差體制機制,全方位提升經濟運行效率和效益。要以“比效率、比效益”為目標,深入貫徹落實中國銅業“深改革、全對標、好融合、多盈利”的工作主線,堅持對外對標、對內優化,找出差距,努力趕超,完成全年各項目標任務。
新平臺開啟新希望,新征程需要新擔當。2021年是金鼎鋅業全面融入中國銅業的第二個完整年,站在更高的平臺上,金鼎鋅業不斷學習貫徹中鋁集團和中國銅業各項先進理念,落實各項工作要求,以變革的思維、扎實的作風、飽滿的精神積極應對市場危機挑戰,堅定信念、滿懷激情、齊心協力、砥礪奮進,持續增強“五力”,不斷奪取高質量發展的新勝利,為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銅鉛鋅企業作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