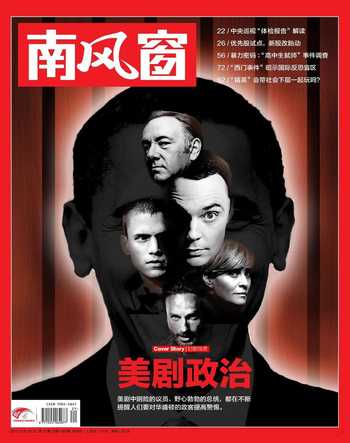中東政治生態回歸本來面貌
張墨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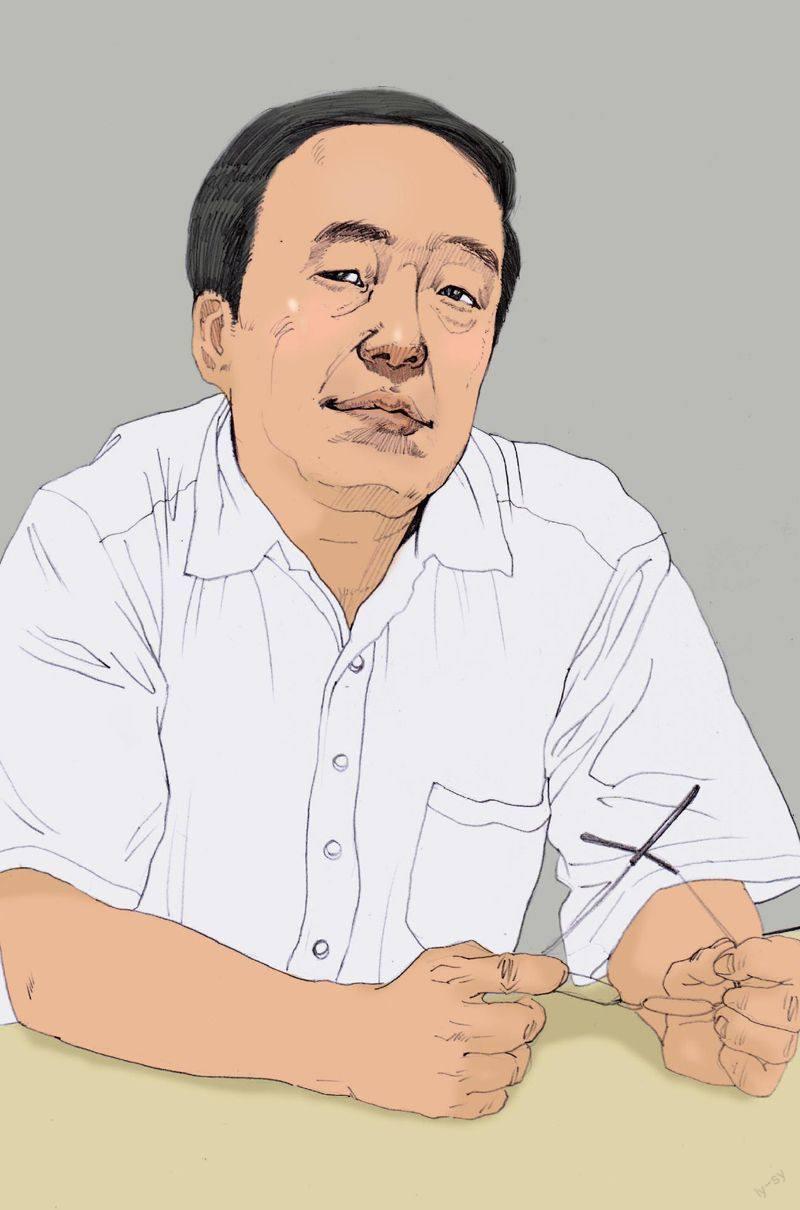
美國支持的中東秩序正在崩潰,但新秩序并沒有出現。相反,有的只是不斷蔓延、可能遠遠溢出地區邊界的混亂。敘利亞和埃及的事態還在發展,中東內部不僅持續著民族教派的沖突,極端主義的力量也被釋放。就地區大國中誰能取代美國成為秩序維持者,中東是否需要外部干預,內部再平衡又如何實現,本刊專訪了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殷罡。
內部博弈變得重要
《南風窗》:近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關于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的決議,打破了國際社會在敘利亞問題上長達兩年半的僵持,局勢似乎有所緩和,美國的態度變化起到了什么作用?
殷罡:敘利亞的問題原本是個僵局。今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到莫斯科準備和俄羅斯攜手政治解決,化武危機發生后,相當于把政治解決的可能性打破了。縱觀這幾個月的態勢,美國接受俄羅斯的政治解決意向,后來接受和贊同普京的“化武換平安”,這表明美國的確希望有人幫它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兩次俄羅斯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外部大國干預、激化矛盾的力量在減弱,而中東地區國家之間、民族教派之間的博弈就變得重要了。
《南風窗》:民族教派之間的博弈在敘利亞將以何種方式上演?少數派的阿拉維人會被遜尼派統治所取代嗎?
殷罡:要推翻少數派的統治,遜尼派就要成氣候,有自己的方向、合法的基本組織。這是他們目前所缺乏的。而且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遜尼派過于分裂。
在我看來,少數派統治多數派合法性的問題是被夸大了。少數派往往是社會變革的前鋒,容易接受全新的意識形態。在敘利亞,長期引導歷史發展的正是阿拉維派、德魯茲人這樣的少數派。敘利亞要實現政治現代化,國際壓力是必要的,要使敘利亞的政治生態更合理化,遜尼派在權力格局中必須取得更多的份額,而如果砸爛原來的體制,建立起來的肯定是混亂的大雜燴,相比于社會改良,革命的代價太大了。
《南風窗》:有消息稱,美國正計劃對巴沙爾·阿薩德發起審判,并且已開始收集犯罪材料。您怎么看?
殷罡:審判是很不明智的行為。伊拉克戰爭前,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承諾不取締復興黨,只針對薩達姆和他的少數隨從,復興黨的問題由伊拉克人自己解決,結果戰后美國防長拉姆斯菲爾德取締復興黨,復興黨高層干部、軍隊中旅長以上的軍官一律不得進入新政府和新體制,把大批本來可以爭取和利用的薩達姆追隨者趕到了基地組織那邊。直到2006年,美國才明白過來,跟伊拉克新政府一起落實政策,只要承認新體制,就可以參加政治進程。所以說,對立的各方都容易犯一個同樣的錯誤,就是熱衷于出氣,而不是改造社會。
美國的使命已經完成
《南風窗》: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單邊行動幻滅后,逐漸調整中東政策,美國不過多插手敘利亞,是不是符合淡出中東計劃的長遠戰略?
殷罡:自從美國有意淡出中東后,中東地區的生態恢復了本來面貌。內部的基本矛盾,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間、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之間以及伊朗核計劃對阿拉伯人的威脅等等,就真正表現出來了。
過去總是有外部大國的包辦,冷戰時期是美國和蘇聯各包一頭,冷戰之后,美國借反恐專打激進專制的遜尼派力量,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時候,美國開始明白,不能卷入過多的地區事務。所以,不想在敘利亞有太大作為。其實從利比亞戰爭就能看出端倪了,美國就打了幾天,讓法國和卡塔爾承擔更多。如果說中東需要外部干預的話,根據這個地區千年以來固有的政治生態,應該是歐洲國家來管,這也是地緣政治的基本規則在發揮作用。
美國本身就是被冷戰推到了主導中東力量和格局平衡的位置,它的使命已經完成。過去的反恐過于草率魯莽、方向不準、考慮不周全,留下了很多后患。比如,打遜尼派的激進極端組織和地區強權人物,反而成全了什葉派、成全了伊朗。
《南風窗》:未來的中東是否還離不開外部干預?歐洲國家又如何參與?比如在敘利亞問題上,誰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殷罡:敘利亞今天的局面與法國歷史上的委任統治有很大關聯,沒有很好地引導敘利亞這個社會。一戰后,敘利亞、黎巴嫩歸法國委任統治,法國在敘利亞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意識,就是搞民族分離,試圖把敘利亞變成5個國家,黎巴嫩基督徒國家、阿拉維國、德魯茲人國家、遜尼派大馬士革國以及北邊的阿勒頗國。這激起了敘利亞人非常強烈的反抗,規模遠遠大于1936年巴勒斯坦人對英國的反抗。法國人實際上是摧毀了敘利亞整個社會,應該對這一地區負歷史責任。國際社會也很清楚,所以2006年聯合國在向黎巴嫩派遣維和部隊時,就以法國人為部隊司令。所以,現在敘利亞亂起來的時候,往美國身上看,就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
《南風窗》:法國能擔負起這個歷史使命嗎?
殷罡:法國掌握了一部分敘利亞上層反對派,跟戰場上的自由軍也有些聯系。利比亞戰爭時,法國的國防部和退伍軍人協會就在利比亞發揮了很大作用,曾試圖撮合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談判,非常活躍。
在敘利亞這個問題上,法國可以提出建議,因為它對敘利亞的社會結構有很深的了解。敘利亞問題交給國際會議的話,法國方面應該提出完整的、切實可行的方案。
宗教權威和體制權威的爭斗
《南風窗》:中東內部的力量角逐繞不開宗教權威和體制權威的爭斗,在埃及,是不是走向了簡單粗暴的路線,變成了伊斯蘭革命和軍隊反革命之爭?
殷罡:穆兄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歷史上已經有很多次了。穆兄會早年是要推翻君主和軍人專制,建立伊斯蘭國家,現在它知道建立不了了,因此就想在一個世俗的政權中當老大,必然要把伊斯蘭的意識灌輸到社會當中,試圖把伊斯蘭權威和世俗體制權威嫁接起來,由它來主導。
在埃及,為了保證體制權威的正常發育,必須限制宗教權威,這個使命要由軍人來完成。土耳其軍隊、阿爾及利亞軍隊過去也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如果沒有軍人的干預,稚嫩的世俗力量肯定斗不過深厚的宗教力量。埃及主張世俗權威的是世俗派、基督徒、中產階級、青年群體,這些人的人數至少在目前沒有伊斯蘭勢力的追隨者多,如果把“一人一票”拿到伊斯蘭世界,伊斯蘭的勢力肯定是占上風的,所以需要有軍人的力量強扭這個方向。
歷史上,穆兄會被抓被殺好幾茬了。經過這一次的教訓,穆兄會會變得更聰明,新一代的穆兄會可能會根據現在的政治環境建立新的政黨,淡化伊斯蘭色彩。一方面,軍人堅持原來的角色,另一方面,伊斯蘭勢力也會向新的規則妥協,建立一個健康的形象。
伊朗是另一場巨大博弈
《南風窗》:中東力量內部的平衡會產生新的地區性大國嗎?比如伊朗?
殷罡:阿拉伯世界可能會出現一個或者兩三個盟主,比如沙特、埃及。但是不可能出現伊朗對阿拉伯世界的征服,這會促使阿拉伯世界團結起來反征服。未來,主體民族之間的征服是不存在的,他們之間可能打仗,但不是征服性的戰爭,而是力量的較量,尋求新的和平的角逐。
原來的地區霸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他們都是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屬于土地、資源之爭。這種地區沖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在現代社會里,出現這種情況,通過安理會的決議、制裁是可以干預的。
《南風窗》:伊朗正式接手了俄羅斯援建的核電站,聯大會議上,伊朗在針對以色列的立場以及核談判問題上,都展示出了某些不同以往的新面貌。美國也在推動同伊朗的切實接觸,這會對阿拉伯世界產生怎樣的沖擊?
殷罡:很顯然,奧巴馬準備接受一個有核伊朗,跟伊朗和解,但是海合會國家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對伊朗來講,跟美國和解、放棄核武器計劃,革命衛隊又不情愿。所以,各自的內部陣營都有矛盾。
奧巴馬本人是愿意找到一條和伊朗的非戰解決方式,魯哈尼本人也在改變伊朗的國際形象。在核問題上,哈梅內伊也知道,如果真要發展核武器的話,必然挨打,而且會是以伊朗無力招架的方式。如果開戰,就會把伊朗打回半個世紀以前。所以伊朗有可能在得到相應的回報和保證之后,真的放棄核武器計劃。
而如果接受一個有核伊朗,阿拉伯國家、歐洲國家、以色列都會感到害怕。在以色列看來,盡管伊斯蘭國家的巴基斯坦有核武器,但那是針對印度的,而且受到中國的監控,對以色列不構成威脅。盡管以色列明白,伊朗發展核武器是同美國抗衡、同阿拉伯世界抗衡,但是伊朗領導人一貫揚言要把以色列滅了,這讓他們產生了很強烈的不安全感。以色列盡管很難成為伊朗核打擊的目標,但也做好了準備,常年保持有一艘“海豚”級潛艇帶著核反擊導彈在紅海值班。以色列還是認為,伊朗掌握了核武器的話,會給整個地區安全造成很大的不平衡。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無疑會增加黎巴嫩真主黨、什葉派的籌碼。
這就是中東地區的另一場巨大的博弈,即是否承認伊朗的國家地位的博弈,是否承認伊朗可以是一個同日本相類似的擁核國家,有核工業基礎,但是不制造核武器。
魯哈尼與奧巴馬沒會晤成,說明雙方都沒有冒進,這其實是個好事,要真是激化了內部矛盾,麻煩就大了。
《南風窗》:中東的態勢會促使美國加快重返亞太嗎?
殷罡:無論是美國、法國還是俄羅斯,都是中東的外部勢力。美國逐漸淡出中東是不可逆轉的,美國的政策無非是“把羅馬的谷倉還給羅馬”。冷戰時期,美國得支持以色列,跟蘇聯支持的敘利亞、埃及打仗。但現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已經完成了反恐義務。美國本來就是亞太國家,二戰以來,美國在亞太受到的挑戰更大,從日本偷襲珍珠港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是在亞太。而現在,美國要進行中東和亞太的力量再平衡。中東地區4個大種族廝殺3000年,他們以及他們的祖先一直在尋求力量平衡,冷戰時期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而冷戰結束之后,中東內部原生態的力量就顯得非常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