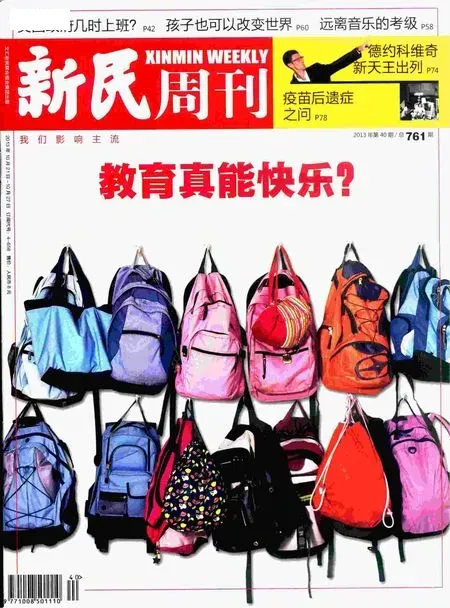聽(tīng)取罵聲一片
韓濱鴻

習(xí)慣性吐槽
這個(gè)夏天電視上兩檔漢字節(jié)目有聲有色。一檔是河南電視臺(tái)的“漢字英雄”,三位妙齡少女過(guò)關(guān)斬將奪得狀元、榜眼和探花(有人建議第二季索性改名“巾幗英雄”得了),另一檔是央視科教頻道的“中國(guó)漢字聽(tīng)寫(xiě)大會(huì)”,來(lái)自全國(guó)各地?cái)?shù)十所中學(xué)的小選手捉對(duì)廝殺,場(chǎng)上哭哭笑笑的,即將決出最終勝負(fù)。
每場(chǎng)“聽(tīng)寫(xiě)大會(huì)”都有輔導(dǎo)老師觀戰(zhàn)的鏡頭,看得出來(lái)一些老師漢字聽(tīng)寫(xiě)水平不如自己輔導(dǎo)的孩子,往往是看了場(chǎng)上選手寫(xiě)出來(lái)的字才恍然大悟。這也難怪,語(yǔ)文老師不應(yīng)該寫(xiě)不出“癩蛤蟆”,但他們一定要知道“怒艴”是什么意思,要知道“甾醇”、“碌碡”、“饸饹”怎么寫(xiě)嗎? 而這些生僻的詞匯在“聽(tīng)寫(xiě)大會(huì)”上并不少見(jiàn),其實(shí)較量的范圍已經(jīng)不僅是漢字而是百科知識(shí)了。
相比之下,“漢字英雄”對(duì)漢字這個(gè)主旨的聚焦更準(zhǔn)確,難度也明顯親民,決賽時(shí)還有“錙銖必較”、“云蒸霞蔚”這樣的低段位詞匯。這檔真人秀節(jié)目更多民間色彩,參加的孩子都是從心眼里喜歡漢字。而“聽(tīng)寫(xiě)大會(huì)”則是專業(yè)隊(duì)伍的正規(guī)賽,選手們有的深更半夜還在背誦生僻詞匯,一些場(chǎng)邊觀戰(zhàn)的輔導(dǎo)老師也有強(qiáng)烈的求勝欲,不很淡定。
有人用喪心病狂、令人發(fā)指來(lái)形容“聽(tīng)寫(xiě)大會(huì)”的這些考題,以及背后的出題人。其實(shí)話不必這么重。在中國(guó),考場(chǎng)、球場(chǎng)和官場(chǎng),幾乎滿場(chǎng)都是罵人的唾沫星子。全世界的官場(chǎng)都欠罵,但聊起教育和足球,未必隨時(shí)痛心疾首國(guó)將不國(guó)的樣子吧。考你 “怒艴”、“甾醇”、“碌碡”、“饸饹”……不妨看成孔乙己?jiǎn)柲丬钕愣沟摹败睢毕旅嬗心乃姆N寫(xiě)法,答不上來(lái)大可一笑了之,揚(yáng)長(zhǎng)而去,何必動(dòng)氣呢。
如今人人隨身攜帶觸屏小鍵盤(pán)和拼音輸入法,提筆忘字反而是常態(tài)了。網(wǎng)購(gòu)時(shí)問(wèn)賣(mài)家“你能活到付款嗎”,其實(shí)對(duì)方也真不以為忤,還是會(huì)“親”你的。電視臺(tái)舉辦漢字比賽,對(duì)維持中國(guó)人的文字水平而言有好處。自從有人在高考時(shí)用甲骨文作文,官方態(tài)度已經(jīng)明確,高校錄取對(duì)文字上的各種招數(shù)不再另眼相看了,居然還有中學(xué)生愿意參加此類“性價(jià)比”不高的節(jié)目,這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既然是不含功利的娛樂(lè)比賽,題目難一點(diǎn)也未嘗不可,看過(guò)美國(guó)小孩拼寫(xiě)比賽的詞匯嗎?再看看沖擊吉尼斯紀(jì)錄的那些項(xiàng)目,那才真是無(wú)聊得喪心病狂、令人發(fā)指呢。一個(gè)正常的社會(huì),應(yīng)該允許一小部分人鉆鉆牛角尖,比如做一個(gè)全世界最大最重的蛋撻,或者問(wèn)一問(wèn)“回”字有幾種寫(xiě)法,學(xué)一學(xué)吐火羅語(yǔ)的數(shù)與格。
不過(guò),罵考試,尤其是罵那種有點(diǎn)難度的考試,是最安全、最省力,也最容易收獲共鳴的,“聽(tīng)寫(xiě)大會(huì)”挨罵不足為奇,生活中更是處處都能聽(tīng)到類似的習(xí)慣性吐槽——中考、高考,你總不能一笑了之揚(yáng)長(zhǎng)而去吧。上海最近提出加大高中會(huì)考在高校擇優(yōu)錄取過(guò)程中的權(quán)重,江蘇正醞釀未來(lái)高考時(shí)不把英語(yǔ)成績(jī)計(jì)入總分……幾乎每一項(xiàng)嘗試都會(huì)迎來(lái)罵聲一片。那么,維持原狀呢?敢,罵死你不償命!
開(kāi)罵的多是家長(zhǎng)。魯迅寫(xiě)過(guò)怎樣做父親的指南,據(jù)說(shuō)現(xiàn)在他的文章都被陸續(xù)請(qǐng)出了中學(xué)教科書(shū)。不過(guò),怎樣做家長(zhǎng),當(dāng)前倒正需要這樣的指南。我以為,做家長(zhǎng)的首要任務(wù),是淡定地和孩子一起認(rèn)清現(xiàn)實(shí),尋找出路,而不是依賴習(xí)慣性吐槽以減壓。
人云亦云的誤區(qū)
吐槽而有新意并不容易,大多是人云亦云,只是為社會(huì)的氣場(chǎng)增加一些負(fù)面情緒而已。關(guān)于教育問(wèn)題(尤其是基礎(chǔ)教育)的大量吐槽,鬼打墻,繞圈圈,心態(tài)不好,自然影響思考質(zhì)量。
比如,國(guó)外的孩子學(xué)習(xí)都很輕松,都能快樂(lè)健康地成長(zhǎng),不像中國(guó)孩子學(xué)海無(wú)涯苦作舟,每天三更燈火五更雞的。于是眾人點(diǎn)頭嘖嘖贊同,很少會(huì)追問(wèn)一下:國(guó)外是哪里?輕松的是哪些孩子?
說(shuō)到辛苦,首先想到的是課外補(bǔ)習(xí)。最近的一個(gè)雙休日,筆者在上海某教育培訓(xùn)機(jī)構(gòu)看到了這樣一幕:早上9點(diǎn)孩子從各個(gè)方向涌進(jìn)教室開(kāi)始上課。11點(diǎn)半,結(jié)束上午課程的孩子們沖出教室到街上買(mǎi)吃的,有些周到的家長(zhǎng)已經(jīng)早早買(mǎi)好了盒飯,送到已顯疲態(tài)的孩子手中。第二場(chǎng)是從12點(diǎn)開(kāi)始的,也就是說(shuō)午飯和休息時(shí)間一共只有半小時(shí)。為什么這么趕?因?yàn)橄挛邕€有第三場(chǎng)呢,全部結(jié)束已是暝色入高樓了。這些孩子用雙休日的一天完成數(shù)理化三門(mén)課程的課外學(xué)習(xí),另一天要對(duì)付的是學(xué)校布置的大量作業(yè),甚至還會(huì)抽出時(shí)間補(bǔ)習(xí)英語(yǔ)、語(yǔ)文……
這樣辛苦值得嗎?家長(zhǎng)們說(shuō),這是為了在名校的自主招生考試中取得優(yōu)勢(shì),提早拿到入場(chǎng)券。對(duì)這群心氣頗高的孩子來(lái)說(shuō),如此場(chǎng)景是有普遍性的。有的雖不參加培訓(xùn)機(jī)構(gòu)的補(bǔ)習(xí),但請(qǐng)了家教,或者參加幾戶家庭自行組織的“團(tuán)購(gòu)課程”,還有的會(huì)參與網(wǎng)課培訓(xùn)。
挑戰(zhàn)名校自主招生的自然是成績(jī)優(yōu)異的孩子,他們算不算辛苦,也應(yīng)該拿那些正在沖擊哈佛、耶魯?shù)让5拿绹?guó)中學(xué)生來(lái)比較才合理。據(jù)我所知,大洋彼岸的那一群也是常常忙得沒(méi)時(shí)間吃午飯的。無(wú)論在哪里,想攀到金字塔的頂端都要拼搏,如果只是在塔底下溜達(dá)溜達(dá),固然免了出汗,風(fēng)景卻也不同。道理就是這么簡(jiǎn)單。更何況中國(guó)這種窮地方的娃要像瑞士的、瑞典的孩子那樣悠閑,中國(guó)夢(mèng)就永遠(yuǎn)只能在床上做做了。
有人說(shuō),中國(guó)孩子如此辛苦,大大抑制了創(chuàng)造力的生發(fā),于是中國(guó)人與諾獎(jiǎng)無(wú)緣。即使參與這種歡樂(lè)的吐槽游戲,家長(zhǎng)的頭腦也一定要清醒:辛苦也好,不辛苦也罷,諾獎(jiǎng)本來(lái)就和絕大多數(shù)人無(wú)緣。如果在培養(yǎng)自家孩子的過(guò)程中,時(shí)時(shí)刻刻把奪取諾獎(jiǎng)懸為目標(biāo),或者相信了輕松的孩子獲得諾獎(jiǎng)的可能性更大,那只能像發(fā)票刮獎(jiǎng)一樣“祝您好運(yùn)”了。另外,巨貪張曙光參評(píng)院士的那2300萬(wàn)究竟用到哪里去了?搞清楚這個(gè)簡(jiǎn)單的問(wèn)題,對(duì)中國(guó)人早日取得諾貝爾獎(jiǎng)更有幫助。孩子們的創(chuàng)造力從來(lái)不成問(wèn)題,從古到今有實(shí)力說(shuō)中國(guó)人笨的族群也許是有的,可還真不多。
“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也是近年來(lái)劇烈吐槽的對(duì)象,劇烈到甚至令人懷疑:那些起跑較快的孩子,是不是將來(lái)卻更可能輸呢?而起跑慢的孩子,是不是今后的成功機(jī)會(huì)反而更大呢?真的嗎?當(dāng)然,最狠的是否認(rèn)世界上居然有“起跑線”和“輸贏”這回事,他們說(shuō),孩子們壓根就沒(méi)在參加賽跑,也不應(yīng)該參加任何賽跑,甚至今后走上社會(huì)也沒(méi)有賽跑,因?yàn)閮r(jià)值是多元的,成功可以自己定義。真的嗎?呵呵。有人要問(wèn):賽跑也就算了,不必搞得這么嚴(yán)酷吧,比如漢字聽(tīng)寫(xiě)大會(huì),有必要考孩子們“怒艴”、“甾醇”、“碌碡”、“饸饹”嗎?理由是:區(qū)分度。一旦選手眾多,實(shí)力接近,非如此不足以決勝負(fù)。
辛苦也許難免,但為什么有人可以不勞而獲,靠拼爹過(guò)上幸福生活呢?這的確令人憤慨,可與教育有一毛錢(qián)關(guān)系嗎?事實(shí)上,基礎(chǔ)教育階段的激烈競(jìng)爭(zhēng)有一定合理性與必要性,而更值得吐槽的其他事情多了去了,比如,為什么大批優(yōu)秀學(xué)生一門(mén)心思考公務(wù)員,為什么醫(yī)學(xué)院的入學(xué)新生成績(jī)?cè)絹?lái)越差,為什么借債讀完大學(xué)卻面對(duì)蕭條的就業(yè)市場(chǎng)難以收回教育投資,為什么藍(lán)領(lǐng)的社會(huì)地位和經(jīng)濟(jì)地位無(wú)法對(duì)孩子有吸引力……
看似是教育的許多問(wèn)題,實(shí)際根子幾乎完全在“場(chǎng)外”。
于是越來(lái)越多的人打定主意帶著孩子索性離開(kāi)這個(gè)“場(chǎng)”。這是個(gè)一了百了的好辦法,只是要對(duì)另一個(gè)“場(chǎng)”的規(guī)則有心理準(zhǔn)備。地球上各處的蘋(píng)果長(zhǎng)得不一樣,卻總是往下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