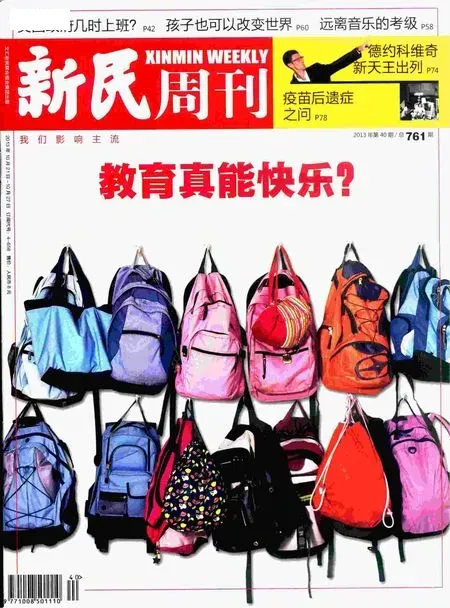被圖像拉垮的將不只是官員
劉洪波
這個時代的舉報變得簡單起來。傳統舉報靠文字描述,靠字據票根,現在只需獲取圖像了。如果獲得的是“官員不雅視頻”,簡直就可以一擊而中。考慮到圖像獲取和信息傳播的普及程度,舉報所需的只是跟蹤拍攝的耐心而已。
近年,通過照片和視頻形成輿論關注,已成常態,倒下的官員不止是雷政富、楊達才、上海四法官等等。余姚大水中一鄉鎮官員頭天被曝走訪災情要人背著過積水,第二天報道說已被免職。剛剛過去的十一長假中,有“焦作首長車司機被超車后打人”風波,那也是一段行車視頻,后來說打人車都屬私車,但尚未消除疑問,人們懷疑豫H00027、豫H00061不是私車,也猜測即使是私車,上面是否真載有“首長”。
有的圖像是妙手偶得,無意間得之。還有的圖像是自我提供,無意而成了輿論場上的證物。有的地方領導據稱在指導工作,把人加在背景上,PS技術不過關,登出的是“懸浮照”;有的官員平時很拉風,出鏡都很有派頭,集中起來就讓人看出目不暇接的名貴行頭;還有的是被人做局,一時玩得HIGH,留下錄下“十二秒”;還有的是不慎走光,本來私密的娛樂被曝光出來;還有的圖像來源神秘,發布者自稱撿到了手機或者以修電腦為業。
最具威脅的,還是一個人單槍匹馬,長時跟蹤官員,錄到圖像后公布。暫時地,人們可以看到其反腐效果。深想一下,跟蹤錄到圖像而后公布,其實還是最值得慶幸的一種跟蹤行為。如果跟蹤者是要進行人身襲擊,那又如何? 用作舉報證據的圖像生產,有時還是一種經過協調組織的購買行為。有一個例子是,大連一位女企業家因遭遇野蠻拆遷,調查大連市城管局長,舉證包括局長有5輛豪車、使用假牌、婚后兩年消費1126萬元等。這不是個人親力可為,而是有個人蹲守,還有信息懸賞征集,出價10萬元,跟公安部門懸賞捉拿的最高額度相當。從中可以看到企業家的“死嗑”精神,也可以看到其資源調動的能力。
支撐舉報人去拍攝的,是“不信他沒有問題”這樣一種認知,而事實也往往證明那些威嚴的官員真是“不查就沒有問題,一查就一定有問題”。
這些反腐圖像的生產行為,其實有比揭開腐敗官員更重要的社會含義。這種圖像生產行為,實在是當下社會狀況的喻體之一。跟蹤行為作為一種投入,有一定的產出預期,如果這一預期很難實現,那就會影響投入的熱情,但事實上圖像獲取經常是有收益的。
這種行為還可以讓人感知到某種“不抱希望”。圖像獲取者對獲得腐敗記錄的圖像有很高的預期,但對腐敗行為會得到正常的發現和查處則不抱希望,于是自力而為,把證據送到負有發現和查處之責的機構面前。
圖像的獲取者有時是分散的網民,有時是單一的個體,有時則是像斗敗城管局長的大連女企業家那樣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這些圖像生產和獲取行為都圍繞著官員而展開,實際上就是一種可以稱為“圖像政治”的民間活動。
從另一方面看,現在每有一事發生,人們幾乎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調看監控視頻”,而經常地,監控恰好在緊要處斷掉,有時是監控壞了,有時是監控留下的死角,有時則干脆就是不翼而飛,變成了空白。還有的時候,普通人的現場圖像錄制會受到禁止,例如執法隊現在經常有視頻錄制,普通人拿出手機拍攝則會被禁止。這些顯然造成了圖像控制上的可信度問題,也提示了圖像權力與圖像權利的分野,促成了人們要把圖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傾向。
“有圖有真相”作為一種樸素的觀念,為人們普遍認可。現在,它更多地發生在反腐領域,但影響并不止于反腐而已,圖像可能撬動社會。圖像生產和獲得的普遍性,可能讓人產生“真相隨手可得”的印象,但圖像控制上的官民之爭,可能表達出的仍然是兩部以片斷和截面書寫的“真相史”,而且指向絕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