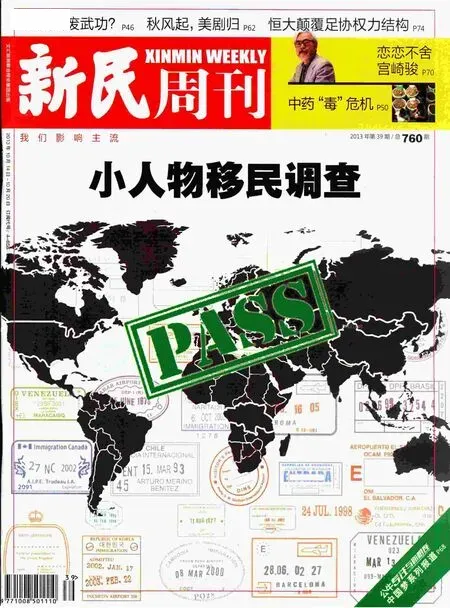被摘走的紅櫻桃
任蕙蘭


中產(chǎn)淪為藍(lán)領(lǐng)
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里有個(gè)令人唏噓的細(xì)節(jié),在國(guó)內(nèi)一號(hào)難求的心臟科專(zhuān)家,移民到了美國(guó)只能開(kāi)出租車(chē)。其實(shí)這不僅僅發(fā)生在美國(guó),也是很多國(guó)家技術(shù)移民的真實(shí)寫(xiě)照。
在宣布砍掉近30萬(wàn)積壓的技術(shù)移民申請(qǐng)之前,加拿大移民部長(zhǎng)康尼對(duì)媒體講過(guò)一個(gè)故事,他在阿爾伯特省遇到的一對(duì)夫妻來(lái)自哥倫比亞,兩人都是牙醫(yī),他們?cè)诩幽么笞龃髲B門(mén)衛(wèi)及管理員的工作。很多人都聽(tīng)過(guò)這樣令人傷心的故事,不少加拿大的出租車(chē)司機(jī)移民前是工程師或醫(yī)生。
康尼的故事同樣也發(fā)生在中國(guó)的技術(shù)移民身上。多倫多大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系教授Janet Salaff和她的中國(guó)助手許麗平曾在2000年初做過(guò)一個(gè)針對(duì)中國(guó)技術(shù)移民的課題研究,采訪(fǎng)了100位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國(guó)技術(shù)移民,其中大部分在國(guó)內(nèi)是工程師或醫(yī)生,他們幾乎都面臨人力資源貶值的窘境。
中國(guó)的技術(shù)移民大都正值壯年,擁有良好的職業(yè)和教育背景。根據(jù)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間,共有2841名來(lái)自中國(guó)內(nèi)地的準(zhǔn)技術(shù)移民報(bào)名參加了加拿大移民融入計(jì)劃,這是一個(gè)為來(lái)自海外的準(zhǔn)技術(shù)移民提供信息,幫助他們了解加拿大勞工市場(chǎng)動(dòng)態(tài)的政府項(xiàng)目,其中有2038人報(bào)讀了該計(jì)劃開(kāi)辦的迎新工作坊。
從2038名中國(guó)內(nèi)地準(zhǔn)技術(shù)移民的年齡來(lái)看,大部分處在事業(yè)黃金年齡。介于21歲至35歲的人數(shù)最多,共有1081人,比例為53%;其次為年齡介于36歲至50歲之間的準(zhǔn)移民,比例占45%。從學(xué)歷背景來(lái)看,這2038名技術(shù)移民中擁有碩士學(xué)位的人數(shù)最多,共有964人,比例為49%;擁有學(xué)士學(xué)位的比例為29%,擁有博士學(xué)位的比例為9%。
但是,專(zhuān)業(yè)背景和年富力強(qiáng)為何沒(méi)能成為成功就業(yè)的保證?
從Janet Salaff和許麗平的研究結(jié)果來(lái)看,大部分人是倒在了外國(guó)專(zhuān)業(yè)人才的認(rèn)證上。在加拿大,所有需要大學(xué)以上學(xué)歷的專(zhuān)業(yè),都有自己的協(xié)會(huì)和其制定的一套認(rèn)證監(jiān)管制度,對(duì)外國(guó)證書(shū)幾乎一概不認(rèn)。經(jīng)濟(jì)收入和社會(huì)地位越高的專(zhuān)業(yè),認(rèn)證制度越復(fù)雜嚴(yán)格。
以工程師為例,2000年,1.5萬(wàn)人入境時(shí)申報(bào)在加拿大準(zhǔn)備從事的職業(yè)是工程師,加拿大工程師協(xié)會(huì)(CCPE)估計(jì)同一年從加拿大大學(xué)畢業(yè)并獲取工程師資格的人數(shù)只有1萬(wàn)人左右。可以看出加拿大非常依賴(lài)“進(jìn)口”工程師。
在所有外來(lái)工程師中,中國(guó)工程師的“產(chǎn)量”很大。
Janet Salaff采訪(fǎng)的50對(duì)中國(guó)移民夫婦中,丈夫是工程師的就有41位,全部有5年以上工作經(jīng)驗(yàn),但其中只有2位拿到加拿大工程師牌照。
不在加拿大本地接受工程師教育和培訓(xùn)的移民要通過(guò)工程師協(xié)會(huì)認(rèn)證,必須經(jīng)過(guò)三個(gè)主要考察項(xiàng)目。一是提交工程師學(xué)歷、成績(jī)單和文憑,如果審核不合格,就要在加拿大學(xué)校重讀部分課程。二是具備3-4年工程師工作經(jīng)歷,其中至少一年在加拿大公司實(shí)習(xí),這家公司必須雇有兩名以上工程師協(xié)會(huì)認(rèn)可的工程師。移民在滿(mǎn)足前兩個(gè)條件后,才有資格參加專(zhuān)業(yè)考試。通過(guò)考試的佼佼者可以成為注冊(cè)工程師。
但加拿大公司在請(qǐng)人時(shí)需要有本地工作經(jīng)驗(yàn),很少會(huì)雇傭新移民,因此移民很難獲得一年的加拿大實(shí)習(xí)經(jīng)驗(yàn)。資深精英只能從繪圖員之類(lèi)的輔助工作做起,極少數(shù)會(huì)被拔擢為工程師。
受訪(fǎng)對(duì)象中,最快的一個(gè)也用了3年半時(shí)間才成為注冊(cè)工程師,而大部分人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放棄了,有些人干著和持牌工程師差不多的工作,但待遇相去甚遠(yuǎn);也有些人放低身段,以工程師背景去做熟練技工,甚至做更低的初級(jí)技工,不知哪天才能回到移民加拿大前所從事的專(zhuān)業(yè)工作水平。
工程師可以屈就技術(shù)員,移民醫(yī)生則更艱難,在加拿大行醫(y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加拿大對(duì)醫(yī)護(hù)人員需求很大,在今年5月移民局公布的24項(xiàng)職業(yè)中,醫(yī)護(hù)領(lǐng)域就有10項(xiàng)之多。加拿大人口老齡化嚴(yán)重,培養(yǎng)醫(yī)生過(guò)程漫長(zhǎng)且昂貴,因此很需要海外醫(yī)療人才。但嚴(yán)格的本地化過(guò)程和官僚的認(rèn)證制度令移民醫(yī)生們無(wú)用武之地。
移民拿醫(yī)生牌照需要通過(guò)醫(yī)生評(píng)估考試,加拿大不認(rèn)可移民在中國(guó)的教育經(jīng)歷和工作經(jīng)驗(yàn),因此申請(qǐng)者在通過(guò)語(yǔ)言關(guān)后,要花2-3年時(shí)間全職讀書(shū)修專(zhuān)業(yè)課,參加三項(xiàng)專(zhuān)業(yè)考試,學(xué)費(fèi)、考試費(fèi)以及全職讀書(shū)期間的生活費(fèi)讓移民很難承受。
除此以外,申請(qǐng)人還要完成12個(gè)月的實(shí)習(xí)。醫(yī)學(xué)生實(shí)習(xí)是由加拿大駐診中介負(fù)責(zé),原則是先照顧本國(guó)醫(yī)學(xué)生。2002年,496名申請(qǐng)駐診的非加拿大醫(yī)科學(xué)校畢業(yè)生中只有83名獲得機(jī)會(huì),概率只有16.7%。在1998年這個(gè)數(shù)字還不到10%,1999年在15%上下。
即便移民愿意勒緊腰帶讀幾年書(shū),也未必能搶到不足兩成的實(shí)習(xí)機(jī)會(huì),所以很多人不得不放棄。一位北京新生兒護(hù)理中心的副主任醫(yī)師只能在加拿大診所做翻譯員,業(yè)余去敬老院當(dāng)護(hù)理。嚴(yán)格的認(rèn)證制度讓這些名醫(yī)連開(kāi)診所專(zhuān)門(mén)為中國(guó)移民服務(wù)的機(jī)會(huì)都沒(méi)有。
窮太太和富太太
在技術(shù)移民群體中,女性的就業(yè)下降幅度更大,她們不但要接受專(zhuān)業(yè)、學(xué)歷得不到認(rèn)可而導(dǎo)致的人力資源貶值,還要為支持丈夫事業(yè)、照顧家庭而犧牲自己的專(zhuān)業(yè)。
《金融時(shí)報(bào)》的專(zhuān)欄作者一多曾撰文描述過(guò)技術(shù)移民女性的尷尬生存狀況。她把將定居在溫哥華的中國(guó)女人們劃分為窮太太和富太太兩大群體。“窮太太大多來(lái)源于技術(shù)移民,有著高學(xué)歷、豐富的工作經(jīng)驗(yàn)和不怎么豐厚的物質(zhì)基礎(chǔ),一般屬于來(lái)了就趕緊提升語(yǔ)言、找工作的人群。富太太則大多是投資移民,學(xué)歷未必高但財(cái)富很可觀,多數(shù)在國(guó)內(nèi)有著自己的家族企業(yè),來(lái)了之后學(xué)英語(yǔ)就是看看‘西洋景,順便結(jié)識(shí)些朋友打發(fā)時(shí)間,主要精力用來(lái)買(mǎi)房子置地,為推高當(dāng)?shù)胤績(jī)r(jià)做貢獻(xiàn)。”
窮太太和富太太的交集是在ESL語(yǔ)言學(xué)校,這是加拿大政府為移民提供的免費(fèi)語(yǔ)言培訓(xùn)服務(wù)。ESL語(yǔ)言學(xué)校里除了學(xué)習(xí)英語(yǔ),更多是幫助新移民在學(xué)習(xí)中了解當(dāng)?shù)匚幕⑸鐣?huì)機(jī)構(gòu)、行為規(guī)則。兩個(gè)群體在那里展示出完全不同的生態(tài)。
ESL學(xué)校門(mén)前停車(chē)場(chǎng)內(nèi),在教師的專(zhuān)用停車(chē)位上停著的都是很簡(jiǎn)單的日系小型車(chē)或北美非常大眾化的轎車(chē)。富太太們的座駕區(qū)域則不亞于高端車(chē)展,新款、高配的寶馬、奔馳、卡宴、蘭博基尼、路虎。窮太太們以普通車(chē)甚至二手車(chē)為代步工具。
“一個(gè)班如果有超過(guò)三個(gè)中國(guó)移民富太太,那么這個(gè)英語(yǔ)班的性質(zhì)很可能就變成商學(xué)院了,成了富太太們交流房地產(chǎn)買(mǎi)賣(mài)案例和心得的場(chǎng)所。”富太太們每天必然是駕著豪車(chē)來(lái)上課,拎著名牌包,衣著時(shí)尚光鮮,甚至珠光寶氣,把課堂直接當(dāng)成了奢侈品的秀場(chǎng)。
她們的張揚(yáng)很快讓當(dāng)?shù)亟處熜睦黼y以平衡:他們是土生土長(zhǎng)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當(dāng)?shù)厝耍廊恢荒荛_(kāi)著自己非常簡(jiǎn)陋的車(chē)為衣食奔波,向政府繳納可觀的稅收,然后政府用他們的錢(qián)為這些大富大貴的海外移民提供著免費(fèi)服務(wù)。富太太們還成為溫哥華高昂房?jī)r(jià)的始作俑者,讓這座城市失去了世界宜居城市一度高居榜首的排名。
富太太要面對(duì)的是本地人的極端排斥,窮太太們要對(duì)抗的則是生活壓力。在Janet Salaff采訪(fǎng)的50對(duì)夫婦中,50位妻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為13.9年(高中程度為12年,大專(zhuān)為14年),她們中有證券交易所的副總經(jīng)理、服裝廠廠長(zhǎng)、主任醫(yī)師、主任麻醉師等。
為了保證丈夫接受英文或?qū)I(yè)培訓(xùn),以便盡快找到好工作,妻子們迅速進(jìn)入打工行列,維持基本家庭開(kāi)支。一位妻子為了支持丈夫考工程師執(zhí)照,甘愿當(dāng)制衣工人,她原來(lái)是服裝廠副廠長(zhǎng)。
50位妻子中有17人在國(guó)內(nèi)從事工程師類(lèi)別工作,但在加拿大只有2人拿到移民前相當(dāng)?shù)穆毼唬?人降至技術(shù)員,其他14人有的是服裝廠女工,有的做咖啡店店員,也有從事傳銷(xiāo)或保險(xiǎn)。
女性技術(shù)移民在國(guó)內(nèi)努力學(xué)得的專(zhuān)業(yè)技能蒙上塵埃,她們與丈夫事業(yè)差距越來(lái)越大,也與自己本初的人生和目標(biāo)越來(lái)越遠(yuǎn)。
人才輸出國(guó)的悲哀
縱觀歷史,移民往往為輸入國(guó)帶來(lái)蓬勃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19世紀(jì)50年代到20世紀(jì)30年代的經(jīng)濟(jì)大蕭條,數(shù)以百萬(wàn)計(jì)的工人從經(jīng)濟(jì)停滯的北歐、東歐及南歐國(guó)家涌入美國(guó),1200萬(wàn)移民在紐約港的艾里斯島登錄接受移民檢查,他們推動(dòng)了美國(guó)作為工業(yè)強(qiáng)國(guó)的興起。
如果國(guó)內(nèi)失業(yè)問(wèn)題嚴(yán)重,出境移民對(duì)輸出國(guó)而言,因?yàn)榫徑饩蜆I(yè)競(jìng)爭(zhēng)而有積極意義,這是菲律賓政府鼓勵(lì)保姆出境的一個(gè)原因,另一方面是寄錢(qián)回來(lái)。同樣的原因下拉美人熱衷向美國(guó)移民,就像美劇《魔鬼女傭》里描述的,在美國(guó)比佛利富人區(qū)工作的保姆大部分來(lái)自拉美。
但低技術(shù)移民容易沖擊本地的勞動(dòng)市場(chǎng),尤其是對(duì)本地低技術(shù)工人的工資水平產(chǎn)生影響。紐約做過(guò)的一份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參與程度和收入狀況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男性非裔美國(guó)人排名下降,正是移民入境最多時(shí)期。非裔美國(guó)人在整個(gè)勞動(dòng)市場(chǎng)中最脆弱,受到的影響也最突出。
富國(guó)更愿意積極招募高技術(shù)人才,不惜搜羅全球,像摘櫻桃一樣把最優(yōu)秀人才納入囊中。二戰(zhàn)后歐洲最優(yōu)秀的科學(xué)家移民北美,那里工資水平高,研究經(jīng)費(fèi)寬裕,設(shè)備先進(jìn)。世界的科研中心也從歐洲轉(zhuǎn)到美國(guó)。
出去的高技術(shù)移民是最有創(chuàng)業(yè)精神、受教育最高的人群。如果技術(shù)在本國(guó)不匱乏,像印度大量IT人才出境,因?yàn)楹芏嗄贻p人都有技術(shù)所以對(duì)本國(guó)產(chǎn)業(yè)影響不大。但更常見(jiàn)的是,流動(dòng)使本身缺乏技術(shù)的國(guó)家雪上加霜。
華盛頓人道問(wèn)題研究員Khalid Koser在《國(guó)際移民》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國(guó)家的醫(yī)療人員移民歐美,2000年起,在英國(guó)注冊(cè)工作的來(lái)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國(guó)家的護(hù)士有16000名,贊比亞獨(dú)立以來(lái)接受過(guò)培訓(xùn)的醫(yī)生中,600人只有50人留在當(dāng)?shù)匦嗅t(yī)。在英國(guó)曼徹斯特市工作的馬拉維醫(yī)生人數(shù)超過(guò)馬拉維全國(guó)醫(yī)生總數(shù)。醫(yī)療人員移民令窮國(guó)嬰兒死亡率患病率超高,對(duì)這些國(guó)家發(fā)展造成負(fù)面影響。
20世紀(jì)70、80年代,來(lái)自亞洲的國(guó)際移民增長(zhǎng)迅猛,其目的地主要是北美、澳大利亞和海灣國(guó)家。2000年,美國(guó)的亞洲移民超過(guò)700萬(wàn),中國(guó)每年入境美國(guó)的移民在人數(shù)上僅次于墨西哥。根據(jù)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的估計(jì),澳大利亞亞裔人口超過(guò)100萬(wàn),占全國(guó)人口的5%。
高技術(shù)人才的流失將動(dòng)搖中國(guó)的競(jìng)爭(zhēng)力,本國(guó)看不到教育和培訓(xùn)投資的任何回報(bào),面對(duì)櫻桃被摘去后空蕩蕩的果園興嘆。而移居他國(guó)的技術(shù)人才也未必如意,不得不付出種種融入成本,并且接受自己在異國(guó)他鄉(xiāng)降低幾個(gè)檔次的社會(hu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