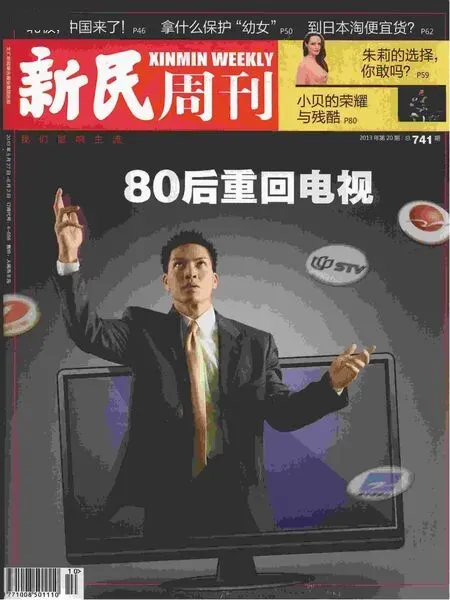超越疆界的智者
孟暉
在香港海港城葉一堂書店翻到一本英文傳記《中國的戀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一開卷就講一個叫Joseph Needham的英國人在1943年歷經險阻來到他一生熱愛的中國。讀了幾頁忽然明白,這是一本李約瑟傳呀。
說來夠窘,此前我一直不曾留意李約瑟的本名是Joseph Needham。該書的作者西蒙·溫徹斯特(Simon Winchester)是撰寫科學家傳記的高手,《中國的戀人》是他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佳作之一。讀來果然準確嚴謹又生動有趣,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理解了李約瑟之所以能夠出現的那個學術與思想的黃金氛圍。
最讓人敬服的事例之一,1948年,李約瑟向劍橋大學出版社送交了一份兩頁的提綱,闡述撰寫《科學與文明在中國》(國內一般譯成《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設想,結果校方立刻認識到這一計劃意義非常,遂免除他一切教學工作,讓他從此在歷史達數百年之古的學院辦公室里潛心學術研究。同樣感人的是,李約瑟“二戰”期間曾經在中國與竺可楨短暫會面,談到自己的想法,結果戰后忽然收到竺可楨跨洋運來、無償相贈的大批資料,包括一套《古今圖書集成》。盡管李約瑟的強烈左翼立場在冷戰環境中惹出各種麻煩,但隨著他的巨著一卷卷出版,西方學術界尤其是英國給予這位驕子以各種榮譽,認為“他的成果讓他,他的學院,他的大學,他的國家以及一個開明的西方世界無限驕傲”。
不過,很可惜,西蒙·溫徹斯特完全沒有理解立傳的對象,對李約瑟及其學術的介紹流于庸俗。他一味強調李約瑟之于中國似乎宿命式的迷戀,把這解釋成他的人生與工作的出發點、內容與終點,好像李約瑟是個原教旨式的中國優越論的迷信者與鼓吹者,如此的褻瀆令人難以容忍。尾章居然說當代中國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自認居于世界中心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本來作者愛咋認為是他的事,但全書終句竟是:“李約瑟對此不會感到惶恐,他甚至一點也不會覺得驚奇。”這是硬把李約瑟與西方人的一個頑固成見拉在一起,而這位曾被預測將會是現代伊拉斯謨的學者一生都在努力破除成見。如果他真的是個中了邪的腦殘粉,又豈能蒙騙國際學術界。
我曾經對水車、北宋蘇頌建造的水運儀象臺、元代皇宮中的“燈漏”深感興趣,為此而翻閱《科學與文明在中國》的相關章節,結果立刻被一個遼闊恢宏卻又精細嚴謹的科學世界震住。對于任何一項技術,書中都是將歷史上諸大文明區連貫在一起探討,典型如《時鐘機構和各文化間的關系》一節。不管中國怎樣燃燒著李約瑟的激情,但在研究中,他與助手們都秉持科學家的嚴謹與客觀,傾力描繪技術與觀念的全面景觀。
我認為,在西方文明的巔峰時刻,中國讓李約瑟敏感地發覺,多種技術發明的歷史、人類文明的歷史遠遠超出歐洲人的既有認知。通過溯源古代中國,由此連帶起其他文明,人類的智慧史的縱深度與廣闊度被大大拉長——“咱人類厲害著呢!”由此產生的喜悅與興奮結晶成他對中國的癡愛。在一個中國戀人的表象下,實際上活躍的是人類智慧的戀人。看他書中關于一項技術的探討在希臘、羅馬、印度、拜占庭、阿拉伯、歐洲與中國、朝鮮等地之間縱橫穿插,你能清晰聽到一只夜鶯因人類而動聽地歌唱。
毫無疑問,今天我們中國人關于自己過去的研究,一如任何人對任何地區的研究,都必須在李約瑟的成就上展開。李約瑟的成果雖然驚人,但仍然只是開始,漫長的路正等著后來的勇者。不過,這位巨匠還有一層教導意義。在大英帝國的光輝里,他卻奮于讓學術研究、讓知識生產、讓歷史認識突破帝國的地理疆界、突破歐洲語言的疆界。對于我們來說,在觀察傳統現象時需突破國家的有形疆界與漢語文獻的無形疆界,恐怕也是早晚要面對的關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