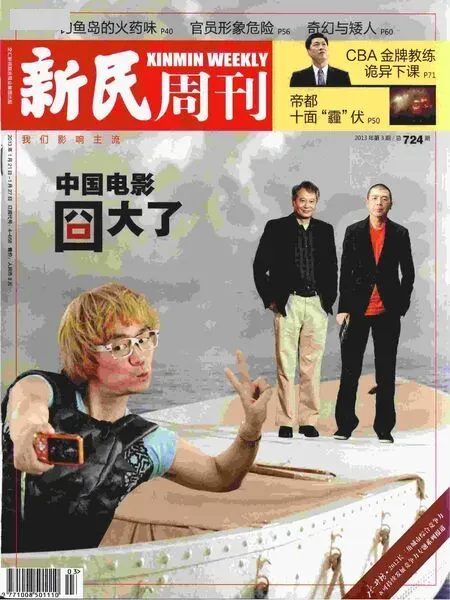生煎&上海
沈嘉祿
上周,上海市旅游局政務微博“@樂游上海”上完成了首期“喜歡上海的99個理由”網絡征集活動,網友針對活動主辦方設定的“地鐵沿線風景”、“上海美食”、“老弄堂·懷舊”、“上海夜色”、“上海正能量”五個微話題發表意見,結果在近60萬條“理由”中,關乎美食的“理由”最為生猛、最為麻辣,吃貨們毫不吝嗇地使用重量級的贊美詞來表達對城市生活的態度。
《舌尖上的中國》熱播后,我先后接到十多家媒體的采訪要求,均予婉拒,一則因為本職工作已經叫我手忙腳亂,二則是不再想以大腹便便的吃貨形象招搖過市。但旅游局請我去新浪當嘉賓,專門回答美食方面的問題,考慮到不出形象,我就去了。結果那天下午,網友的問題劈面而來,有的請我指點美食路徑,有的請我提供實戰秘辛,還有的請我分享美食感受,一個多小時飛一般過去,彼此意猶未盡。沒人以魚翅鮑魚炫富,只談生煎小籠濃油赤醬,懷舊是總基調,尋訪賽過奪寶游戲,草根美食成了共同的饗宴。若說來自外省的新上海人對此話題還有額外的想法,就是當他面對一張蔥油餅、一塊糯米糕從鄉村迢迢千里來到昔日十里洋場、最終得以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前世今生,就會對照自己在上海灘闖蕩的種種艱難與機緣,陡增美夢成真的信心。在飲食這檔俗事上,新老上海人達成了高度共識。
縱覽世界文明史,每座對周邊產生輻射力的大城市似乎都是移民行為的結果,都有美食從四面八方引進,上海也如此,只不過在三次移民大潮中,開放度更大,風味美食積淀更多一點罷了。但就是出于生存需要的業態形成,聚沙成塔、百川歸海,造成了上海美食天堂的色香現實。不過僅僅從味覺層面來梳理喜歡上海的理由,也太過表面化了,其實,無論男女老少,喜歡上海的風味美食,都基于多種物象的疊加。
比如說,在城市高速發展的匆匆腳步中,殘存的風味美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蝕風化。優質的原料由于種種原因而不復存在,或被打亂了原有的譜系,比如做刀魚面的長江刀魚也所剩無幾,大多數河海鮮和家禽、家畜都實現了工業化養殖,記憶中的原有風味就不復存在了。在制作環節,手藝精神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兢兢業業的誠信勞動被當作傻瓜,投機取巧、以次充好、惡意造假、濫用添加劑和色素等非法行為,反倒成為致富新思路。
還有,風味小吃的生態也被粗暴覆蓋了。過去,風味小吃與城市的文化娛樂密不可分,人們可以在茶館里吃到各種糕點,現在幾成天寶遺事,三五知己隨意小酌的酒樓也被一再擠壓,有此需求的老百姓只能在路燈下的大排檔抿一口,與城管玩貓捉老鼠游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關部門將當年串街走巷的叫賣聲視作非遺項目,但重視的結果只不過化為表演性質的歌謠,老上海市井風情早化作隨風而去的黃葉,零落作泥。最后一點是,某些經營者對商業利潤的過度追逐,將價廉物美的民間小吃逐出門外,而飯店酒樓里彌漫不去的奢靡腐敗風氣又引起路人側目,千夫所指。
凡此種種,都是人們在春風秋雨中品嘗風味小吃時隱約感知而一時又說不上來的,欣喜、憂慮、感念、傷時、回望、追憶……或許都有一點,與椒桂醋醬一起構成了現世生活的復合滋味。在投機致富、權錢交易、資本游戲等潛規則和強人傳奇的流言中,越發無助與寥落的老百姓只能舉起毛竹筷子挾起一只剛出鍋的生煎饅頭移至嘴邊,去吮吸那期待之中、與兒時記憶相去不遠的肉汁。所以,人們珍愛風味美食,歸根結蒂是因為風味美食不僅予人味蕾的豐富體驗與心理安慰,而且在價格、經營、環境及人際關系等方面,可以為社會底層的民眾所謹慎把握,那種在卑微享受中獲得的小樂趣,最終酵化成我們共同的精神財富,不允許別人奪走。
愛上海,體味上海,成就上海,就從一只生煎饅頭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