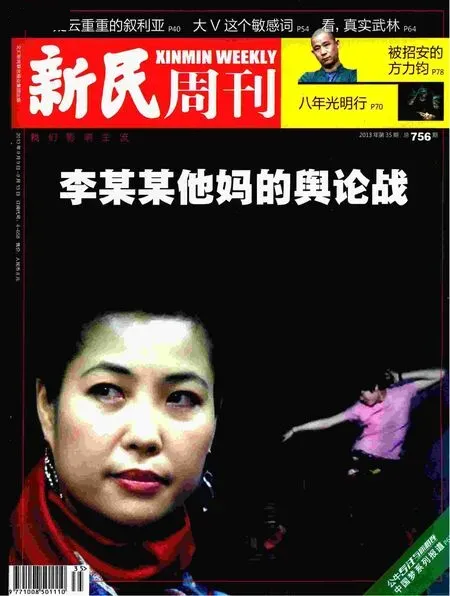讓謠言止于法治
王琳
一場指向網絡謠言的“嚴打”行動正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先是秦火火和立二拆四在北京被刑拘,再有各地爭相發布“嚴打”成果,一大批“推手”和“水軍”紛紛落網。從輿情反饋來看,絕大多數民眾對網絡謠言持否定態度。但在不同的輿論場上,對“嚴打”網絡謠言行動的評價不盡一致。
不一致并不是對網絡謠言的或贊或彈,而在于如何認定“網絡謠言”,以及如何追究網絡制謠、傳謠者的責任。什么是謠言、什么不是謠言,看上去似乎簡單明了:不實的傳言,就是謠言。偏離真相,甚至與真相背道而馳的,都是謠言。但如果將時間因素考慮進來,我們就會發現,賴以認定謠言的“真相”其實也存在多變。尤其是當真相關聯到特定群體的利益時,既得利益者總是會想方設法來阻撓真相浮出水面。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就現有信息提出合理推斷(哪怕并非最終的事實),也是輿論監督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如近日受審的“表叔”楊達才,因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間和一個不恰當的地點,露出了不恰當的微笑,成為網民“人肉搜索”的對象。由于缺乏足夠的信息公開,更缺乏相應的調查取證權,網民只能依賴于對有楊達才影像的新聞照片進行分析。這種分析固然具有“技術含量”,但就算再專業的鑒表師,也難以保證他所認定的手表型號與手表價格就是不差分毫的“真相”。輿論監督所起到的作用其實更多是在為司法機關提供可資繼續追尋真相的“線索”,而不是在提供一個結果。因此我們不能說,只要網民在網上發表了對楊達才所戴手表的言論與事實有偏差,就認為該網民在“造謠、傳謠”。
對某事物的認識,往往是一個過程,而不僅僅是一個結果。如果否定了求證的過程,那就等于否定了言論自由。認定網絡謠言絕不能簡單地抽出某個具體的時間點,來對照言論與事實是否一致。發言者的主觀心態、客觀行為以及危害后果,需要綜合考量。不久前,安徽一位網民在網上將當地一次車禍10人遇難錯報成16人死亡,安徽警方據此將該網友行拘,引來網絡一片嘩然。好在警方知錯能改,迅速撤銷了該處罰決定并向事主和網民道歉。“廣州公安”(廣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和“法耀嶺南”(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更是先后援引“子產不毀鄉校”的典故,提醒同行“打擊造謠要防擴大化”。
謠言盛行,司法有責。但打擊網絡謠言亦要依法而為。從責任承擔來看,網絡制謠、傳謠者面臨的是一個覆蓋了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的責任體系。民事責任需要被侵權人的提告為前提。這次“嚴打”有別于過往,就在于警方更多指向了刑事究責。
遏制網絡謠言,理當追求常態化執法,而非運動式執法。有報道揭露某些嫌犯的網絡造謠史已有十余年。但問題恰恰在于,十余年的持續違法為何遲遲不見警方介入?“不知情”或“未接到舉報”是解釋不過去的,因為造謠、傳謠都是公開而為,而偵查是一項主動的權能,不依“有告才理”的約束。今天的成績,從另一視角看就是過去的失職。
當然法治并不排斥“專項行動”,但法治更強調常態化執法。必要的“專項行動”也不能脫離法律的軌道。比如,在遏制網絡謠言上要做到公平公正,就不能選擇性執法。在我們這個“民以吏為師”的傳統淵源深厚的國度,“官謠”之惡遠甚于“民謠”。從“畝產上萬斤”到“休假式治療”,受此蒙蔽的民眾在求得真相的道路上,往往山高水長。謠言止于公開,謠言也受制于法治。執法理當由事到人,而不應由人到事,否則,難免給人以“犯事于東,獲罪于西”的疑問。而哪怕是作為專項行動的“嚴打”,也應法內從嚴,而不能法外施罰。須知,改革開放之后的四次“嚴打”所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就在這“依法”二字。
(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