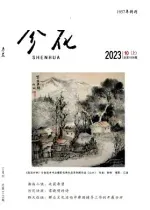攤餅
周成新
周日難得休息,早晨起床岳母特地用面粉和著雞蛋做了一些面餅,方狀的、碗狀的,金黃色的、香噴噴的,十分誘人。
吃著這些形狀各異、色澤光鮮的面餅,不由得讓我想起家鄉的攤餅,一種將面粉調成面糊,用老虎灶燒火,在尖底鍋上攤成的薄餅。
與路邊平底攤餅不同的是,家鄉的攤餅是在老虎灶上用燒菜的尖底鍋攤成的,由于尖底鍋上攤餅不像平底鍋那樣順溜,面糊容易下滑,因此難度比較高。
八十年代物資匱乏,鄉下人家為了填飽肚子,常喜歡在吃飯的時候烙餅,茄餅、玉米餅、薄荷餅成了各式各樣的主食。喝稀粥時,一手端碗,一手咬餅,只有這樣肚子到中午才不會餓著。
在諸多的烙餅中,我唯獨對攤餅情有獨鐘。不僅是因為它薄如紙片,香脆可口,更因為攤餅的過程本身就是一門藝術。站在灶前的人不僅要心態平和,運籌帷幄,還要指揮若定,容不得半點急躁和慌亂。
水瓢舀來面粉,和水用筷子使勁調成糊狀,糊要做到不稀不稠,將面粉打上勁,攤餅才會有韌勁。面糊調好后,待鍋底溫度升高、變穩,端起碗沿著鍋沿迅速轉上一圈,讓面糊均勻地由碗中流出。一圈轉好,用鍋鏟將碗邊上殘留的面糊刮掉,然后趕緊再用鍋鏟沿著剛才那倒糊的一條線往下至鍋底劃圈,目的是使面糊能夠均勻地分布于鍋中,這是攤餅最為關鍵的一步,不能攤得厚一塊、薄一塊,更不能這一處堆積著,那一處卻露著一個洞,否則整個餅就不夠完整。
當面糊均勻地布滿鍋底的時候,才可以長吁一口氣,靜等面糊成型。成型后的面糊呈鍋形,貼著整個鍋壁,并能夠從鍋壁上起出來了,這時不用再擔心火的大小了,可以將這個面鍋隨意移動,哪兒沒烤好,就將這一塊拖到火大的地方。等到面鍋每一處都烤熟了,烤脆了,將事先切好的韭菜或蔥末大把灑上去,再放些鹽、油,用鍋鏟攤均勻了,這時整個廚房都彌漫了一股特殊的香氣,讓人饞涎欲滴。這時候,攤餅就做成了。倘若喜歡甜的,可以用紅糖代替食鹽,大把的紅糖灑在餅上,紅糖受熱、受潮后迅速融化到鍋餅中,一個香甜的攤餅也就形成。
燒火也是攤餅的關鍵,過旺,面糊粘住鍋壁,容易焦糊;過弱,面糊粘不住鍋壁,容易下滑。只有在溫度適中時,面糊才能粘住鍋壁,鍋鏟才能及時將不平的面糊攤均勻。因此,沒有過好的手藝和心態是絕對攤不成好餅的。
對于手藝好的人來說,燒火、攤餅一人就可完成,而且一鍋即成。對于手藝差或學藝不精的人來說,不僅需要找人配合,就是攤餅至少也需要三鍋以上才能成型。起得過早,容易粘牙;起得過晚,容易焦糊。
攤餅做成后,用鍋鏟托著,用手扶著鍋形的攤餅從廚房出來,穩穩地放到飯桌上早已準備好的盤子中時,攤餅如一個荷花形的立體雕塑豎立在盤子的中間。吃的時候,可以用手撕開,一片一片地卷成卷,和著稀飯或者茶水吃,咬著夠勁,嚼得夠味,別有一番滋味。
如今,家鄉的生活條件變好了,攤餅很少再被提上飯桌。每當吃餅或者在菜場看到平底鍋攤餅時,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家鄉的攤餅,腦海仿佛又浮現出兒時母親依在灶邊攤餅的樣子,那股誘人的蔥油、紅糖香仿佛又讓我回到了那純真的童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