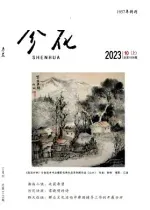學琴小記
姜燕
摘要:現今社會中,紛繁嘈雜,奔波忙碌的人們似乎忘記了如何收心,古琴借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雖有部分人在其中裝神弄鬼,卻真正有大批人將精神回歸,寄托于琴上。他們崇尚自然,崇尚靜逸,把古琴作為了自娛自樂的樂器。
關鍵詞:古琴;禮樂;儒士
[中圖分類號]:B835 [文獻標識碼]:A
琴,古代專指古琴。禮樂的至高樂器,古代儒士的才德“琴棋書畫”中,琴屬首位。凡鼓琴者必是修養較高之人。“士無故不撤琴”表明了琴在古代文人中的崇高地位。而琴也是文人雅士情意之間的傳遞工具。無論是孔子不得志時的《龜山操》,亦或是不愿與鄙夫為伍的《猗蘭操》,無不滲透著古代文人豐厚的思想情感。琴,成了文人雅士傳遞內心情感的重要工具之一。
現存最早的《流水》曲譜見載于明代初期朱權的《神奇秘譜》。其后刊載有《流水》一曲的琴譜多達三十余種。其中又以《天聞閣琴譜》中所載的川派琴家張孔山的《流水》最為著名。1977年8月22日,由著名琴家管平湖演奏的琴曲《流水》,被錄入美國“航天者”太空飛船攜帶的一張鍍金唱片上,發射升空。如今,《流水》依舊隨同人類其他的文明一起,向宇宙萬物傳達著人類智慧的聲音,也在尋求著屬于自己的知音。
壬辰年盛夏,終于習得古琴大師管平湖演奏的古琴名曲《流水》,內心倍感激動,之余亦有惶恐,不知自己能否駕馭此圣曲。閑暇時翻閱《琴史》,借古人之心境解現今之名曲。
子期與伯牙之間的知音故事,早已耳熟能詳。朱長文《琴史》中記載:“伯牙鼓琴,鐘子期善聽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
關于伯牙的一則小故事,或許可以得出古琴的魅力所在。“嘗學鼓琴于成連先生,三年而成,神妙寂寞之情未能得也。”成連日:“吾雖傳曲,未能移人之情,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與子共事之乎。”乃共至東海,上蓬萊山,留伯牙日:“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荀日不返。牙心悲,延頸四望,寂寞無人,徒聞海水洶涌,群鳥悲鳴,仰天嘆日:“先生亦以無師矣,蓋將移我情乎?”乃援琴而作《水仙》之操。荀卿嘗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鳥獸猶感之,況于人乎?伯牙被成連留在東海蓬萊島上,四周寂寞無人,“徒聞海水洶涌,群鳥悲鳴”,得到外物的觸動,伯牙有感而發,創作《水仙操》,因此中國古代傳統的“移情”需要通過外物來喚起人的情感,并以物來表現,從而達到“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這不得不說明琴樂在最初的階段,就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人與自然的統一性,意識到藝術的至高境界應該是人、宇宙萬物高度和諧為一的綜合交融的藝術。
現今社會中,紛繁嘈雜,奔波忙碌的人們似乎忘記了如何收心,古琴借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雖有部分人在其中裝神弄鬼,卻真正有大批人將精神回歸,寄托于琴上。他們崇尚自然,崇尚靜逸,把古琴作為了自娛自樂的樂器。
除了“文人琴”,更甚者是“藝人琴”,如今,尚處在主攻技巧方面,如同“師襄之學,徒知其音;圣人之學,必得其意。”孔子學琴于師襄,十日不進,師襄子曰:今子于琴己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己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己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己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有間……有間……有間……有間之間,看到的是孔子的進步,看不到的是孔子不斷的聯系。在絡繹的琴聲中,在不斷的付出中,由曲至數,由意至人,文王的面容、文王的神情逐一顯現,由模糊到清晰。伴隨整個過程的,惟有不絕的琴音,以及孔子永不言棄的叩問。
在“習其曲”、“得其數”、“得其志”、“得其為人”中,孔子給我們總結了學習古琴,乃至學習藝術的幾個階段。
習其曲,即將琴曲彈得熟練;得其數,是在熟練的基礎上對琴曲的音樂內涵有了一定的感知;得其志,即在前兩者的基礎上領悟到了某種音樂實質;得其為人,即從琴曲中感悟到了音樂的蘊涵。在整個教授的過程中,師襄子并未告訴孔子他所習琴曲的“內容”,但孔子經過自己的練習與體驗,看到了一個“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的“人”,感悟到了這曲子表現的就是“文王”。也許這個故事有一定的夸張成分,但“曲”、“數”、“志”三種不同的感知深度以及“人”的體悟,就是對琴曲的音樂從表層的樂音到“弦外之音”的理解,再到從這種理解深化為某一個具體人的形象進行聯想的生動刻畫。
流水的形態有百千種,時而浩蕩,時而湍急,時而緩流,時而激涌,或吾將不遺余力,愿習其曲,得其數,得其志,得其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