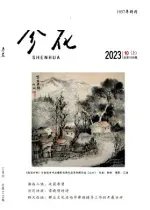我與文學
我與文學發生親密關系已經近四十年了——不算多長,卻也不短。
四十年間,邊寫,邊不斷思考,調整與文學的關系。歸納起來,所得對于文學之理解,無非以下諸條:
一、說到底文學是人學。
寫作者在某一時期,與某一些人接觸深入,產生了創作沖動(指現實題材),于是寫出了關于那樣一些人的作品——比如關于工人、農民、軍人、知青等等。以往之評論及讀者,由而認為,其作品便是反映了工人、農民、軍人、知青之什么什么樣的命運、品格、精神。然而任何人都首先是人。正確的理解應是——反映了是工人、農民、軍人、知青的“人們”,在特定情況下的人性狀態。作品離那一時期越遠,便越是在寫人。
二、說到底,人類是因為希望一代比一代更配是人才需要文學的,而不是反過來。
故不論什么體裁、題材、風格,都不可能不呈現普世價值與人的關系。不呈現的,不是好作品。批判是為此,歌頌是為此,托想象于神話是為此,寄愿望于將來也是為此。普世價值乃是人與社會與時代的契約的總和。
三、說到底,人人都喜歡并可以進行文學寫作,比只有少數人善于的好。
因為人人都喜歡并可以,證明文學之雨露遂使人類共享。廣泛的寫作帶動更廣泛的閱讀,使文學“化人”不再是一句空話。當然,須看都在寫什么。若都只不過通過寫作與普世價值對著干,唯解構之消滅之為最大快事,那么對一個國家是不幸了。
然而我以我眼來看,目前之中國還并不是這樣。
四、我不諱言我是人性理想主義者。我對社會和時代的種種理想——說到底,寄托于我對中國下幾代人的人性理想。
2013年5月17日
北京
(責任編輯高云平)
作者簡介:梁曉聲,原名梁紹生。當代著名作家。祖籍山東榮城,出生于哈爾濱市,現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曾任北京電影制片廠編輯、編劇,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及中國電影進口審查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