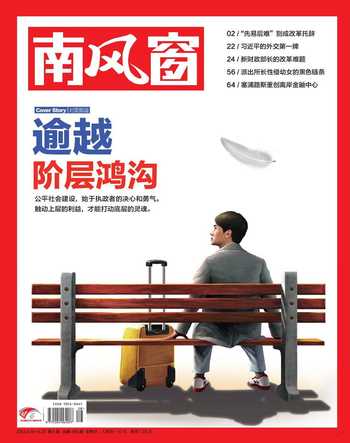新財政部長的改革難題
覃愛玲
3月24日,新任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第一次以財長身份公開講話,用罕見的直白話語,批判了政府通過財政增收或擴大赤字兩種方式擴大福利再分配的政策路徑,認為中國經濟和社會亟需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政府應創造公正的環境為市場化提供更大空間而非福利品,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
樓繼偉素有“市場派”之名。急盼市場化改革的經濟界對新財長充滿期待,基于其個人經歷和思想取向,有解讀甚至稱,其上任本身即可看作是中央將下大力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的信號。
當前公認的是,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已經到了新的關鍵時刻,需要進行大的整體性改革。但“改革”一詞本身已經充滿歧義,可能指向完全相反的政策取向,具體怎么改,從哪里入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以財稅改革作為新一輪改革的突破口,是其中頗有影響的一種聲音。樓繼偉的發聲,強化了這一觀點。
事實上,樓自己也以此為期許。他表示,過去30多年中國堅持市場取向的持續改革中,財稅體制起了突破口與先行軍的作用。
但當前中國經濟下行,財政增收壓力加大,支出卻有增無減。財政部門如何在維持收支平衡的基礎上進行財稅自身的改革,并為新一輪經濟社會改革提供突破口,面臨諸多難題。
告別超規模增長?
在2013年的中央預算中,財政赤字高達1.2萬億元,比2012年預算增加4000億元,成為建國后財政赤字的歷史高點。
對此,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財政赤字的總量雖然創歷史新高,但是在可控之內。他認為,造成2013年財政赤字猛增有兩大因素,收的一面,是因為更加突出結構性減稅,營改增的減稅量接近2000億元;從支出看,側重在增加改善民生方面,包括新農村建設、教育、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等。
從樓繼偉在論壇上的表述,不難看出其對龐大赤字規模的憂慮,以及尋求財政收支平衡的意愿。他表示,在民生支持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政府已經做了許多民生方面的中長期承諾,這種情況容易變成既幫窮人又幫懶人,并表示,政府不能碰到民生問題都要去做,“承諾過多而收入不夠,就會走向不歸之路”。他預計未來財政收入將降至一位數增長,不太可能出現超規模的增長。
中國財政收入近年來年年上一個臺階,從2007年的5.13萬億元人民幣升至去年11.72萬億。而目前較為公認的說法是,從去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從此前的高速增長期進入中速增長周期,預計會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低于8%的增長率。在這種情況下,財稅收入顯然難以進一步增大。
在收入增加有限,福利支出不可能大幅下降的財政收支矛盾下,降低政府自身開支成為選擇之一。一些吃財政飯的單位年底突擊花錢,“三公”消費的高額支出,政府大修樓臺館所、形象工程等現象,一直深為大眾詬病。新任總理李克強明確表態,要收緊政府開支,政府行政經費和人員編制只減不增,更大興節儉令。
但據媒體報道,雖然許多一度火熱的豪華酒店在節儉令下受到打擊,消費量急降,更多公款消費轉為地下。不從預算和財務公開等制度建設方面進行控制,只憑行政命令,顯然難以實質性解決公款消費問題。
一項增加財政收入的可能,是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交財政的比例。最近幾年,大型國企尤其是壟斷性國企的規模和利潤都得到巨大擴張,但上交利潤比例最高不超過20%。
樓繼偉表示,以前國有企業上交利潤比例不大,主要考慮的是這些國有企業有包括下崗職工在內的歷史問題需要解決,現在10多年過去,這些問題越來越少,因此會不斷提高上交比例。
但從這些頗有政策能量的大型國企嘴里奪食,顯然并非易事。近日,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就曾呼吁,13年前買斷工齡的“中石化下崗職工活不下去了”,要求通過增加財政轉移支付解決這些職工的養老保險問題。
而近日有媒體稱,近日從國資委處獲得的信息表示,國資委短期內并無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的考慮,也沒有時間表。
整體改革突破口?
中國的財稅改革已經到了不得不改之時,這是近年來業界的公認看法。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負面效應越來越大,引起各方爭議。賣地財政不可持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顯現。
中共十八大報告曾明確提出,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構建地方稅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
如何解決土地財政缺位后的地方財政問題,有各種不同意見,包括中央上收事權,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與地方共享消費稅,開征房產稅、資源稅和環境稅等構建新的地方稅體系等。其中,同時進行行政框架扁平化改革,降低行政成本的呼聲甚高。
曾參與過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樓繼偉,對央地財政關系重構的構想頗為宏遠。他曾表示,應由中央層面來管理社會保障等全國福利性事務,同時相應地對中央、地方的行政人員結構進行大幅調整,將大量地方公務員劃歸中央政府。他認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小的中央政府,中央公務員僅占全部政府雇員的6%,而世界平均水平在1/3。這種大動作的改革顯然非短時間內能夠定奪。
就目前來看,最為現實的財稅改革內容是“營改增”的進一步推廣,它被賦予了結構性減稅、推動服務業發展的產業結構優化等功能。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稅種以間接稅為主,被認為無法對收入分配進行合理調整。因為低收入者的消費額占比例更大,稅收大部分被隱性地置放于中低收入者身上。從間接稅過渡到直接稅,征收以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為主的直接稅,是眾多改革派財稅專家一直提倡的財稅改革方向之一。
房產稅、資源稅和環保稅等,是眾多財稅專家看好的新興稅種。它們通常被認為除了籌集財政收入外,還具有調節經濟發展和資源分配的更廣泛作用。
2010年,資源稅改革率先在新疆試點。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稅率為5%。從2011年開始,在全國全面推廣。它被寄望成為包括電力體制改革在內的中國基礎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的切入點,并從長遠看,產生節能降耗的杠桿作用。
房產稅在目前則有很大爭議。以賈康為代表的贊成者認為,它將在為地方構建健康穩定的新稅種、房地產調控、優化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產生正面效應;而以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為代表的反對者則認為,房產稅的收取成本高昂,且在收取過程中易使政府與民眾造成直接沖突,得不償失。
許善達曾建議,作為房產稅的替代,政府在交易過程中一次性分享房產持有者的新增利潤。這種方式被認為既能為地方政府收取到一定的稅收,又容易操作,且避免與民眾長期爭利。新出臺的“國五條”內容正與這一觀點類似。
從更大的角度看,直接稅將徹底改變政府與民眾的關系。一個需時時拿出自身收入納稅的公民,必將更為關心政府的花費所在;而需時時直接從民眾手中收錢維持運轉的政府,勢必對民眾的訴求更為在意。
但在短時期內,房產稅、資源稅和環保稅等將仍處于試點培育甚至規劃階段。今后一段時間,流轉稅和所得稅仍將扮演主體稅種,稅收籌集國家財政收入的作用仍是主要的。
另一個大的問題,是進一步推進預算制度建設。上一屆政府為建立科學的預算制度做了不少努力,尚需實質性進展。一個缺乏科學預算的財政制度,不可能是一個完整的現代財政制度。以爭議重重的《預算法》修訂為契機,全面調整、規范中國的預算制度體系,應是政策選擇之一。
黃金十年與失落十年
樓繼偉素有說話直率,不怕得罪人之名。“幫窮不幫懶”一論,公開表達了對福利再分配政策取向的謹慎態度。除了福利支出比例過大會產生政府對市場的壓制作用,導致長遠發展的不可持續性,這句話的另一層意思是指,目前中國的福利支付制度本身很不健全,加大了消耗度。
事實上,對中國過去10年中央政府在“民生”這一概念下推行的大規模福利政策,不同的社會群體和基于不同價值立場者,有時有著截然相反的感受和評價。
從2012年開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就開始談及,從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來的10年,是億萬農民的“黃金10年”。
從農業稅的徹底免除,各種轉移支付,覆蓋面達80%的農村合作醫療等各種政策,中央財政的“三農”投入從2003年的1700多億增加到2011年的1.2萬多億,8年間增長了6倍。僅2011年一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規模即超過“十五”時期5年的總和。
盡管有資金挪用和制度不合理等各種問題存在,過去10年中國農村民生改善取得的巨大成績有目共睹。農民收入連續9年保持較快增長,最近3年,增長速度更是超過了城鎮居民。除了城鎮化征地引發的問題外,農村休養生息效應明顯。曾有媒體評論,過去10年中國最重大的政策成績發生在農村。
回憶上世紀90年代末至20世紀初期農業稅時代,中國農村近乎烽煙四起的危情,會對近10年的改變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過渡到“黃金10年”,財政少取多予的政策功不可沒。
與韓俊有類似感受的是著名社會保障專家、全國人大常委鄭功成。近10年來,他最深切感受就是,中國社會保障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
他記得,10年前提到社會保障時,最流行的說法是只能“雪中送炭”,不能“吊高了老百姓的胃口”,公共投入極端有限,社保水平甚至無法真正免除困難群體的生存危機。而近10年來,政府對社會保障的投入持續大幅增長,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持續攀升,已經形成了覆蓋城鄉的全民社會保障體系,進而成為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格局日益重要的機制。
與此相對照的是,日前,中國“市場派”代表、經濟學家張維迎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呼吁新一代領導人沖破壓力,“重啟改革”。在文中,他將中國過去的10年稱為“失去的10年”(lost decade)。這一呼聲,得到了市場派內部的廣泛認同。
對市場派而言,過去幾年,在國進民退的壓制之下,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受到擠壓。東南沿海一帶大量民營中小企業,更是在全球經濟危機、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稅費過重等各種綜合壓力下,成批破產。
而在飛速上升的房價和通貨膨脹壓力下,工資上漲有限的中間收入階層的生活痛苦指數急劇加大。大學生兩三千元的起薪與一般農民工差距越來越小。不少人成為用父母積蓄首付,每月主要收入花在月供上的“房奴”。“白領”一詞,已經由受人羨慕的對象變為嘲諷之詞。
20年前開始,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企業家群體地位高漲,企業家黨代表成為一時風潮,國企改革取得突破;但同時產生了大量下崗職工,農村處于相當危險狀態。10年前開始政府將“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關注農村和底層,努力構建社會保障體系,但在民營企業發展和中產階層培育方面難盡人意。而新一屆政府在承諾繼續上一屆政府福利保障的情況下,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化取向。
從這里可以看出,對市場和福利的施政側重點不同,這一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常常交相出現的情形,在中國政府換屆過程中也已然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