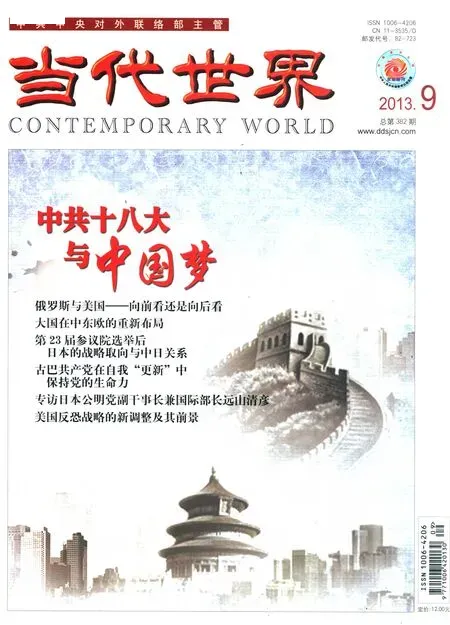第23屆參議院選舉后日本的戰(zhàn)略取向與中日關(guān)系
■ 胡令遠(yuǎn)/文
(作者系復(fù)旦大學(xué)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舉世矚目的日本第23屆參議院選舉已經(jīng)落下帷幕,其對(duì)日本國(guó)家戰(zhàn)略取向的影響日漸顯露。由于東亞地緣政治的日益復(fù)雜化,特別是在目前中日關(guān)系處于戰(zhàn)后以來(lái)極少見(jiàn)的嚴(yán)峻局面下,深入研判這次參議院選舉對(duì)未來(lái)中日關(guān)系的影響,無(wú)疑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長(zhǎng)期政權(quán)”預(yù)期及其效應(yīng)
隨著冷戰(zhàn)的結(jié)束,日本“1955年體制”于1993年壽終正寢。在戰(zhàn)后這一日本政壇“超穩(wěn)定”的38年之后,日本政界進(jìn)入令人眼花繚亂的重新分化組合的劇烈變動(dòng)期。而所謂“十年十相”,已在近年的日本政壇“常態(tài)化”。這一現(xiàn)象所帶來(lái)的直接后果在于,無(wú)論是在內(nèi)政、還是外交方面,日本都難以形成一以貫之、內(nèi)外協(xié)調(diào)的國(guó)家長(zhǎng)期發(fā)展戰(zhàn)略,這也必然投射在具體的政策策略上。
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率領(lǐng)該黨于2012年年底贏得大選,從民主黨手中奪回政權(quán),其本人也梅開(kāi)二度,重登首相寶座,今年再下一城,又贏得參議院大選。這樣的結(jié)果,一方面使其本人信心大增,以為得到國(guó)民普遍認(rèn)可,遂作打破“十年十相”魔咒、長(zhǎng)期執(zhí)政的打算。另一方面,按照日本眾議院議員任期四年,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選半數(shù)的法律規(guī)定,今后三年內(nèi),將無(wú)決定現(xiàn)政權(quán)命運(yùn)的所謂“國(guó)政選舉”。如果“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不崩盤(pán),沒(méi)有其他極端政治、社會(huì)危機(jī)發(fā)生,以及他本人身體不像上次那樣出狀況的話,一般認(rèn)為安倍長(zhǎng)期執(zhí)政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這樣一種對(duì)安倍政權(quán)將長(zhǎng)期執(zhí)政的社會(huì)預(yù)期,必然會(huì)產(chǎn)生種種效應(yīng),撮其大要,有以下數(shù)端。
首先,從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視角,人們對(duì)“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期待感將得到強(qiáng)化。本來(lái)日本內(nèi)閣(包括安倍本人)對(duì)“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第一支箭,即所謂超量化寬松舉措背后隱藏的極大風(fēng)險(xiǎn),是非常擔(dān)心的,并無(wú)勝算的把握和信心,是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姑且一試的無(wú)奈之舉。對(duì)于“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重中之重的所謂第三支箭——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戰(zhàn)略,人們普遍認(rèn)為缺乏新意,并不看好。但不管怎么說(shuō),這次參議院選舉結(jié)果表明,“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短期效應(yīng)還是喚起了日本國(guó)民的期待感。正是這種期待感,使安倍贏得參議院選舉勝利后政權(quán)基礎(chǔ)得以鞏固,并增大了成為長(zhǎng)期政權(quán)的可能性。而安倍內(nèi)閣一旦長(zhǎng)期執(zhí)政,則必然會(huì)進(jìn)一步穩(wěn)固地推行和展開(kāi)其經(jīng)濟(jì)發(fā)展計(jì)劃,在條件和環(huán)境方面,增添了“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成功的要素。所以,這樣一種預(yù)期,反過(guò)來(lái)又必然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日本國(guó)民的期待感。
這種期待感,實(shí)際上是一柄雙刃劍。所以參議院選舉結(jié)束后,安倍把進(jìn)一步推行其經(jīng)濟(jì)政策視為與自身政權(quán)生死攸關(guān)的首要課題。在長(zhǎng)期政權(quán)的預(yù)期下,為了把“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短期效應(yīng)變?yōu)殚L(zhǎng)效機(jī)制,安倍采取了相應(yīng)的措施,并進(jìn)行了相關(guān)規(guī)劃,包括著手制定明年預(yù)算時(shí)向醫(yī)療、農(nóng)業(yè)、科技等部門(mén)傾斜,為尋求新的支柱性增長(zhǎng)點(diǎn)、第三支箭以及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議(TPP)所需結(jié)構(gòu)改革的具體目標(biāo)等都已提上日程。雖然安倍把與重建財(cái)政密切相關(guān)的消費(fèi)稅增稅問(wèn)題留待2013年秋季做決斷,但也已著手對(duì)20世紀(jì)90年代的增稅效應(yīng)進(jìn)行測(cè)算和評(píng)估。以上種種,意味著著眼于長(zhǎng)期政權(quán)預(yù)期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藍(lán)圖已經(jīng)展開(kāi)。

安倍上臺(tái)后推行的經(jīng)濟(jì)新政可以概括為三個(gè)方面,也被稱(chēng)為“三支箭”:寬松的財(cái)政和貨幣政策,以及結(jié)構(gòu)性改革。此次參議院選舉結(jié)果表明,“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短期效應(yīng)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日本國(guó)民的期待感。
雖然日本經(jīng)濟(jì)問(wèn)題如山,“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的高風(fēng)險(xiǎn)和低成功率也沒(méi)有排除,日本經(jīng)濟(jì)能否真正走出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通縮”還是個(gè)問(wèn)號(hào),但這次參議院選舉對(duì)“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的進(jìn)一步展開(kāi)所產(chǎn)生的助推作用——即由“推高股價(jià)”、“日元貶值”等以金融為抓手的第一階段向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實(shí)際增長(zhǎng)的第二階段延伸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是值得關(guān)注的。因?yàn)樗鎏砹恕鞍脖督?jīng)學(xué)”成功的可能性,而對(duì)這一可能性,中國(guó)需在做出及時(shí)、準(zhǔn)確之研判的基礎(chǔ)上,加以應(yīng)對(duì)。
其次,在安全保障領(lǐng)域,安倍本人及其自民黨團(tuán)隊(duì)出于長(zhǎng)期政權(quán)的預(yù)期,勢(shì)必有若干重大調(diào)整及變化。基于保守理念,一直以來(lái),安倍認(rèn)為戰(zhàn)后自民黨立黨理念的兩大目標(biāo)只實(shí)現(xiàn)了一半,即在經(jīng)濟(jì)繁榮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領(lǐng)域,即領(lǐng)導(dǎo)日本真正走出戰(zhàn)后方面毋庸說(shuō)是失敗的。其所謂真正走出戰(zhàn)后,即以廢除外國(guó)“強(qiáng)加”給日本的作為國(guó)家根本大法的戰(zhàn)后憲法為標(biāo)志,實(shí)現(xiàn)日本的真正獨(dú)立。現(xiàn)在,安倍認(rèn)為這一使命已經(jīng)歷史性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所以,以修憲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biāo),首先充分體現(xiàn)在他第一次登上首相寶座之時(shí)。安倍為此可謂殫精竭慮,終于在短短一年任期內(nèi),通過(guò)了修改憲法的“國(guó)民投票法案”。由于他過(guò)度專(zhuān)注于修憲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政治訴求,在經(jīng)濟(jì)上了無(wú)建樹(shù)、乏善可陳,最終不得不以身體不適為由黯然下臺(tái)。
重登首相寶座的安倍以上一任期為鏡鑒,把經(jīng)濟(jì)作為政權(quán)存續(xù)的首要課題。但修憲畢竟是其夢(mèng)寐以求的夙愿,因而安倍也未曾須臾忘之。從這一意義上,此次參議院選舉對(duì)安倍來(lái)說(shuō)可謂憂喜參半。一方面雖然與執(zhí)政聯(lián)盟公明黨的席位超過(guò)半數(shù),但公明黨在修憲問(wèn)題上與安倍并不同調(diào)。因而,扣除公明黨席位的話,即便與贊成修憲的維新會(huì)、大家之黨等聯(lián)手,席位還是達(dá)不到修憲法定要求的三分之二。為此,安倍積極推動(dòng)首先修改憲法第96條,以便降低修憲門(mén)檻。但這樣做一是涉及立憲的法理,二是深受戰(zhàn)后和平憲法恩惠的廣大國(guó)民的抵制,其進(jìn)展并不順利。但另一方面,此次參議院選舉,畢竟鞏固了安倍政權(quán)的基礎(chǔ),而在此基礎(chǔ)上的長(zhǎng)期執(zhí)政預(yù)期,為其穩(wěn)固地、分步驟地實(shí)現(xiàn)修憲提供了空間和余地。
具體而言,安倍以執(zhí)政六年為預(yù)期,將原來(lái)設(shè)想的一氣呵成調(diào)整為分兩步走。第一步可稱(chēng)之為“啄殼戰(zhàn)術(shù)”,即首先通過(guò)修改憲法解釋?zhuān)惺辜w自衛(wèi)權(quán),使和平憲法成為徒具理念形式的空殼;第二步伺機(jī)將其啄破、徹底打碎。而時(shí)間的節(jié)點(diǎn)則控制在六年的任期內(nèi),也即安倍要親手完成修憲的歷史使命,從而使日本徹徹底底地走出戰(zhàn)后體制,其本人也因此而能夠“名標(biāo)青史”。其實(shí),參議院選舉后,安倍已經(jīng)加速推進(jìn)第一個(gè)步驟。如在其第一任期內(nèi)成立的首相個(gè)人咨詢機(jī)構(gòu)“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礎(chǔ)再構(gòu)筑懇談會(huì)”重新啟動(dòng),將于今年秋季就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quán)的相關(guān)法律解釋提出報(bào)告書(shū),其成果將反映在今年年底制訂的新防衛(wèi)大綱中,進(jìn)而在明年秋季修訂日美防衛(wèi)合作新指針時(shí)就深化日美同盟發(fā)揮作用。與此相關(guān),考慮到在國(guó)會(huì)就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quán)修改憲法解釋等進(jìn)行答辯時(shí)起重要作用的、被稱(chēng)為“法律的看門(mén)人”的內(nèi)閣法制局長(zhǎng)官這一關(guān)鍵崗位時(shí),安倍在參議院選舉后的半個(gè)月,即把堅(jiān)持歷代內(nèi)閣關(guān)于集體自衛(wèi)權(quán)日本在“國(guó)際法上擁有,但與憲法第九條的關(guān)系而不能行使”之解釋的山本庸幸內(nèi)閣法制局長(zhǎng)官解任,而以對(duì)此持積極態(tài)度的駐法大使小松一郎取而代之。這種由外務(wù)省官僚充任內(nèi)閣法制局長(zhǎng)官的“異例”舉措,反映了安倍在修憲問(wèn)題上“順昌逆亡”的決絕態(tài)度。另外,安倍還將于2014年撤銷(xiāo)基于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反省、標(biāo)志文官統(tǒng)治而設(shè)立的防衛(wèi)省“運(yùn)用企劃局”,因?yàn)檫@有礙于職業(yè)軍人(所謂自衛(wèi)官)的一元化統(tǒng)治,也不符合自民黨在“憲法修正草案”中明記的“設(shè)置國(guó)防軍”的目的和要求。
以上種種說(shuō)明,以參議院勝選為基礎(chǔ),安倍政權(quán)以實(shí)現(xiàn)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quán)為抓手,或啟動(dòng)相關(guān)組織做法律上的準(zhǔn)備,或運(yùn)用職權(quán)鏟除修憲的障礙,或蠶食依據(jù)和平憲法理念設(shè)置的機(jī)構(gòu)等。他正一步一步地實(shí)施和切切實(shí)實(shí)地推進(jìn)修憲的舉措與步伐。
“擰勁國(guó)會(huì)”的消解及其后果
所謂“擰勁國(guó)會(huì)”或者“扭曲國(guó)會(huì)”,是指執(zhí)政黨與在野黨分別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占據(jù)主導(dǎo)權(quán)的情形。從“1955年體制”于1993年解體至今恰好20年,其間,政界幾經(jīng)分化組合,呈現(xiàn)出不穩(wěn)定的特點(diǎn)。其表現(xiàn)形式,一是自民黨雖然多數(shù)時(shí)期居主導(dǎo)地位,但已經(jīng)不僅不能單獨(dú)執(zhí)政,而且作為執(zhí)政聯(lián)盟往往失去參議院多數(shù)席位;二是與選舉制度改革密切相關(guān)的兩大政黨化趨勢(shì)。
由于眾、參兩院在制度設(shè)計(jì)時(shí)眾議院具有優(yōu)越地位,其中包括參議院選舉不能直接決定首相的去留和政權(quán)的更迭,所以在參議院選舉時(shí),選民的心態(tài)相對(duì)放松,加之政黨政治的相互制衡原理,以及日本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往往會(huì)出現(xiàn)選票的流向與眾議院選舉呈逆向方式,其結(jié)果就會(huì)形成所謂“鐘擺”現(xiàn)象。即或?yàn)榱酥萍s執(zhí)政黨使其不至于“暴走”,或?yàn)榱吮磉_(dá)對(duì)執(zhí)政黨政策的不滿等,使執(zhí)政黨包括執(zhí)政聯(lián)盟在參議院淪為少數(shù)派。加之冷戰(zhàn)后政界重組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所以近年日本政壇的“擰勁國(guó)會(huì)”現(xiàn)象已經(jīng)“常態(tài)化”,由此帶來(lái)兩個(gè)顯著的后果。一是作為執(zhí)政聯(lián)盟的主導(dǎo)政黨黨首、也即首相往往為參議院選舉失敗承擔(dān)責(zé)任,以辭職的方式“以謝天下”。其實(shí)2007年安倍的下臺(tái),與當(dāng)年參議院選舉失利有直接的關(guān)系也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二是國(guó)會(huì)運(yùn)營(yíng)的困難。政府的很多法案在參議院擱淺,即便是執(zhí)政聯(lián)盟在眾議院占據(jù)三分之二以上議席,可以再次審議通過(guò),但次數(shù)多了的話,也會(huì)遭到“暴走”、“無(wú)能”等非議。“擰勁國(guó)會(huì)”無(wú)疑使政權(quán)運(yùn)營(yíng)難以順暢,而這勢(shì)必影響政權(quán)的支持率,待到“危險(xiǎn)水域”,就離下臺(tái)不遠(yuǎn)了。無(wú)論是自民黨的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還是民主黨的菅直人等前首相,都為此吃盡苦頭,這也成為他們下臺(tái)的重要原因。
對(duì)于“擰勁國(guó)會(huì)”的評(píng)價(jià),可謂毀譽(yù)參半。一方面有人認(rèn)為這是日本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現(xiàn),由此引發(fā)的執(zhí)政黨與在野黨的博弈,并不是正常的政策論爭(zhēng),而只是以?shī)Z取政權(quán)為主要目的的故意“擰勁”,毒化了政壇。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認(rèn)為這是議會(huì)民主制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參議院由此發(fā)揮了真正的制衡作用。雖然見(jiàn)智見(jiàn)仁,但不論怎么說(shuō),其實(shí)際效果的負(fù)面影響是不能否認(rèn)的。
第23屆參議院選舉,自民黨與公明黨組成的執(zhí)政聯(lián)盟獲得的議席,加上非改選部分,共計(jì)135席,遠(yuǎn)超過(guò)半數(shù)的121席。多年來(lái)令執(zhí)政黨十分頭痛的“擰勁國(guó)會(huì)”得以消解。其所帶來(lái)的效應(yīng)和后果,主要有以下幾點(diǎn)。一是增強(qiáng)了安倍執(zhí)政的基礎(chǔ),使其成為長(zhǎng)期政權(quán)有了可能;二是以此為前提,使日本的內(nèi)政和外交有了制定長(zhǎng)期戰(zhàn)略并付諸實(shí)施的基本條件;三是今后安倍內(nèi)閣提交國(guó)會(huì)審議的相關(guān)法律法案,特別是與“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相關(guān)的法案在國(guó)會(huì)的通過(guò),可以說(shuō)基本上暢通無(wú)阻;四是因?yàn)樵谝包h在眾、參兩院皆居少數(shù),缺少對(duì)安倍內(nèi)閣的制度性框架制約的手段,所以安倍政權(quán)容易過(guò)度“暴走”,獨(dú)斷專(zhuān)行。
“一強(qiáng)多弱”的政黨政治生態(tài)
原參議院第一大黨民主黨在此次參議院選舉中議席銳減,相對(duì)于自民黨的115席,僅剩59席。雖然民主黨現(xiàn)在的議席為參議院第二大黨,但具體席位數(shù)僅為自民黨的二分之一強(qiáng)。而在選舉前,民主黨86席居首位,自民黨84席次之,可謂勢(shì)均力敵,能夠發(fā)揮對(duì)自民黨的制約作用。但現(xiàn)在自民黨一騎絕塵,其他黨派都在20議席以下,由此形成所謂“一強(qiáng)多弱”的局面。
雖然選舉后自民黨和公明黨以外的各在野黨,特別是席位減少的政黨尚未發(fā)生大的分裂和重組,但民主黨不僅未見(jiàn)復(fù)興的兆頭,也還存在以民主黨政權(quán)時(shí)代的核心人物野田佳彥、前原誠(chéng)司等組成的所謂“六人幫”與海江田萬(wàn)里代表的對(duì)立,有潛在的分裂危險(xiǎn);而維新會(huì)的共同代表橋下徹雖然請(qǐng)辭未果,但今后主要精力將向大阪轉(zhuǎn)移也勢(shì)在必行;大家之黨黨首渡邊喜美與干事長(zhǎng)江田憲司的決裂,也給該黨帶來(lái)不小的負(fù)面影響。擔(dān)任社民黨黨首已長(zhǎng)達(dá)十年,在日本政壇頗有影響的福島瑞穗為承擔(dān)敗選責(zé)任而黯然辭職,以社會(huì)黨為前身的該黨在參議院現(xiàn)在僅占3席。
以上這種“一強(qiáng)多弱”的黨勢(shì)分布,其效應(yīng)和后果大致有以下幾點(diǎn)。一是冷戰(zhàn)后逐漸形成的日本政壇兩大政黨化的趨勢(shì)遭受很大阻遏,2009年以后人們所期待的兩大政黨輪流執(zhí)政的日本政黨政治藍(lán)圖,驟然暗淡起來(lái);二是自民黨一黨獨(dú)大容易形成“獨(dú)斷專(zhuān)行”政治,這與日本實(shí)行的議會(huì)民主制原理不相容。即便是在“1955年體制”下,“保革伯仲”的局面使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黨實(shí)際上發(fā)揮了關(guān)鍵的制衡作用,現(xiàn)在這一體制消失了;三是由于各在野黨之間理念和政策,包括人事的巨大差異和復(fù)雜性,彼此聯(lián)手制衡安倍自民黨政權(quán)的有效機(jī)制很難形成。
參議院選舉對(duì)中日關(guān)系的影響
綜上所述,這次參議院選舉有三點(diǎn)值得特別關(guān)注:一是增強(qiáng)了安倍政權(quán)的基礎(chǔ),產(chǎn)生了其長(zhǎng)期執(zhí)政的預(yù)期;二是以此為背景,安倍政權(quán)在經(jīng)濟(jì)、安保領(lǐng)域有條件制定并實(shí)施國(guó)家長(zhǎng)期發(fā)展戰(zhàn)略,而其戰(zhàn)略取向不言而喻對(duì)中日關(guān)系會(huì)產(chǎn)生深刻影響;三是“擰勁國(guó)會(huì)”的消解和“一強(qiáng)多弱”的黨勢(shì)分布,使以議會(huì)和政黨政治為依托的、對(duì)安倍自民黨政權(quán)的制衡非常有限,有人將此稱(chēng)之為“2013年體制”。可以說(shuō),這種體制是戰(zhàn)后在野黨制衡執(zhí)政黨最弱的形態(tài)。
以上情形對(duì)中日關(guān)系的影響,大致可以歸納為:
第一,出于內(nèi)外環(huán)境的壓力和長(zhǎng)期執(zhí)政的預(yù)期,參議院選舉后安倍顯然已經(jīng)將修憲調(diào)整為中長(zhǎng)期政治目標(biāo),而以實(shí)現(xiàn)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quán)為現(xiàn)實(shí)首要政治和外交訴求,并為第二步進(jìn)行修憲做鋪墊,而將時(shí)間的節(jié)點(diǎn)掌控在維持六年的政權(quán)任期之內(nèi)完成;同時(shí),在優(yōu)先順序上,則以經(jīng)濟(jì)發(fā)展為最重要課題。另一方面,安倍雖然需要借助釣魚(yú)島爭(zhēng)端激發(fā)民族主義情緒和渲染中國(guó)軍事威脅來(lái)實(shí)現(xiàn)其修憲等政治目標(biāo),但綜合以上經(jīng)濟(jì)、政治情勢(shì),特別是他對(duì)長(zhǎng)期政權(quán)的自期與考量,接下來(lái)的一段時(shí)間,他會(huì)謀求與中韓在一定程度上的關(guān)系緩和,而不是激化對(duì)立。以此為前提,釣魚(yú)島問(wèn)題有可能形成“事實(shí)上擱置”的狀態(tài),即雙方擇時(shí)建立海上應(yīng)急聯(lián)絡(luò)機(jī)制,中國(guó)海警釣魚(yú)島巡航常態(tài)化,圍繞釣魚(yú)島問(wèn)題兩國(guó)不進(jìn)一步采取刺激對(duì)方的舉措,形成各自嚴(yán)格控制己方民間人士登島等行為的默契。
第二,出于對(duì)安倍長(zhǎng)期執(zhí)政的預(yù)期,美國(guó)總統(tǒng)奧巴馬預(yù)計(jì)2014年將正式訪問(wèn)日本,中國(guó)也應(yīng)該視其為將要長(zhǎng)期打交道的對(duì)手,并為此作必要的準(zhǔn)備。截至目前,安倍一直聲稱(chēng)與中國(guó)對(duì)話的大門(mén)是敞開(kāi)的,之所以沒(méi)有進(jìn)展,是因?yàn)橹袊?guó)設(shè)置了首腦會(huì)晤的條件。安倍此舉的策略性是不言自明的,即把責(zé)任推給中方。但參議院選舉后,安倍出于長(zhǎng)期政權(quán)的預(yù)期,存在由策略手段向逐步主動(dòng)采取一些積極舉措,如通過(guò)各種渠道,包括加強(qiáng)經(jīng)貿(mào)合作等以求緩和緊張關(guān)系,為首腦會(huì)晤和改善兩國(guó)關(guān)系創(chuàng)造條件的方向轉(zhuǎn)變的可能性。對(duì)此,中國(guó)應(yīng)一方面揭露其策略手段的欺騙性,另一方面應(yīng)密切關(guān)注其真實(shí)意圖的變化情況,做出積極的應(yīng)對(duì)。根據(jù)日本國(guó)內(nèi)的政治生態(tài),現(xiàn)在要安倍政權(quán)明確承認(rèn)釣魚(yú)島存在爭(zhēng)議并非易事,以一種相對(duì)靈活的方式事實(shí)上承認(rèn),也應(yīng)該是我們爭(zhēng)取的第一步目標(biāo)。如果有利于這一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或鞏固,根據(jù)需要,高層領(lǐng)導(dǎo)會(huì)晤等應(yīng)逐步展開(kāi)。
第三,中日關(guān)系也還不能完全排除向另外一個(gè)方向發(fā)展的可能性,即如果安倍的經(jīng)濟(jì)舉措崩盤(pán),又或者反過(guò)來(lái)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獲得相當(dāng)成功,都會(huì)刺激安倍加速實(shí)現(xiàn)以修憲為核心的政治訴求。這樣,中日關(guān)系不言而喻將會(huì)惡化,不要說(shuō)短期內(nèi)、甚至數(shù)年都難以根本改變僵局狀態(tài)。而在中日關(guān)系繼續(xù)惡化的情況下,參議院選舉后由于國(guó)會(huì)和黨際對(duì)安倍政權(quán)的制衡作用大幅弱化,就存在安倍政權(quán)容易一意孤行、并容易得逞的現(xiàn)實(shí)可能性。對(duì)此,中國(guó)一是要有充分的心理準(zhǔn)備,同時(shí)也要有應(yīng)對(duì)之策。譬如不僅要適時(shí)、適度地積極推動(dòng)與日本在野黨之間的交流,也要深化與自民黨的執(zhí)政聯(lián)盟公明黨之間的交流,以期從內(nèi)外最大限度地制約安倍自民黨政權(quán)給中日關(guān)系施加的負(fù)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