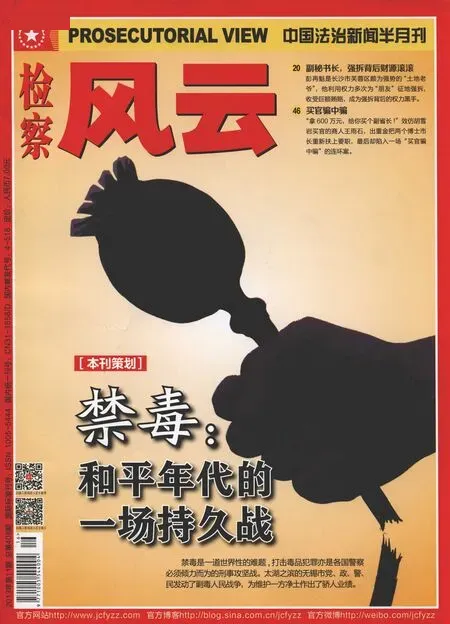沈敏: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打鑒定
沈敏: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打鑒定
在中國,從事司法領域高端科學研究和高層管理的女性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沈敏是為數不多的一個。她被評為全國“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層次人選,全國第三屆優秀科技工作者,首屆全國司法鑒定管理工作先進個人。司法鑒定在中國的發展歷史是怎樣的,它對于司法活動有著怎樣的作用和意義,司法鑒定行業還存在著哪些制約其發展的因素?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于近日走訪了沈敏所長。


本期客座總編輯:
沈敏,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法醫毒物化學專家、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檢察風云》:沈所長您好,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司鑒所”)擁有“中國司法鑒定搖籃”的美譽,培養出了很多福爾摩斯式的人物,您能為我們介紹其中一、兩位代表嗎?
司鑒所的前身是20世紀30年代創立的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所,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業開展司法鑒定的機構。獨立執業機構的出現,標志著司法鑒定作為一個行業已真正興起。新中國成立后,司鑒所為共和國培養了第一批政法干線的技術精英,奠定了新中國司法鑒定事業的基礎。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這是新中國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時期,隨著司法部被撤銷,司鑒所也不得不面臨同樣的命運。直至1983年國家同意司鑒所恢復重建,今年正好是司鑒所恢復重建30周年。
談到司鑒所走出的代表人物,首推應屬林幾教授。林幾教授是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所的創立者,我國近代法醫學的奠基人。林幾教授一生致力于法醫學研究和法醫人才的培養,他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改良法醫”,引入西方現代法醫學原理和技術。他提出,廢除舊法驗尸,改為尸體解剖,提倡科學辦案,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法醫學事業的前進。他對法醫學有獨到的見解,破獲了很多民國時期的離奇大案,包括1936年發生在北平火車站的“箱尸謎案”,1935年發生在京津鐵路的“移尸臥軌案”等。林幾教授知識淵博,辦案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一絲不茍,翻看林幾教授的鑒定書,每份都近萬字,分析嚴謹,思路縝密,說理透徹,鑒定書結尾都寫有“鑒定系公正平允真實不虛須至鑒定者”字樣,以示對鑒定結論負責,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堪為司法鑒定人的楷模。
我想介紹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是烏國慶教授。司鑒所曾在20世紀50年代舉辦過被法醫學界稱道的“黃埔三期”培訓班,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刑偵技術專家,烏國慶教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烏老現在是公安部首批特聘的八大刑偵專家之一,終身成就榮譽勛章獲得者,被譽為“中國當代的福爾摩斯”,凡公安部掛號的大案他幾乎都參與過。比如武漢長江大橋爆炸案,吉林博物館特大縱火案,“二王”持槍殺人案,還有2012年告破的周克華持槍殺人案。雖然烏老1997年就已經退休了,但還一直戰斗在大案要案的第一線。
還有很多知名的專家,比如公安部特聘刑偵專家陳世賢教授,原中國人民警官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的翟建安教授等等,我就不一一贅述了,有興趣可以來參觀我們的所史展廳。
《檢察風云》:您覺得司法鑒定在司法活動中的作用和意義是什么?對司法鑒定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謂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并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這里涉及兩個關鍵詞,“訴訟”和“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司法鑒定的手段、武器,服務訴訟和司法程序才是司法鑒定的最終目的,簡而言之,司法鑒定就是用科技和專業知識為司法公正保駕護航。
我國古代“法醫學之父”宋慈曾有名言:“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從“滴血認親”到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人類社會的證明活動雖然經歷了從神證、人證到物證的演變過程,但其核心的追求始終未變,那就是對事實、真相的探尋。因此司法鑒定作為八種法定證據之一,被認為是查明案情,定案量刑的依據。俗話說,打官司就是打證據,就是打鑒定,很形象地揭示了司法鑒定在司法活動中的角色定位,它是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神,是促進司法公正的“科學衛士”,是訴訟活動的重要保障。既然司法鑒定如此特殊和重要,那么什么才是它的靈魂?我認為是“實事求是”四個字,無論外部環境發生如何翻天覆地的變化,司法鑒定必須堅守這“四字真諦”,才能讓這份事業不斷傳承。
《檢察風云》:根據您的介紹,我們知道了司法鑒定是與科技創新密切聯系的行業,那么在司法鑒定領域有哪些最新的技術成果?它們在案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司法鑒定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業,它包含的專業非常廣泛,傳統劃分為三大類:法醫類、物證類、聲像資料類,現在還增加了電子數據。科技創新是司法鑒定發展的持續動力。
我們可以結合一些案例簡單地說明科技創新在司法鑒定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第一個案例就是“許云鶴交通事故案”,這個案子也被人民法院報評為2012年度十大典型案件之首。案件源于許云鶴與王秀芝老太太之間是駕車撞人還是助人為樂引發的糾紛,由于涉及公民道德的問題,很快發展成一起廣受關注的公共事件。案件的焦點在于王秀芝的腿傷是否為許云鶴駕車行為所致。由于現場缺乏有力的直接證據,首次鑒定的機構也沒有提出確鑿的鑒定意見,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引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司鑒所接受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委托后,組成了多技術部門的聯合鑒定組,其中包括法醫臨床學、影像學、道路交通事故技術的專家,運用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研究成果,數字化構模技術和有限元技術對王秀芝的損傷部位進行了三維重建和模擬實驗,對傷情成因進行科學推斷。根據王秀芝的傷情鑒定,其右膝部的損傷特征符合較大鈍性外力由外向內直接作用于右膝部的致傷特征,這種傷只有遭受車輛撞擊可以形成,單純摔跌難以形成,且損傷高度與許云鶴所駕車輛的前保險杠防撞條高度在車輛制動狀態下相吻合,因此可以認定王秀芝腿傷是許云鶴駕車行為所致的客觀事實。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出一份科學嚴謹、公正求實、論證周詳的司法鑒定意見,能為公正司法、平息輿情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
第二個案子是一起發生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酒駕案。2012年7月的一天,何某駕駛的豐田越野客車與張某駕駛的三菱越野客車相撞,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張某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當地鑒定中心對何某進行血液中酒精濃度的檢測后作出酒后駕車的結論。對于鑒定結論,何某及其所在單位均提出異議,何某否認當日飲過酒,并有多名人證證明,因此提請重新鑒定。當地公安機關帶著何某的血樣來到司鑒所,我們運用兩種最新的技術手段,均未檢出乙醇成分,尤其是對于乙醇代謝物的檢測呈陰性,更加確鑿地證明何某沒有飲酒。那么先前的檢測數值是怎么得出的?經過了解,何某在事故發生后曾經進行過開顱手術,期間使用過一種叫七氟烷的麻醉劑,會對乙醇檢測形成一定干擾。這個案子也警示我們,目前我國大多數鑒定機構還在采用單色譜柱單檢測器對血液中乙醇含量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很可能得出錯誤結論。
此外,司鑒所在特殊親緣關系鑒定技術、虛擬解剖、交通事故仿真重建、損傷與疾病關系等方面的研究和應用都處于領先地位,運用這些技術,破解了不少疑難案件。
《檢察風云》:在您看來,目前司法鑒定行業存在著什么問題?原因是什么?應該如何解決?
相較西方發達國家,司法鑒定行業在我國起步較晚,還處于發展的初期,今后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成長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多頭鑒定、重復鑒定現象沒有得到解決;鑒定機構趨利傾向嚴重;違規鑒定、虛假鑒定、“回扣”、“鑒托”現象等等,這些都嚴重損害了司法鑒定的社會公信力。
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我覺得是多方面的,一是司法鑒定管理體制尚未實現完全統一;二是社會司法鑒定機構準入門檻過低,導致機構間良莠不齊、資源浪費和無序競爭;三是人才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程度不高,很多機構的鑒定人都是臨床醫務人員兼職擔任。
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加強制度建設和行業監管,為整個行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生態。我相信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環境是各方期盼的,尤其老百姓才是真正的獲益者。
另外加強司法鑒定知識普及也很重要,很多群眾對司法鑒定一無所知,鑒定錯過最佳時機造成損失。還有很多群眾,尤其生活在長三角地區的百姓都不知道有司鑒所這樣一個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就在他們的身邊,有的在外面做了很多次鑒定,被一些技術手段落后的鑒定機構耽誤了時間,也增加了訴訟成本,我們覺得很惋惜,因此加強信息對稱很必要。作為司法鑒定業本身還是要堅持科學發展,要以世界的眼光,以虛懷若谷的心態,以“揚棄”的精神去不斷追求,持續改進,將這份事業傳承好、發展好。
采寫:王潔
編輯:鄭賓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