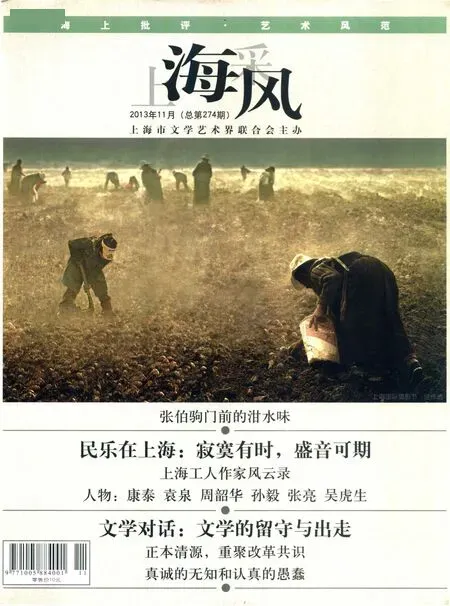文學伉儷夕陽紅——孫毅、彭新琪文學生涯60年
文/馬信芳

是無話不談的老朋友。孫老曾當過三家雜志的領導和編審,當然知道我想了解的情況,他不客氣地代我直言相問,少了我不少難言的尷尬,使我順利地完成了采訪。
與孫老相識已快20年,在本刊和文聯等單位舉辦的兒歌大賽中,作為評委,我們曾不時交流和榷商,但從未聽過他談自己。這次,在榮膺陳伯吹兒童文學“杰出貢獻獎”之際,有機會到他府上當面賜教。我們相對而坐,確切地說,我在聆聽,聽他講一生學做的那件“最有教育意義的事”。
想當演員的他,結果卻做了編劇
我的面前放著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孫毅親自編選的一套“兒童戲劇快活叢書”:它們是原創兒童劇《小霸王與皮大王》、小學課本劇《秘密》、中學課本劇《美猴王》、木偶劇《小小五彩雞》、兒童相聲《嘻嘻哈哈》《娃娃劇場開演了——孫爺爺教你寫劇本》等六本大書。日前,當第25屆陳伯吹兒童文學杰出貢獻獎授予這位為兒童文學耕耘了60多年的老將時,我致電前輩表示衷心祝賀,他笑著向我透露:他的另外四本書已在編輯中:《美麗的眼睛——兒歌新詩集》、《野小鬼與野小狗——文學作品集》《心詩——山歌200首》和《新中國60年兒童短劇選》。這樣,此“10本書”將伴隨他“邁步百歲”。說到這里,孫毅哈哈大笑。
孫毅,圈內人稱其“老頑童”,對此雅號,他悠然自得,他的上網戶名就由拼音“LWT1923”組成。“老頑童”一點不假,90高齡的他還能騎著電瓶車穿梭于大街小巷。那是前年,我知道,他與“同庚老兄”任溶溶關系不一般。任老由于身體方面的原因,已經閉門謝客。對于這位為兒童作出畢生貢獻的翻譯大家,我很想采訪,正是買了孫毅的面子,任先生才“破格”同意見我。那天,我騎車來到孫毅家,放下車正準備打的,孫毅卻推出了他的電瓶車。“這,太危險了!”我緊張地說,“這怎么行?”孫毅笑了,“怎么不行?我天天騎。”站在一旁的他夫人彭新琪老師發話了:“沒事,他天天騎。”我還是不放心,但終究沒能拗過孫毅,只好同意騎車同去任溶溶家。我們一前一后,從鎮寧路,過靜安寺,一直來到泰興路。其中七轉八彎,孫老卻是熟門熟路。
任先生已在客廳等我們。兩老相見甚是親熱,看得出他們
孫毅生于1923年,他的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是在恒豐路橋下、父親開的茶館里度過的。孫毅回憶道:“每天天還沒亮,老茶客們就上來喝茶。一位流浪藝人抱著破京胡,嘶啞的一聲‘催馬加鞭迷了道……’麒麟童的《追韓信》把我從夢中驚醒。接踵而來的是南腔北調的賣唱……我從各種韻味中逐漸聽懂了不同方言的地方戲——滬劇、越劇、淮劇、評彈以及上海的滑稽、小熱昏等。”
或許是從小的熏陶,孫毅青年時代,就立志于當演員。他爸雖一字不識,卻認為當戲子“下三流”而拼命反對。孫毅全然不顧,偷著把逼他去讀英文夜校的錢,報名進了上海電影話劇專科學校。是抗日戰爭的爆發和解放戰爭的開始,打破了他的演員夢。他投入到當時上海學生與工人的愛國民主運動中。他拿起筆寫傳單、快板、朗誦詩、活報劇,這些合轍押韻的語言文字,像犀利的匕首,在當時反饑餓求民主斗爭中起著作用。
1946年,孫毅讀到了宋慶齡對下一代提出戲劇教育的主張:“希望中國有個專為兒童演出的劇團,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通過戲劇培養下一代,提高他們的素質,給予他們娛樂,點燃他們的想象力,是最有教育意義的事。”
這不啻是盞明燈,更是一個火種,點燃了孫毅把舞臺當講臺,把劇場當課堂的理想追求。
當時宋慶齡不顧環境艱險,在中共地下黨劉厚生等人協助下籌建了“兒童劇團”。1947年,畢業于“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孫毅,沒有去當記者,出于對戲劇的愛好,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中國少年劇團”。地下黨老大哥、兒童文學家包蕾成了他的老師。包蕾當時寫戲劇和電影已經很出名,在參與他編劇的《胡子與駝子》《巨人花園》演出中,包蕾教孫毅如何寫劇本:設計故事確定中心任務、勾勒相關人物、拉互相之間的矛盾線,故事動作一結構,戲就出來了。孫毅學著為劇團寫了反映孩子苦難生活的《新漁光曲》《壓歲錢》《病從口入》等短劇,這些小戲到學校演出后受到歡迎。
解放后,孫毅被調入中國福利會兒童劇團,這是他夢寐以求的地方。為赴北京演出,他趕寫出木偶劇《兔子和貓》。1952年,兒童劇團來到中南海為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演出,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夠上演,孫毅寫戲的勁更大了。
調任辦雜志,寫劇本“矢志不移”
沒想到,此時《兒童時代》雜志剛創辦,極需要專業人才。1953年2月,中福會決定調孫毅擔任副社長、主編,要離開這樣的正規劇團,他當然不愿意。出于對干部的愛護,當宋慶齡知道孫毅懷有編劇夢時,特在簽發調令時,除任命為兒童時代社副社長外,還讓他同時兼任兒童劇團的創作室主任。這讓孫毅高興啊,因為雖走上了兒童文學編輯崗位,但仍能為“最有教育意義的事”繼續奮斗。所以孫毅在《兒童時代》創業7年,從未放棄業余創作。他創作出版了兒童劇《一張電影票》與《小白兔和小花貓》。同時,還為中國福利會少年宮寫了舞劇《群雁高飛》和歌舞劇《公雞會生蛋嗎》,參加首屆和第二屆“上海音樂之春”演出,并獲獎。

孫毅作品集
1963年,新建立的“上海木偶劇團”急需編劇,把孫毅調去擔任編導組長和藝委委員。在木偶劇團五年,孫毅對現有的木偶制作進行了改革,將當時只能演傳統京劇的木偶發展成可以演民間故事、演童話,特別是可演現代人物的新木偶。與此同時,他創編演出了《南京路上好孩子》《南方少年》等十出大型木偶劇,和《毛毛小淘氣》《蘿卜是誰拔的》《老貓釣魚》等十多出短劇。其中獲獎的《五彩小小雞》現在還在上演。
1981年,上海市婦聯老領導看中了孫毅,將他調去創編婦女雜志,這樣又一次把他從最愛好的戲劇專業單位調回編輯崗位。在婦聯五年,孫毅參與創刊《為了孩子》《現代家庭》兩本雜志,在擔任領導的同時,他的業余創作仍未停止,寫出了《培養勇敢精神》《翻筋斗》等兒童劇、兒童相聲、曲藝五本集子,約十多萬字。他主持的《為了孩子》還和《少年文藝》《少先隊活動》雜志一起,為繁榮上海兒童曲藝舉辦了兩次全國兒童相聲曲藝專場創演活動。
1986年,孫毅離休了。離休那天,他想,從此可以放手干編劇了,但現實并不是他所想象的美,少年兒童報刊因不能賺錢,已不發表諸如兒童劇等作品;而學校迫于“應試教育”,美育已得不到重視,演兒童劇更成了一種奢望。但孫毅明白,孩子健康成長離不開美育和藝術。“寓教于樂”,孩子們是需要娛樂的。為此,他重新開始為孩子們寫劇,并不求名利,主動送到少年宮和各學校,“我的報酬就是孩子們的歡樂與歡笑,他們饋贈我的歡笑,是我的無價之寶。”
2002年,《少年文藝》給任溶溶、圣野和孫毅頒發了突出貢獻獎,捧著鮮花和獎狀,孫毅夜不能寐。夫人彭新琪早就讀懂了孫毅,知道孫毅多么希望能將過去創作的兒童劇本匯總出版。于是,在夫人幫助下,一個自費出版《孫毅兒童戲劇快活叢書》的計劃醞釀起來。少年兒童出版社與上海教育出版社大力支持,如本文開頭所言,一套6本的叢書出版了。這套叢書大多贈送給了有關文化教育單位,以及各區學校、希望小學等。

溫家寶給孫毅的信

孫毅與“同庚兄弟”任溶溶(左)親切交談
山歌唱了七十年
孫毅說,他一生只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這實在是謙虛。我知道,他兒童文學創作的另一成果,就是童謠和詩歌。他曾聽取夫人的意見將其統稱為“山歌”。從1947年,孫毅在《新少年報》上發表第一首童謠《小鐵匠》起,他的山歌已唱了快七十年。
“我的童謠為孩子而寫,為孩子而唱。”孫毅說,“所以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遵守公共秩序,提倡社會公德,是我永恒的題材。”如《洗臉》《刷牙》《剃頭》《衛生好習慣》《美麗眼睛》《媽媽好幫手》等,音韻和諧,朗朗上口,易記易傳;而《祖國燦燦爛爛的》《家鄉好春光》等以祖國的山河美景,建設新貌,引領孩子們熱愛家鄉熱愛祖國。
“我的名字叫丁丁/爸爸給我起的名/要問為啥叫丁丁/學習雷鋒‘兩個釘’/一學雷鋒‘小鐵釘’/能擠能鉆不怕硬/擠出時間勤學習/學深學透靠鉆勁/二學雷鋒‘螺絲釘’/哪里需要哪里擰/祖國是座大機器/機器全靠它固定/小鐵釘,螺絲釘/學習雷鋒兩個釘/丁丁就愛學雷鋒/越學雷鋒越聰明。”這是孫毅去年的作品,童謠圍繞“兩個釘”唱出了孩子學雷鋒釘子精神的心聲,隱含著孩子甘為祖國獻身的愿望,內涵深刻,意味深長,此作在2013年全國童謠大賽中榮獲成人組一等獎。
數十年來,孫毅幾乎天天吟唱:從辛亥革命到地下少先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從鐵錘鐮刀到黨的90年輝煌……1997年到2013年,孫老已連續7次榮獲全國以及上海童謠的大賽獎。
2008年,上海作家協會和兒童時代社為他召開了研討會,并印發了他的山歌集《心詩》。會后,他想,既然《心詩》是他吐露心聲之作,何不寄給黨和國家領導交交心呢?于是他在2008年最后一天寄出了他的作品。沒想到,2009年1月14日溫家寶總理就親筆回信鼓勵:“您年事已高,仍筆耕不輟,關心國家大事,令人感佩。詩寫得很好,我很愛讀。”
一句話開始的戀愛
孫老的愛人彭新琪,筆名辛奇、沙妮。1951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歷任《兒童時代》《收獲》《上海文學》雜志編輯、編審。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專著《動畫大師萬籟鳴》《包身工的眼淚》《巴金的世界——親情、友情、愛情》《友情依舊》等。《偷橘》《巴金的世界——親情、友情、愛情》分別獲1994年、1998年青少年優秀讀物獎。1988年曾獲全國文學期刊優秀編輯獎。
1982年我入職市文聯,彭老師時任《上海文學》編輯。當時我們在一幢大樓,我知道她是我的大學姐,巴金先生好友靳以的學生,自1957年《收獲》創刊就當編輯,為培養作者作出了貢獻。很快我還知道了,她與孫毅老師是對伉儷,但當初他們如何結為連理自然不會去打聽。這次正好借與孫老“促膝交談”的機會,便不由相問。孫老笑了,笑得那么甜。是啊,已過金婚的他,回憶當初的一幕,怎不讓他喜形于色。
原來,孫毅時為兒童時代社的領導,彭新琪從上海市少年宮調到該雜志當編輯。孫毅說,那時我們的婚姻其實是由組織安排,經物選、“審查”,組織給我“相中”了彭新琪。當然“自由戀愛”還得我自己談。
孫毅清楚地記得,那天已經下班,別人紛紛離開了雜志社,忙完了手頭的工作的彭新琪卻被約請來到社長室“談話”。談了一些工作后,要進入正題了,孫毅此時開口如登天難,辦公室的空氣凝固了,憋了好一會的孫毅終于吐出了一句話:“我們好,好嗎?”話沒說完,他的臉已經紅脹,而彭新琪的臉也紅了。此時雙方都沒了話語。就這樣,一句話結束了首次戀談。
接下來,孫毅奉命去北京參加會議。這讓孫毅找到了向彭新琪表白的機會,他幾乎是每天一信,向她匯報自己的出生與經歷,如何當學生,如何參加革命,又如何愛上兒童文學創作。“鴻雁傳書”,孫毅的真實和坦誠讓彭新琪產生了敬意和好感。半月后,當孫毅回到上海,兩人已從相識到相知。
孫毅說,或許兩人都胸襟坦白、彼此尊重,我們的戀愛期很短,1955年,我們結婚了。不久,有了我們的孩子。此秦晉之好,一結就五十多年。雖風風雨雨,但文學把他們緊緊連在了一起。
“巴老給我的人文精神”
彭新琪從《兒童時代》到《收獲》創刊,到后來轉入《上海文學》,從編輯到編審,直至退休,至今還在編書,其編輯生涯六十年。
“‘把心交給讀者’,幾十年來,是巴金先生教我如何當編輯,是巴老的言傳身教讓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文精神。”那天彭老師告訴我。
彭新琪清晰地記得,那是十年動亂結束,《上海文學》剛復刊。此時編輯部開始舉辦文學青年座談會、講習班。青年人敬仰巴金,很想見見他,聽他講文學創作的問題。領導把邀請巴老來講習班的任務交給了彭新琪。
彭新琪與巴金很熟,去巴金家一談,巴老很快同意了與文學青年見面,但表示“我不了解情況,講話就不講了。”當時巴金已經74歲,經過“文革”九死一生的磨難,又經受了愛妻病逝的悲痛,已是心力交瘁,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答應了和文學青年見面。

孫毅、彭新琪夫婦結婚照

《巴金的世界》(彭新琪著)

彭新琪與巴金在一起
隔天,彭新琪去接巴老。那不是用轎車去接他,而是陪他從武康路寓所走到淮海路的公交車站乘公交車到陜西南路站下車,再沿陜西路走過兩條馬路到巨鹿路作協大樓。電車很擠,沒有人讓座。誰也沒注意這位穿著藍卡嘰布上衣,腳穿松緊口黑布鞋的小老頭是位享譽世界的文學巨匠。那天擠車,步行,巴老相當辛勞,但當他出現在文學青年面前時,顯得精神矍鑠、毫無倦容,他的樸素隨和、和藹可親給文學青年留下了極深印象。
文學巨匠的身影就這樣,一直留在彭新琪的腦海里,正是他的精神不斷激勵她以后如何培養作者,培養讀者。
作為巴老的晚輩和學生,彭新琪的一本《巴金的世界》專著,不僅詳細記述了巴金的文學和人生,而且為文學史留下了極珍貴的資料。
巴金懷念夫人蕭珊的文字很多,但寫巴金和蕭珊愛情的文章卻很少,不少作家不敢觸動巴老這個感情的“禁區”,但彭新琪認為,巴老也是人,他也有友情、親情和愛情。揭開其面紗,才能更準確地認識巴金。于是,彭新琪敢于去做研究。
在電視連續劇《家春秋》放映時,彭新琪直言巴老的感情問題,“別人以為你是覺慧,覺慧和鳴鳳相愛確有其事。你在成都老家愛過丫頭嗎?”巴老說:“沒有過。我們那樣的封建大家庭是不允許的。”彭新琪對巴老說準備寫他和蕭珊的愛情故事,沒想到巴老很爽快地答應了,并用了四五個半天的時間向彭新琪講述了他們的故事。彭新琪說,在巴金與蕭珊28年的婚姻生活里,他們相親相愛,沒有紅過臉,沒有爭吵過一次。在“文革”最痛苦難熬的日子里,蕭珊為了不讓巴金擔心,隱瞞了受到北京來的紅衛兵銅頭皮帶毒打的痛苦,巴金也向蕭珊隱瞞著自己所遭受的種種非人待遇……所以,巴老的人文精神貫穿于他的人生和生活,也包含在他的愛情中。彭新琪不無感慨:“巴老的人文精神也同樣一直引導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

甘當人梯,攜手作者見真心
巴金兒子李小棠,靠著自己的努力,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個“文學新人”。首先是姐姐李小林發現了他,當從弟弟手里接看他的處女作《機關軼事》時,禁不住發笑,因為那里面有太多的“黑色幽默”。如果是別人的作品,無疑她會把它發表在她負責的《收獲》上,但誰讓作者是她弟弟呢,她不能不避嫌疑。于是,她一邊將稿子交小棠修改,一邊告訴了在《上海文學》當編輯的彭新琪,說小棠寫了篇小說,有些基礎,現在正在修改,等修改好了想讓她看看。彭新琪聽了很高興,當他看到《機關軼事》后,覺得作品不但幽默風趣,而且主題鮮明,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寫作基礎很好。送審后她對李小林說,已通過審稿,《上海文學》決定刊用。李小林馬上關照她千萬別說是李小棠的作品,按稿子上寫的“李曉”筆名發表。彭新琪明白:巴金的兒子不愿意靠父親的聲譽登上文壇,巴金的女兒也不愿意讓人誤會用手中的權發表自己弟弟的處女作。但彭新琪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責任把這樣一個新人新作推薦給讀者。刊物出版后,北京的《小說選刊》要轉載,問作者簡歷,彭新琪只告訴他們:李曉,1950年生,安徽農村插隊6年,后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畢業后在一個機關里工作。后為匯寄稿費,要作者地址,這才把真情傳開。以后,彭新琪又約李曉寫第二篇作品。他沒有辜負彭姐的鼓勵,交給她一篇題目叫《繼續操練》的小說,依然是一篇帶有作者特有的機智幽默之作,后來得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作為老編輯,彭新琪甘做人梯,攜手青年,培養作者無數。在當今文壇閃閃發光的作家中很多都受過她的教悔。如程乃珊,當年她的處女作《媽媽教唱的歌》投給《上海文學》,李楚成、費禮文和彭新琪看后都提了意見。作為責任編輯,彭新琪更是直接指導程乃珊修改。三次修改后,才發表在該刊1979年第7期上。這篇文章對程乃珊影響很大,不久,她聽取彭新琪的意見,又寫出了《天鵝之死》。自此,與彭老師結為“忘年之交”。彭新琪退休后,在一次聚會上,程乃珊仍感慨“沒有彭老師,沒有我今天。”原來,她寫《藍屋》《金融家》時都得到過彭老師的幫助。
旅美作家曹冠龍,原是上海汽車修理四廠的工人,“文革”后,他的《三個教授》中的《鎖》在上海文學發表,自此與彭新琪建立了親密關系。從1979年到1983年,他每年都有小說在《上海文學》上發表。彭新琪有次來到他的假三層閣樓,僅十多平方,卻是三代四口人的家。當彭新琪知道曹冠龍的文章是在床頭寫出來時,她忍不住了,經向文聯和編輯部領導匯報后,找了當時任南市區區長的作家李倫新先生。在他的關心下,區房管部門為曹冠龍解困,在浦東配了一套住房,在新環境中,曹冠龍后來寫了不少作品。
最有意思的是茅盾獎得主周大新,當初還在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學習,利用課余時間寫成的《黃埔五期》投給了《上海文學》,彭新琪讓他幾次在“生活化和注意用細節刻畫人物”上修改,才得以發表。二十多年后,至今還未與彭新琪謀面的周大新卻在一次談他創作體會時提到了彭新琪,說當初是彭老師的幫助,才使他的學作得以發表。
退而不休,為“老祖母們”當主編
當肩負幾十年的文藝工作擔子早已卸下,本該心安理得享受含飴弄孫之樂的彭新琪卻無法放下手中的筆。她說,逝去的生活和接觸過的一些人時時浮現出來:酸甜苦辣,也是不可多得的財富。自省、追憶、理解、情誼、感恩,揮之不去。她驚異地看到:老祖母們經歷過的生活竟是那么曲折、坎坷,幾乎是解放后歷次運動的縮影。于是,她建議老祖母們,你們近年來寫了這么多文章,我們合出一本《七人集》好嗎?想不到都欣然同意。
彭新琪主編此書,所選的七位上海女作家是:羅洪、歐陽翠、歐陽文彬、黃宗英、姚芳藻、黃屏和她自己。這七位,伴隨著新中國的成長,活躍在中國文壇的前沿,在她們步入八十歲、九十歲,甚至臨近百歲高齡時仍筆耕不輟,以其豐厚的歷史積淀和思想感悟,向我們真實展現了中國文學界、文化界讓人刻骨銘心的一段段歷史。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王安憶特為此書作序——《我的阿姨們》:“那些不堪的歲月,她們都是見證。而我則是要付出心智和虔敬去了解她們,她們經過的時代,我不可望其項背。”
《七人集》,2009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甫一亮相就獲得好評。而孫毅對夫人的評價卻是:“她是個平凡的俗人,平生沒有偉大的追求抱負,凡事適可而止,不過,她努力做到了處事認真誠信,待人熱情真誠。這也是我最為欣賞的。”
在稱贊聲中,彭老師的編輯生涯至今沒停息下來。這兩年,她編選的《巴金蕭珊雙葉集》已出版,《生活如此多彩》不日即可與讀者見面。

彭新琪與老祖母級作家黃宗英(右二)、歐陽文彬(右一)、姚芳藻(左一)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