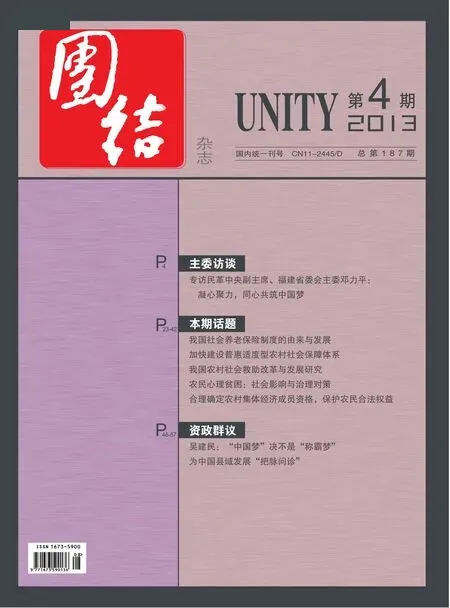農(nóng)民心理貧困:社會影響與治理對策
◎王洛忠 李唯真
自2006年中央提出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以來,我國農(nóng)村的面貌和農(nóng)民的生活都有了極大的改善;但在農(nóng)民物質(zhì)生活逐漸豐富的同時,農(nóng)民心理精神方面的匱乏也逐漸顯現(xiàn)出來。據(jù)媒體報道,中國平均每年約有28萬人死于自殺,其中80%來自農(nóng)村。多項農(nóng)民心理健康狀況調(diào)查研究顯示,我國農(nóng)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國正常人的平均水平。農(nóng)民心理貧困問題已經(jīng)不容忽視。
一、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主要表現(xiàn)
根據(jù)美國學(xué)者英格爾斯的研究,心理貧困是相對于物質(zhì)貧困而言的,是指人的道德、信仰、理想、價值觀、風(fēng)尚、習(xí)慣等生活觀念、價值取向等,不能滿足現(xiàn)實生活需要,落后于社會主要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的狀態(tài)。在我國,一些學(xué)者認為心理貧困是指由于經(jīng)濟貧困等原因,給人們帶來的精神迷茫和心理困惑等一系列個性特征和心理健康方面的負性變化。在我國農(nóng)村,農(nóng)民心理貧困最主要的表現(xiàn)有過度的保守心理、依賴心理、焦慮心理和自卑心理等。
(一)保守心理
現(xiàn)代農(nóng)村中,農(nóng)民 “既是傳統(tǒng)文化的守望者,又是現(xiàn)代文明的倡導(dǎo)者。正是在這種相互矛盾的雙重角色扮演中,農(nóng)民遭遇了空前的精神迷失與心理困惑”(李景春,2006)。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強大慣性的文化因子,使得農(nóng)民依然保留著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塑造成的安于現(xiàn)狀、思想封閉、觀念保守的性格特征:不思進取、頑固僵化的鄉(xiāng)土主義觀念;小富即安、目光短淺的小農(nóng)意識;墨守成規(guī)、循規(guī)蹈矩的生活方式;不敢競爭、害怕風(fēng)險的落后心理;不愿投入、不求創(chuàng)新的懈怠心理,不學(xué)科學(xué)、僅憑經(jīng)驗的盲目心理;等等,已經(jīng)成為我國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和農(nóng)民自身發(fā)展的重大阻礙。
(二)依賴心理
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靠天吃飯的特點,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長期的壓迫和剝削,使得傳統(tǒng)農(nóng)民形成了忍辱負重、依賴他人的個性。計劃經(jīng)濟時代,農(nóng)產(chǎn)品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體制又從另一方面使農(nóng)民養(yǎng)成了依賴心理和惰性心理。即使是現(xiàn)在,“等、靠、要”的心理也占據(jù)著一部分農(nóng)民的主流意識。此外,有研究顯示,女性農(nóng)民更容易在經(jīng)濟和心理兩方面產(chǎn)生對他人和社會的依賴,特別是心理上的依賴,在潛意識里依然根深蒂固,缺乏應(yīng)有的自我意識和獨立意識,對農(nóng)村女性的心理健康危害較大,表現(xiàn)為農(nóng)村女性心理疾病發(fā)生率和自殺率都明顯高于男性。
(三)焦慮心理
運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對我國部分地區(qū)農(nóng)民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我國農(nóng)民在焦慮因子上與全國常模差異極其顯著,表明焦慮心理是我國農(nóng)民心理貧困問題的重要表現(xiàn)。農(nóng)民的焦慮心理主要表現(xiàn)為身份認同焦慮和安全感缺失導(dǎo)致的焦慮。城市規(guī)模的急劇擴張和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guī)模轉(zhuǎn)移,不但導(dǎo)致農(nóng)村留守人員中傳統(tǒng)社會關(guān)系的斷裂,也導(dǎo)致一個廣泛的農(nóng)民工群體在城市中產(chǎn)生了身份的錯位,農(nóng)民工渴望在城市中有所作為,卻遭受到 “二等公民”的歧視待遇,在各方面遭遇社會排斥,無法滿足生理、安全、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等多重需要。在農(nóng)村,我國長期的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導(dǎo)致農(nóng)民在法律地位、政治權(quán)利、社會保障等生產(chǎn)生活的多個方面都缺乏安全感,而鄉(xiāng)村社會關(guān)系的斷裂和基層公共服務(wù)的闕如更加深了這一不安和焦慮。對留守農(nóng)村的弱勢群體而言,老無所依、幼無所托和女性持家壓力往往產(chǎn)生難以治愈的心理問題。
(四)自卑心理
低自尊、自卑感強是心理貧困的典型表現(xiàn)。農(nóng)民不但在傳統(tǒng)觀念中低人一等,在現(xiàn)代社會中也在多個方面遭到排斥。分散的、原子化的農(nóng)民不僅在涉及集體利益的事項中無法一致行動,而且往往無力抵制外來力量對個體權(quán)益的侵犯,只能忍氣吞聲,自認低人一等。久而久之,農(nóng)民已經(jīng)習(xí)慣了自己弱者的地位。再加上文化水平低下、心胸視野狹窄、宿命論盛行等因素,造成農(nóng)民對自身價值認識不到位,加劇了農(nóng)民的自卑心理。
二、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社會成因
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產(chǎn)生既有經(jīng)濟、社會、文化層面的宏觀因素,又有家庭、鄰里、親情等生活空間弱化的人際因素,也有農(nóng)民自身素質(zhì)等個體因素。農(nóng)民心理貧困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保守心理成為我國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和農(nóng)民自身發(fā)展的重大阻礙。
(一)經(jīng)濟收入水平低
對我國不同地區(qū)農(nóng)民心理健康狀況的多項調(diào)查均顯示,家庭收入與農(nóng)民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顯著相關(guān)關(guān)系,低收入家庭的農(nóng)民具有的心理健康水平往往偏低。低收入不僅在物質(zhì)上限制了農(nóng)民應(yīng)對生產(chǎn)中產(chǎn)業(yè)調(diào)整、天災(zāi)人禍等風(fēng)險的能力,也限制了農(nóng)民接受教育、提高人力資本、積累社會資本的可能,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低收入農(nóng)民的自卑心理和宿命心理。同時,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落后還造成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等問題,農(nóng)民難以獲得各種必要的信息、見到更多的世面、享受公平的服務(wù),思想觀念處于高度的封閉狀態(tài),文化生活處于極度的匱乏狀態(tài),對農(nóng)民心理貧困問題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二)社會排斥現(xiàn)象嚴重
農(nóng)民在經(jīng)濟、政治、社會生活和基礎(chǔ)設(shè)施、社會福利、公共服務(wù)制度中長期遭受著社會排斥,導(dǎo)致農(nóng)民強烈的“無權(quán)感”和“相對被剝奪感”,形成自我形象低落、強烈的無助感和難以改變的宿命觀等心理貧困狀態(tài)。表現(xiàn)為:在經(jīng)濟上,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剪刀差導(dǎo)致農(nóng)民利益受損,城鄉(xiāng)差距擴大加重農(nóng)民心理貧困;在政治上,農(nóng)民缺乏有效的利益訴求和表達機制來維護與增進自身利益,地方強勢群體憑借其強勢地位影響當(dāng)?shù)卣咦呦颍纬蓛?nèi)部社會排斥;在社會生活中,城鄉(xiāng)二元公共服務(wù)結(jié)構(gòu)使占全國人口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被排斥在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外,遇到困難得不到應(yīng)有的救助;教育、文化等基礎(chǔ)設(shè)施的缺乏限制了農(nóng)民人力資本的提升;日常生活中“農(nóng)民工”、“鄉(xiāng)下人”、“鄉(xiāng)巴佬”等標(biāo)簽嚴重傷害農(nóng)民的自尊和自信等。
(三)農(nóng)民原子化的影響
賀雪峰(2011)指出,當(dāng)前中國農(nóng)民已經(jīng)成為一個 “半熟人社會”,農(nóng)民的原子化使他們不僅在涉及群體利益的公共服務(wù)供給中無法一致行動,而且無力抵制任何外力的侵犯,他們的無力感使他們逐步學(xué)會順應(yīng)時代,順應(yīng)社會,忍氣吞聲,忍辱負重。在農(nóng)村,留守的老人、婦女等弱勢群體無法在公共空間中獲得交流與支持,心理壓力得不到抒發(fā)和緩解,往往產(chǎn)生抑郁、自殺等嚴重后果。
(四)農(nóng)民文化素質(zhì)偏低
文化素質(zhì)偏低是導(dǎo)致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需要農(nóng)民具有較高的科學(xué)文化知識,而文化程度低下的農(nóng)民往往無法迎接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和市場機制的挑戰(zhàn)。心理上的閉塞、保守和依賴使得很多農(nóng)民不愿接受新的觀念、知識和技術(shù),經(jīng)濟上的孱弱、窮困和落后使得很多農(nóng)民不能接受新的觀念、知識和技術(shù)。另一方面,在焦慮、自卑等心理問題出現(xiàn)時,受過良好教育、文化層次較高的農(nóng)民不但懂得自我心理調(diào)適,而且知曉救助途徑,往往能夠及時化解心理壓力,治愈心理疾病;而保守、無知的農(nóng)民不但不懂得自我心理調(diào)適,甚至不知道該往何處求援。農(nóng)村 “90%的自殺死亡者,從未尋求過任何幫助。”
三、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社會影響
農(nóng)民是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的主體,農(nóng)民心理健康狀況直接影響農(nóng)民的行為動機、行為偏好,進而影響著農(nóng)民的行為模式。從社會發(fā)展角度來看,農(nóng)民心理貧困對農(nóng)民個體和農(nóng)村整體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一)心理貧困影響農(nóng)民個體的身心健康、子女成長發(fā)展和家庭生活質(zhì)量
目前我國農(nóng)村心理健康服務(wù)體系幾乎處于一片空白,農(nóng)民心理貧困往往發(fā)展為嚴重的心理障礙,導(dǎo)致偏執(zhí)、抑郁、狂躁等心理病癥高發(fā)頻發(fā),嚴重者甚至走向自殘和自殺。調(diào)查顯示,我國農(nóng)民的精神病性因子普遍偏高,許多農(nóng)民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2009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報告更是指出,中國的自殺死亡者80%來自農(nóng)村。心理貧困下的農(nóng)民自卑、自閉、無知、彷徨,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感都相對偏低,嚴重影響農(nóng)民個體的身心健康。
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影響具有代際延續(xù)性,因為家庭環(huán)境對兒童成長至關(guān)重要,兒童極易受到家長心理貧困的負面影響,形成類似的保守、依賴心理,并在焦慮、自卑的環(huán)境中發(fā)展出封閉、膽怯的人格,難以開展健康的社會交往,從而形成新一代的心理貧困。在城鄉(xiāng)二元體制下,很多農(nóng)村兒童或者被父母帶進城市打工,成為城市邊緣人群中的弱勢群體,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和保護;或者被留在農(nóng)村成為留守兒童,成長在缺乏父母親情的孤獨環(huán)境中,承擔(dān)沉重的生活壓力。在這種情境中,尚未形成穩(wěn)定人格的兒童極易發(fā)生心理問題,心理貧困從多個方面影響農(nóng)村子女的健康成長。
有調(diào)查顯示,婚姻家庭狀況對農(nóng)民心理健康水平有顯著影響,處于穩(wěn)定和諧的家庭關(guān)系中的農(nóng)民心理也較為健康;反過來,家庭成員的心理貧困將會影響整個家庭的生活質(zhì)量。農(nóng)民心理上的迷茫、盲目、保守、落后會影響到家庭收入的提升、鄰里氛圍的和諧,進而影響家庭生活水平;農(nóng)村婦女對丈夫的依賴心理導(dǎo)致她們?nèi)狈Κ毩⑷烁瘢狈ιa(chǎn)致富的能力;偏執(zhí)、焦慮和自卑心理則破壞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聯(lián)系,造成家庭沖突,甚至在特定情形下演變?yōu)榧彝ケ┝ΑP睦韷毫Φ脑黾雍托睦韱栴}的發(fā)生是很多農(nóng)民夫妻反目、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
(二)心理貧困影響農(nóng)村整體的人口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
由于重男輕女、“女子無才便是德”等落后心理的影響,大量青壯年男性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愿意、也更容易進城務(wù)工,農(nóng)村留守人口日益老年化、女性化,農(nóng)村人口結(jié)構(gòu)失衡。全國婦聯(lián)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婦女已占中國農(nóng)村勞動力的60%以上。葉靜忠(2008)指出,老年人口成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主要維持者,目前80.6%的留守老人仍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趙蘭香(2011)認為中國農(nóng)村正處于“城鄉(xiāng)差距大——人力資本外逃——心理貧困產(chǎn)生——城鄉(xiāng)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惡性循環(huán)中。

由于重男輕女等落后心理影響,農(nóng)村人口結(jié)構(gòu)失衡問題日漸嚴重。
農(nóng)民的心理貧困和畸形的人口結(jié)構(gòu)直接影響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發(fā)展。農(nóng)民的保守心理、依賴心理導(dǎo)致大部分農(nóng)民安于墨守成規(guī)的生活方式,習(xí)慣了清貧的生活和弱者的地位,對農(nóng)業(yè)科學(xué)知識和市場經(jīng)濟的認識淡薄。王海濱(2007)對安徽西部山區(qū)236戶農(nóng)民的抽樣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有60%的家庭入不敷出,有35%的農(nóng)戶糧食不夠吃,卻有51%以上的農(nóng)戶對目前的經(jīng)濟狀況感到滿意或基本滿意,有38%的農(nóng)戶認為 “咱生來就是受苦的命”。不思進取、保守依賴的心理往往直接導(dǎo)致 “貧者愈貧、富而返貧”、“越窮越悲觀,越悲觀越窮”。
當(dāng)大量農(nóng)村精英群體轉(zhuǎn)移到城市后,在留守農(nóng)民保守、依賴、封建、忍氣吞聲的環(huán)境下,宗族和灰色勢力在一些地方逐漸代替了傳統(tǒng)熟人社會的鄉(xiāng)村秩序。賀雪峰(2013)提到混混、黑社會、地方勢力等在中國農(nóng)村快速成長,而在村民組內(nèi),農(nóng)民往往形成了宗族、小親族、兄弟等血緣共同體。不同背景的勢力通過相互串通、封官許愿、出錢賄選等方式直接插手或操縱基層選舉,同時又為了維護經(jīng)濟利益挑起械斗,激化了農(nóng)村社會矛盾,嚴重影響了農(nóng)村社會穩(wěn)定。
四、解決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對策建議
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成因多種多樣,與之相應(yīng)的治理對策也可以從國家、社會和個人等多個層面來探討。本文重點從國家和社會等宏觀層面來探討解決農(nóng)民心理貧困的對策建議。
(一)確立農(nóng)民的主體地位
農(nóng)民既是農(nóng)村的主人,也是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的主體,然而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社會排斥導(dǎo)致農(nóng)民產(chǎn)生“相對被剝奪感”,極易誘發(fā)心理貧困。在經(jīng)濟層面,政府應(yīng)當(dāng)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在財政上加大對農(nóng)村的投入和農(nóng)民的補貼,實現(xiàn)農(nóng)村產(chǎn)業(yè)升級和農(nóng)民就業(yè)增收,增強農(nóng)民經(jīng)濟上的安全感,讓農(nó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帶動基礎(chǔ)設(shè)施的全面升級和農(nóng)民生活的徹底改觀;在政治層面,應(yīng)該完善農(nóng)村基層民主制度,貫徹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治理農(nóng)村亂象,健全農(nóng)民利益訴求表達的渠道,建立農(nóng)民情緒宣泄的平臺,緩解和消減農(nóng)民負面情緒的產(chǎn)生;在公共服務(wù)層面,落實多項惠農(nóng)政策,確保農(nóng)民在勞動就業(yè)、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wù)領(lǐng)域與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待遇;在社會文化層面,增加農(nóng)民及其子女享受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的機會,實現(xiàn)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文化服務(wù)均等化,進一步增加農(nóng)民信息量,擴大農(nóng)民社會交往范圍,使農(nóng)民在開闊眼界的同時開闊心胸,增加經(jīng)濟收入的同時提升文化素質(zhì),提升社會地位的同時提升自我效能感。只有真正確立農(nóng)民在新農(nóng)村建設(shè)中的主體地位,讓農(nóng)民獲得更多政治、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資源,感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guān)注、關(guān)愛和關(guān)懷,才能重拾農(nóng)民的自立自強與自尊自信。
(二)完善農(nóng)村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
何蘭萍(2011)認為,重構(gòu)農(nóng)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間,有助于填補農(nóng)民由個體的原子化、疏離化帶來的精神空虛,以及由生產(chǎn)生活的不確定性引起的焦慮失落,從而彌補物質(zhì)世界中的匱乏和尊嚴。溫鐵軍(2011)認為,可以由政府牽頭構(gòu)建綜合性合作框架,提高弱勢農(nóng)戶自我發(fā)展能力。他認為從文化領(lǐng)域開展合作進入成本較低,見效快,農(nóng)村的文藝隊和老人協(xié)會都能夠以較小的成本使成員們獲得極大的物質(zhì)和精神福利感。賀雪峰(2009)從湖北省老年人協(xié)會的一項實驗中了解到,自從有了協(xié)會,參與的老年人 “一是覺得時間過得快了,二是身體好了,三是上吊自殺的少了”,原因在于老年人通過經(jīng)常性的集體活動和相互交流,找到了彼此的承認和尊重,找回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當(dāng)然,在完善農(nóng)村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的過程中,政府應(yīng)加強對農(nóng)村文化事業(yè)的財政扶持力度,引導(dǎo)農(nóng)村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消解傳統(tǒng)文化對農(nóng)民保守心理和依賴心理的不良影響。
(三)建立農(nóng)村心理保健體系
針對我國農(nóng)村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咨詢服務(wù)體系還基本空白的現(xiàn)狀,應(yīng)設(shè)立農(nóng)民心理保健專項資金,加大對農(nóng)村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詢服務(wù)體系的投入,將農(nóng)民心理疾病治療的藥物和器材納入新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報銷的項目中。一方面,在廣大農(nóng)村分期分批成立農(nóng)民心理健康咨詢室,定期或不定期開展農(nóng)民心理健康普查,鼓勵社會工作者及非政府組織在農(nóng)村開展心理健康知識的宣傳、教育和心理疾病的義診、治療等活動;另一方面,可以在農(nóng)村中小學(xué)、普通高校和農(nóng)業(yè)技校中開設(shè)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在農(nóng)業(yè)科技培訓(xùn)中增加心理健康講座等方式,通過農(nóng)民子女、農(nóng)村大學(xué)生、農(nóng)業(yè)科技能手向農(nóng)村和農(nóng)村的輻射作用,加強農(nóng)民心理健康教育,培養(yǎng)他們自我調(diào)節(jié)和控制的能力,通過自我安慰和相互幫助緩解心理壓力,通過自我體驗抑制不良情緒,通過自我激勵增大生活動力(李景春,2006)。
處于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中的農(nóng)民群體,一方面糾結(jié)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保守和依賴心理,一方面又因現(xiàn)代化的沖擊變得焦慮和自卑。在他們的生活中,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交等各項生活都裹挾著多重心理壓力,使得他們失去了最起碼的安全感,甚至失去了生命的意義。這樣的農(nóng)民群體既無法實現(xiàn)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也無法彌合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鴻溝、無力阻止人力資源外流的大潮,更無法重建鄉(xiāng)村秩序、找回心靈深處的家園。遭遇心理貧困的農(nóng)民亟需國家和社會的幫助,但國家和社會首先需要看到并理解他們的遭遇和無助。無論是從宏觀層面的經(jīng)濟、政治、社會的增權(quán)過程,還是文化、教育、心理保健體系的完善,又或者是簡單到一只文化隊、一個老年中心的成立,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會的關(guān)心,如此,農(nóng)民的心理貧困問題才能得到標(biāo)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