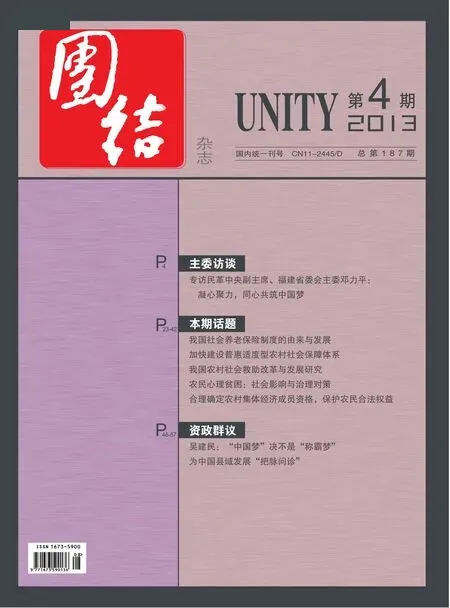合理確定農村集體經濟成員資格,保護農民合法權益
◎孫延平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和集體經濟利益分配引發的糾紛不斷涌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問題,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規等都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認識不一,做法各異,嚴重影響了糾紛解決的效果。本文結合實踐對此類問題淺談幾點看法,以期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探討,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所裨益。
一、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重要意義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是我國廣大農民最基本的身份權。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對完善我國農村法律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土地承包應當遵循以下原則:按照規定統一組織承包時,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權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4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以上規定中均出現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一詞,但如何認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至今我國法律及相關政策均未作出明確規定,一般多散見于集體經濟組織村民自治章程之中。由于不同地區的規定不盡一致,由涉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案件引發的爭議也較多。
第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直接關系到農村家庭承包土地的分配。按照 《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承包土地的權利。如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不能準確界定,家庭承包工作就難以順利開展;

《土地承包合同》對確定農村集體經濟成員資格,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有著重要作用。圖為湖北宜昌農民在認真研究 《土地承包合同》。
第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關系到農戶承包土地的多少。按照 《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5條規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農戶承包土地的多少與農戶成員的多少是密切相關的。而能作為承包土地計算基數的農戶成員應當是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
第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直接關系到特定人群特別是困難群眾合法權益的保護。在實踐中存在的特定人群(如“外嫁女”等)合法權益被侵犯的糾紛,如土地補償費分配、集體經濟利益分配等糾紛,其爭議的焦點和解決問題的關鍵,基本都集中在如何確定當事人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如果成員資格問題不能清晰界定,這類糾紛就很難處理。實踐中既已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糾紛納入司法調整范圍,而成員資格界定標準僅靠地方性規定和村規民約等來確定,顯然已不合時宜。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事關廣大農民的基本民事權利,屬于 《立法法》第42條第1項規定的情形,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具體規定,而不宜通過司法解釋等對此重大事項進行規定。從推動我國農村法治建設進程的角度,應當盡快從立法的層面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標準。
二、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基本原則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是指以本集體所有的土地利益為基本生活保障的自然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取得,應當以是否在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形成較為固定的生產、生活并依法登記常住戶口所在地作為依據。考慮到在當前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情況下,農村承包土地對未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仍具有唯一且有力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對一些特殊情形還應予以特別規定。通過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取得、喪失的原則規定和特殊規定,劃定成員資格的保有期間,并確立資格取得的唯一性原則。
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取得,應以在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生產、生活并以本集體所有的土地利益作為生活保障來源及依法登記常住戶籍為一般原則。這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然共同體特征的必然要求。戶籍是證明一個公民自然情況最直接、最基本的依據,應當依據集體成員資格的變動而遷移。但是現有戶籍制度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越來越不相適應,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關系認定上,也不宜單純以戶籍為判斷標準,對成員資格的認定始終都是一個需要綜合處理的問題,應綜合考慮戶籍、生產生活狀況和基本生活保障的來源。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定之后,還需要考慮資格確定基準日的問題。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取得的日期,應當以戶籍的取得日為準,新生嬰兒則應以出生日為準。能夠準確確定或有證據證明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生產生活或以其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日期的,則應以在前的日期為準,以便更好地保護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利益。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取得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原始取得是指通過人口的自然繁衍,生活在特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的資格取得方式,其表現形式主要是出生。如果父母一方具有成員資格,應結合出生人員實際落戶情況而定。只要以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依法登記為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即應取得成員資格。其中包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生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計劃生育和計劃外生育子女,自出生后應取得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加入取得是指原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基于一定事由嗣后取得的方式。主要包括婚姻、收養以及國防建設或者其他政策性遷入。經由婚姻或者收養關系,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生產、生活并將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的公民,應當具有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此外,因國防建設或者其他政策性原因,通過移民進入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生產、生活并依法登記所在地常住戶口的人,亦應取得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此外,在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時,還應考慮該人是否已經取得城鎮社會保障,或者依據現有制度很快就會取得城鎮社會保障,若屬于這種情況則不應再享有集體成員資格。
四、幾個難點問題的認定
1.在外經商、務工等人員成員資格的保護
基于出生、婚姻或者收養以及國防建設或者其他政策性遷入情形已經取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在實踐中可能因外出經商、務工等原因,長期脫離該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生產、生活,但這些人員在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之前,仍以該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若僅因其脫離集體經濟組織生產、生活而剝奪其成員資格,將導致這些人員喪失基本生活保障。因此,通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所體現的相應的成員權,確保其不至喪失唯一的基本生活保障是極其重要的,對鼓勵農業人口向二、三產業的合理流動和轉移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
2.“空掛戶”成員資格的排除
以戶口作為成員資格的重要標準,并不等于唯戶口論。除在外經商、務工等人員的成員資格問題以外,實踐中還存在大量的“空掛戶”。所謂 “空掛戶”,主要是指有關人員將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的目的,并不是要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生產、生活,而是出于利益驅動和其他各種原因,需要將戶口掛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的一種現象。在考慮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問題時,應當對其進行排除。因為他們僅遷入戶口,并未與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形成較為固定并具有延續性的生活格局。此外,對于遷入戶口后雖在所在地生產、生活,但其生活來源主要依靠離、退休金的離退休返鄉人員,也應當排除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3.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喪失
原則上,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未取得城鎮社會保障之前,應盡量不認定其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在這個原則下,因以下四類情形被注銷或者遷出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常住戶口的人,應當認定喪失成員資格:(1)死亡。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止于死亡。自死亡時起,該人原享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即已喪失。(2)取得了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應當只能在一個集體經濟組織內享有。自依法取得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時起,其原享有的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應隨即喪失。(3)取得城鎮非農業戶口,且享有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與家庭承包所具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相同,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對權利個體擔負著同樣的功能,因此二者不應同時享有。(4)取得城鎮非農業戶口,且納入國家公務員序列或者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當前,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在非設區市以及城鎮尚未普遍建立,取得其非農業戶口并不必然享有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因此仍需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村土地作為其基本生活保障。但如果已經納入國家公務員序列(包括法官、檢察官序列)或者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障體系,則其業已脫離原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需要。
4.學習、服兵役等人員的成員資格保留
此類人員雖喪失了原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常住戶口,但在其喪失成員資格之前,還是以原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否則將使農業人員繼續升學和服兵役的積極性受挫。實踐中有部分地方規定,大、中專院校在校學生保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已畢業的不再具有成員資格。這種規定顯然不完備。保留學習人員在因就業等原因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之前的成員資格,對農村人口素質的提高具有積極意義。此外,根據國務院 《退伍義務兵安置條例》和國務院、中央軍委 《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官退出現役安置暫行辦法》的規定,農村入伍的義務兵和初級士官,復員后應回農村安置,政府不負責安排工作和解決城市戶口。所以這類人員仍需要承包土地作為基本生活來源。而中高級士官和干部退役時,根據有關政策法規應作轉業安置,由國家統一安排工作,解決城市戶口。保留服義務兵或者初級士官兵役期間的成員資格對維護國家安全、鞏固國防事業意義重大。至于 “兩勞服刑”人員,其雖因違法犯罪行為喪失人身自由甚至是政治權利,但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并不因此喪失。其雖遷出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常住戶口,但遷入戶口所在地并不負擔其回歸社會后的基本生活保障。保留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對他們積極接受改造以及避免回歸社會后因生活所迫再次陷于犯罪深淵、真正實現改造目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5.與婚姻關系相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
在整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定問題中,這一類問題是最復雜的。基于經濟利益驅動,相對富裕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在婚嫁入相對貧困的集體經濟組織時,雖已實際在該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生產、生活,卻往往不遷戶口。但其既然脫離原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生產、生活,就表明其與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已不存在較為固定的集體生產、生活狀態,認定其仍然具有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將導致單一戶口標準所帶來的富裕集體經濟組織人口的畸形膨脹,加大該區域內人口與資源的“負壓差”問題。此外,從集體經濟組織自然共同體屬性角度出發,因婚姻進入本集體經濟組織農戶生產、生活所增加的人口應被視為自然共同體人口數量增長的途徑之一。因此以實際生產、生活所在地集體經濟組織認定其成員資格符合歷史形成的自然習慣。然而,實踐中的類似情況極為復雜。婚姻關系發生在持農業戶口人員之間,雙方婚后可能未在雙方原所在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生產、生活,而是在其他的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或者外出務工、經商。此時以其實際生產、生活所在地作為認定其成員資格的標準顯然不妥。面對這類情況,應當遵從習慣解決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并在具體實踐中保留一定裁量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