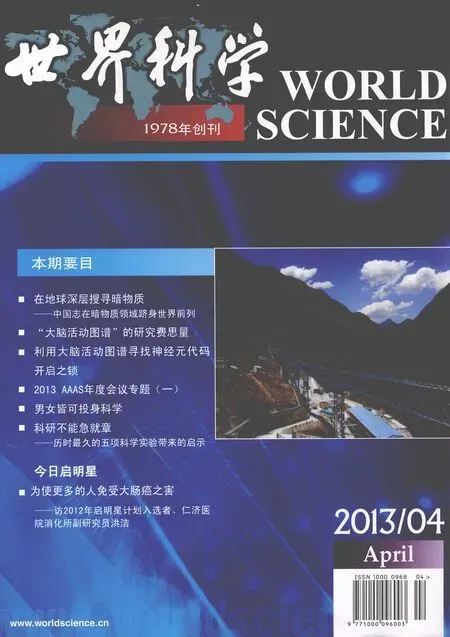科研不能急就章
——歷時最久的五項科學實驗帶來的啟示
方陵生/編譯
科研不能急就章
——歷時最久的五項科學實驗帶來的啟示
方陵生/編譯

伽利略1613年繪制的太陽黑子圖
● 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些實驗告訴我們:科研進展有時就像馬拉松賽,而不是很快就能見分曉的短程賽跑……《自然》雜志近期文章列舉了有史以來時間跨度最長的五個科學實驗和科研項目,其中有些研究項目的數據積累工作已持續了幾個世紀,有的每年產生數以百計的論文,有的10年才產生一個數據點。
科學發展是人類追求的一個長期目標,但一些具體研究項目卻往往是在一個較短時間尺度內進行和完成的,科學實驗或科研項目還要受到資金周期的制約。但也有一些科學實驗或科研項目難以在短期內完成,例如:人類壽命研究;地殼變動情況勘查;太陽表面變化觀察等,有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
如此漫長的實驗其過程受到各種外在條件和因素的挑戰,比如,研究重點的轉移、技術的變化,以及受到經費和人員變動的制約。盡管如此,一些有遠見的科學家的奉獻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將科學實驗的成果傳承了下去。其中一項長達90年的研究項目,是預測人類將擁有比現在更長壽命和更健康的生活,其他幾個例子也各自創下了歷時最久科學實驗和科學研究的記錄。
一、太陽黑子活動觀察和預測:歷時400年
400多年前望遠鏡誕生以來,包括伽利略在內的天文學家就一直在記錄太陽黑子活動,并記錄下他們的觀察結果。但早期觀察者并不知道出現在太陽表面的黑色斑塊究竟是什么,對產生太陽黑子的磁場也一無所知。直到1848年,瑞士天文學家魯道夫·沃爾夫(Rudolf Wolf)對太陽黑子開始了系統的觀察,并制定了一個計算公式,人們對太陽黑子活動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沃爾夫相對數(也叫太陽黑子相對數)今天仍然被用來測算太陽黑子活動的周期性變化。
2011年,比利時皇家天文臺太陽黑子數據分析中心 (SIDAC)主任弗雷德里克·克萊特(Frédéric Clette)在對太陽黑子活動的觀察研究中,利用了自1700年以來500多名天文學家留下的照片和手繪圖等數據資料。這些數百年積累下來的數據對預測太陽黑子活動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歷史遺產:太陽黑子活動的盛衰變化周期約為11年左右,其產生的帶電粒子流向四周空間噴發,對地球衛星和電子產品產生很大的影響。詳細的觀察記錄幫助研究人員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周期性循環,并精確預測強烈的太陽黑子活動事件。
“研究的持續時間越長,越能更好地驗證我們的理論。”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太陽物理學家利夫·斯瓦加德(Leif Svalgaard)說道。每年大約有200篇論文引用了太陽黑子活動的數據,涉及領域甚至延伸到了太陽物理學、地磁學、大氣科學和氣候科學之外的其他學科。
比利時皇家天文臺的SIDAC每個月都要從90名太陽黑子觀察者那里搜集數據資料,其中三分之二為業余天文愛好者,盡管他們用來觀察太陽黑子的小型光學望遠鏡的倍率比200年前天文學使用的望遠鏡強不了多少。克萊特除了作為一位天文學家在比利時皇家天文臺的“夜間工作”之外,還與另一位兼職人員一起負責太陽黑子數據庫的維護工作。
克萊特非常熱衷于與數百年前的同行們“一起工作”。他認為,盡管伽利略對太陽黑子活動的觀察數據并不全面,因為伽利略還要“忙著觀察行星等其他事情”。但他指出,人們仍然能從伽利略所繪制的太陽黑子圖中找到與現代繪制的太陽黑子圖的相同之處,并被這位天文學先輩的遠見所深深吸引。那些幾百年前繪制的太陽黑子觀察圖忠實地記錄了他們當時所看到的一切,并為后世提供了許多有用的信息。克萊特說:“忠實地記錄實驗數據是科學研究的一個基本點,不管最后的結果是什么。”
二、監控躁動不安的超級火山:歷時170年

曾用來監控火山活動的維蘇威火山天文臺原址如今已成為一座博物館
活動頻繁的維蘇威火山每幾千年就要猛烈噴發一次,最后一次發生于公元79年的火山大噴發,埋葬了整個龐培城。在此之前大約3 800年的一次火山噴發中,熾熱的火山氣體和火山巖漿覆蓋了如今的整個那不勒斯地區。自1841年建立以來的維蘇威火山天文臺觀測站,一直在密切關注著其觀測對象,記錄著火山地區附近的地震跡象。觀測站坐落在火山一側600米高的位置,以避免被火山噴發時的巖石碎片和熔巖流所波及。現任天文臺負責人馬賽羅·瑪蒂尼(Marcello Martini)說道,該火山觀測站所做的一切造就了當今火山學和地質學研究的雛形,
瑪西多尼奧·梅洛尼(Macedonio Melloni)是天文臺的首任負責人,在對熔巖磁特性的研究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對之后的古地磁學研究——地球磁場在巖石中的歷史記錄——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856年,第二任負責人路易吉·帕爾米耶里(Luigi Palmieri)發明了用來預測火山噴發的電磁地震儀,對地面震動的監測比之前的一些觀察儀器更為敏感。在帕爾米耶里及以后的幾任負責人的帶領下,觀測站對預測世界各地火山噴發的儀器開發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例如在二十世紀初,由朱塞佩·麥卡利(Giuseppe Mercalli)制定的級別劃分標準至今仍被廣泛用于對火山噴發程度的定級。
但古老的觀測站現今已不再擁有原來的作用。“早期階段是為了盡可能接近火山活動區域,但如今卻沒有必要了。”羅德島大學的火山學家哈拉爾德·西格森(Haraldur Sigurdsson)說道,如今大部分監控數據都可通過遠程地面傳感器發送到那不勒斯的地球物理和火山學研究所的實驗室中。1970年,天文臺原址建筑被改建成為一座博物館。
除了為科學理論提供數據信息之外,火山觀察站的另一個目的是用來預測火山噴發,1944年的成功預測就是一個明證。今天,那不勒斯的實驗室里,科學家們一天24小時密切關注著西西里北面的一個小島上的斯特隆波里火山、那不勒斯西面的坎皮佛萊格瑞火山口和伊斯基亞島。
西格森認為,火山學的未來不在于已知危險火山地區安放的傳感器,而在于可以觀察到所有地面變形的衛星雷達,利用衛星雷達發現火山噴發高風險地區。“我們應該朝著建立國際合作火山監測系統的方向努力,不是只盯著某座火山,而是在全球范圍內全面綜合地評估火山噴發危險。”

自1843年以來研究化肥對小麥產量影響的所在地洛桑
三、化肥對農作物產量影響的數據收集工作:歷時170年
長期研究項目的研究人員必須努力維護和保持研究數據的完整性及相關性。安迪·麥克唐納(Andy Macdonald)于2008年接手了一項農業實驗,即自1843年開始進行的礦物肥料和有機肥料對作物產量影響的研究測試。
這項實驗由化肥生產巨頭約翰·勞斯(John Lawes)在自己位于倫敦北部洛桑的莊園里發起進行,主要研究測試氮、磷、鉀、鈉、鎂和農家肥對幾種主要作物產量的影響,包括小麥、大麥、豆類和一些塊莖作物。
“二三十年的研究測試已經很好地回答了各種不同肥料所起重要作用的許多基本問題。”如今在洛桑研究所負責這項“經典實驗”的麥克唐納說道。實驗表明,氮的影響最大,其次是磷。階段性的實驗一直在進行著,以對新的想法進行測試,并與當前農業生產實踐保持密切聯系。比如在1968年,農民以莖稈較短的高產谷類作物取代了之前莖稈較長的谷類作物,麥克唐納指出,這些新品種農作物與傳統作物相比,需要更多的肥料。
“洛桑是長期農業研究的老前輩,”W·K·凱洛格生物站主任菲爾·羅伯遜 (Phil Robertson)說道。該生物站是密歇根州立大學所設立的一個長期農業研究站點,他指出,連續性的數據資料擁有巨大的價值,不僅有助于環境和生物學發展趨勢的研究,包括土壤中的碳儲存情況、入侵物種的影響等。這類影響只有在較長時間尺度內才能顯現出來,同時也為一些短期研究提供了平臺,比如,土壤中的硝酸鹽流失現象。
洛桑研究所從實驗開始以來,收集并保存了大約 30萬件植物和土壤樣本,2003年,科學家們從存檔樣本中提取了1843年的兩種小麥病原體的DNA,用以研究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對其產生的影響。
然而,讓資助機構對這類長期研究項目保持興趣比較困難。洛桑的研究資金來源包括政府資助、捐款以及勞斯去世前設立的信托基金。“即使在暫時不會有突出研究成果的時期,也應致力于維護研究數據的持續性。”去年參與設立美國農業部長期農業生態系統研究網絡的羅伯遜說道。“我經常會回想起勞斯,”麥克唐納說道,“為了確保實驗的持續和傳承,我深感責任重大。這些數據資料并不是保存在博物館里的老古董,也是當今科研的一個組成部分。”
四、天才兒童成長跟蹤調查:歷時90年
1921年,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劉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在加州開發的斯坦福-比奈智商測試法,確定了于1900年和 1925年期間出生的1 500多名天才兒童,并開始了對這些天才兒童的跟蹤調查。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縱向研究項目之一,也是歷時最長的對人類智力發展進行的研究項目,在時間跨度長達90年的時間里,對他們的家庭生活,所受教育,以及興趣、能力和性格等進行多方面跟蹤調查。

劉易斯·特曼進行了為時最長的人類智力發展研究
特曼的“天才遺傳研究”目標之一是要反駁當時的流行理論,認為天才兒童多表現為體弱多病、社交能力差、發展不全面等。即使是以特曼的天才標準,這項研究仍受制于某種局限。他的選擇方法是隨機的,測試管理工作主要基于老師們的推薦,不同人群的代表性也遠非全面 (90%以上為白人與中上階層,特曼甚至為自己的孩子報名登記)。
這項調查一直跟隨孩子們進入成年。調查發現,這些孩子們與其他孩子一樣健康,一樣能夠適應社會,他們通常都能成長為事業有成的快樂的成年人。隨著調查項目的進展,研究人員也在努力填補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或不足。
例如上世紀80年代,哈佛醫學院的心理學家喬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將特曼的研究數據補充到自己的成人發展的長期研究中;加州大學的心理學家霍華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在利用了特曼一些重要的記錄數據后發現,人的責任心——即審慎、堅韌與計劃性——這一在兒童時期和成年時期都能表現出來的性格特征,是預測長壽的一個關鍵性心理因素。“如果沒有跨越整個人類壽命長度的長期實驗形成的數據資料,是很難發現這一點的。”弗里德曼說道。
隨著當前科學的發展,縱向研究也在與時俱進,斯坦福長壽中心主任勞拉·卡斯坦森(Laura Carstensen)說道。新加入的調查研究人員將會補充一些新的方法,修改或丟棄那些他們認為不再有意義或過時的做法。“比如,我們將以與1900年時完全不同的方式,對心理健康進行評估。”從多種意義上來說,她認為:“90年的縱向研究數據資料,幾乎可以說是書寫下一部心理學發展史。”
瀝青滴漏實驗:歷時85年
1961年,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物理學家約翰·梅因斯通(John Mainstone)接手了一個古怪的小實驗,當時這個實驗在一個櫥柜里已經悄悄進行了34年。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觀察著這個實驗,并等待著見證它最引人注目的下一滴。
這個瀝青滴漏實驗 (Pitch drop experiment)是該大學第一位物理學教授托馬斯·帕內爾(Thomas Parnell)發起的一項長期性物理實驗,他想以此實驗向他的學生示范證明,在冷卻狀態下脆得可以用錘子敲碎的瀝青,也能夠像液體一樣從一個漏斗底部滴出,盡管是以極慢的速度進行著。他的這個小實驗成為了世界上最慢的沙漏,實驗結果也正如他所預測的那樣。瀝青的滴漏速度大約為每6-12年一滴,迄今為止已滴下8滴瀝青。梅因斯通預計,第9滴瀝青將于今年年底左右的某個時候滴下。

瀝青滴漏實驗,從 1927年至今只滴下了8滴
嚴格來說,這個實驗并不是科學發現的溫床。86年的時間里這一實驗只產生了一篇科學論文:該論文計算出瀝青的黏度大約是水的 2 300億倍。2005年該實驗贏得了搞笑諾貝爾獎。
從來沒有人見過一滴瀝青是如何滴下的,記錄實驗過程的攝像頭也未能將瀝青滴下時的情景記錄下來,最近的一滴于2000年11月滴下,但這一滴瀝青與上面的瀝青塊分離時的情景卻沒人清楚。可能再需要一個幾十年時間的觀察,才有可能弄清楚氣候、空調和振動等外部條件對瀝青滴落速度的影響。
梅因斯通認為,該實驗的價值不在于對科學的影響,而在于其對歷史和文化的影響,它激起了雕刻家、詩人和作家對時間流逝和現代生活節奏的深刻思索,并讓人們聯想到科學和事物發展的恒久性。“無論世事如何變幻無常,它自遵循著恒常不變的規律。”梅因斯通說道。漏斗中還存有大量的瀝青,未來150年里它仍將無視世事的紛擾,靜靜地準備著下一滴瀝青的滴落。如今已78歲的梅因斯通將這一實驗任務交付給了一位年輕的同事,在他離開之后將這一實驗繼續下去。
[資料來源:Nature][責任編輯:則 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