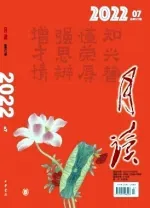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中國古代用人之道
□ 齊惠
用人,是政治的核心問題。用什么樣的人,怎樣用人,事關政權性質、吏制結構以及民心向背,是政治興衰的晴雨表,也是政權存廢的生命線。中國古代的用人思想和制度在兩千多年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智慧和經驗,毛澤東曾說“讀懂歷史,才能認清現實”,探求古代用人之道,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對今天的政治實踐不無裨益。
識人用人,公允的標準是要德才兼備。管仲就提出選人才,一定要審查三個問題:“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這三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讓品德高尚的人處低位,就是人才的浪費;讓品德低下的人處高位,會產生錯誤的用人導向;無功勞者享受厚祿,有功勞的人就得不到激勵;無才能的人任事,有才能的人就會被埋沒。
用德才兼備的人是最佳的用人狀態,但現實生活中,德才往往難以兼得。司馬光認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德與才之間是統帥與被統帥的關系,“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在危難時,必然禍亂朝政。齊桓公本是一代雄杰,在賢相管仲和鮑叔牙的輔佐下,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而至晚年則意志衰退,寵妾用奸,好色起佞。管仲病危時,桓公曾問之:“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沒有正面回答。桓公問易牙怎么樣。管仲說:“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人情莫過于愛子之情,易牙殺兒子做肉羹以取寵,這種人是靠不住的。桓公又問開方如何。管仲說:“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人情莫大于父母之情,開方以衛國公子的身份來齊國,父母過世也不回國奔喪,這人是不忠誠的。桓公再問豎刁怎么樣。管仲說:“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人情莫過于愛己之情,豎刁自閹以求寵,這種人并不是出自忠心。管仲對這三位近臣作了揭露,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不近人情,而是另有所圖,不可委以重任。權力者身邊往往聚集著各種不同心思的人,要保持清醒和警惕,人之愛憎情感必有度,對那些能超出人之常情巴結奉迎你的人要倍加小心,這些人往往心懷叵測,“預先取之,必先予之”,給你的越多,從你那索取的也越多,甚至更多。公元前643年,桓公一病不起,易牙、豎刁遂趁機發動宮廷政變,把桓公囚于宮中,最終被餓死。易牙、豎刁秘不發喪,桓公的尸體一直在床上放了67天,無人理睬,尸蛆爬出宮門之外。“易漲易落三江水,易反易復小人心”,用人不當,禍蒙不測。
但是,也有人不這樣看。被稱為“亂世梟雄,治世賢臣”的曹操就另有一套用人標準——取人以才。曹操一生中曾經多次下令,公開向天下求賢。他針對東漢選官的積弊以無畏的膽略,把“德行”“名”“門第”等迂腐無用的選才標準一掃而光,主張“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曹操一生求才若渴,即使在其晚年,行將就木,仍然求才心切,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確指出:“韓信、陳平,負貪污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要求有司對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對曹操的選人、用人標準,魯迅曾評價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不敢說的。”曹操正是按這個標準,羅致了許多出色的文臣武將,造就了當時最強大的人才陣容。陳琳原在袁紹手下任記室,寫檄文罵曹操是“閹遺丑”。曹操打敗袁紹得到了陳琳,曹操問道:“為什么罵我祖宗三代?”陳琳回答說,當時各為其主,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曹操不再追究,任命他為軍謀祭酒,掌管文書事務。曹操進攻宛城時,張繡投降,但突然又反擊曹操,大敗曹軍,曹操的親兵都尉典韋戰死,長子曹昂與侄子曹安民也死于混戰中,曹操自己也中箭受傷,這是曹操戰爭史上最慘重的一次失敗。按常理說他與張繡勢不兩立,永無和解的可能了,但官渡之戰曹操與袁紹對壘時,曹操又派人招納張繡。張繡猶豫不決,謀士賈詡說:“有大志的人能夠去掉私怨而著仁義于四海,曹操比袁紹有前途,可依靠。”張繡聽了勸告,投降了曹操。曹操與張繡握手言歡,封張繡為揚武將軍,賈詡為都亭侯,發誓不念舊惡。后來,曹操讓兒子娶了張繡的女兒,兩人結為兒女親家。
除了品德和才能外,歷史上有很多人是因為功勞而見用的——取人以功。漢武帝用人破除門第、資歷等標準,不拘一格,能建功者就重用,大刀闊斧,破格用人。被封為大司馬大將軍的衛青、霍去病都出身卑微,卻被委以重任。衛青是平陽公主家奴衛媼同小吏鄭季的私生子,從小為人放牧,過著非人的生活。其妹衛子夫是平陽公主的歌女,為武帝所幸,于是衛青有機會接觸武帝。武帝見衛青樸實、勇武,破格提拔,委以軍權;后來,又決然立衛子夫為皇后,這都是前無先例之舉。霍去病也是奴婢的私生子,武帝命他隨衛青出擊匈奴,首戰有功,18歲即被封為冠軍侯。
簡而言之,時勢造英雄,用什么樣的人往往要根據政治目的和時代背景而定。大政治家用人,往往會把人當棋子來用,進退處置之間都是為了最終的政治目的,該舍得舍,該棄得棄,成為棋子的人才往往命運不在自己手中,而再大的棋局大不過天,再強的棋手強不過時,人事與天命之間往往微妙難測,但也有規律可循。司馬光指出:“進取之時,取人以才;守成之時,取人以德。為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進取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下,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茍不明禮儀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在創業期間,用人以才為主,因為此時政治的首要目的是打下江山,建功立業,不以才則無法建立功業;在守業期,隨著社會承平日久,用人則以德為主,因為此時政治的首要目的是長治久安,安定人心,不以德則不能持久。
總的說來,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荀子·臣道》)。用忠于事業、能團結人、和老百姓親近、受讀書人信任、能戰勝各種困難的人,就能統一天下;用忠于事業、熱愛百姓、實行法治、有應付突發事變能力的人,就能使力量強大;用不忠于事業、欺騙百姓、專門結黨營私的人,就會發生危險;用不能團結、不會預防災難、不親近百姓、花言巧語、拍馬奉承、騙取上級信任的人,就會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