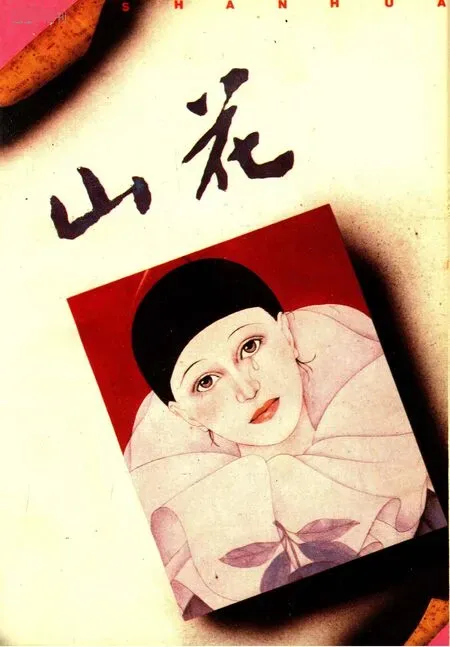文學審美與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龔霞光
問題的提出
心理健康是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在1億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數已超過1600萬。調查顯示,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的排名中居首位。”2013年2月28日,中山大學一學生因患抑郁癥跳樓自殺,當場死亡;2013年4月1日,復旦大學一名2010級在讀研究生因遭室友投毒,醫治無效而死亡;2013年4月17日,江西南昌南航大學一男扮女裝學生在寢室死亡,被發現時已經腐爛;2013年4月22日,山東建筑大學信息與技術學院一名大三男生因失戀在宿舍上吊自殺;2013年5月2日,山東大學佛山校區一名女研究生因患抑郁癥從四樓跳下;2013年5月7日,中國人民大學一名女生從學校知行樓8樓跳下,當場身亡。僅僅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我國高校就發生了如此之多的意外事件,這些都是心理疾病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的極端現象,按照輕重程度和具體誘因,心理疾病表現為多種形式:壓抑、緊張、敏感、狹隘、嫉妒、抑郁、脆弱、威脅、焦慮,等等,甚至升級為攻擊性、恐怖性、絕望性等消極情緒。產生這些心理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客觀地看待社會和自我,缺少必要的精神資源支撐,當遇到困難挫折時, 往往會出現焦慮、泄氣、絕望、頹喪、抑郁等情緒,或者離群索居,封閉自己;或者孤僻羞怯,攻擊他人,在自己和他人之間建立屏障,杜絕和社會的溝通,從而滋生自卑、多疑、戒備和敵視心理,形成狹隘的心胸和心態。
“在社會轉型期,誘發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例如生活節奏的加快導致社會普遍的心理緊張,價值觀念混亂甚至解體造成普遍的無所適從感,社會嚴重分化導致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與實際的落差增加等,種種因素造成當前我國精神疾病患者人數不斷攀升。”市場經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沖擊著人們固化的心理認知和思想意識,現代化不僅是物質財富積累和提升,也是思想和意識不斷調適。現代化物質生活的本質是便利化程度和自動化水平不斷提高,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社會從小范圍的熟人世界變成了大范圍的生人世界。在熙熙攘攘的火車站廣場和人流如潮的大型商城超市,人與人之間彼此觀望,擦肩而過,卻并不熟悉,伴隨而來的是,孤獨感加劇,心靈空間被擠占,道德底線后撤,本我遁形,空虛凸顯,情感冷漠襲擾著每一個欲望炙烤的靈魂,心理不健康因素增多,人際關系越來越淡化。哲學家葉朗說:“物質的、技術的、功利的追求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壓倒一切的統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動和精神的追求則被忽視、被冷漠、被擠壓、被驅趕。這樣發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面人,成為沒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單純的技術性的動物和功利性的動物。”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舊有的精神臍帶沒有完全割斷,新的思想體系建構尚未完成,人們在新舊交替的陣痛中迷茫,在利益至上的價值標準和集體中心的人格規范混淆中搖擺,生活中失去了自我,不能正確客觀地認識自己的價值,也不能為自己角色進行準確地定位,孤獨、封閉、焦慮、自卑、輕生、仇視、攻擊等問題不斷涌現,遂出現了海德格爾所說的“無家可歸,成為世界命運”。
文學審美:心理健康教育的藝術之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基本的價值范式,已經成為主流政治話語,但是內心世界的改變需要情感的共鳴和感情的認同,因此必須客觀認識文學在社會心理形成和個人心理矯正中的作用,以審美態度為切入點,以文學精神和文學形象為載體滋養固化的思想,建立審美的人生態度。通過文學的精神彼岸性觀照人們干涸的心靈世界,達到心理救療的目的。生活是一個多維度的綜合體系,既包括了當下的快樂、幸福與和諧,也涵蓋了伴隨而來的晦暗、低沉和悲哀,但是未來的希冀和光明需要文學的終極關懷,自我內心世界的回歸和人生意義的領悟是文學的重要使命,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關鍵是設置合理有效的載體。
心理健康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它的實現形式卻可以具體化。蘇軾的故事即是文學影響人生的典型范例,一生顛簸流離,一生名滿天下,一生的流放、入獄、貶官,經歷了挫折、痛苦、郁悶,如果沒有寬廣的精神世界、達觀的人生態度,就不能在一次次的挫折中“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流放后超然,入獄后堅韌,貶官后達觀。他汲取儒、釋、道思想的精華,兼收并蓄,并將之融會貫通,形成了獨特的審美人生態度,建構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完美鏡像。盡管在失意之后也有傷感,失落之后也有悲嘆,但在蘇軾的精神世界里,傷感和失意是生命的組成部分,而不是絕望的理由。正是由于這種澄澈的審美心境,蘇軾將憂傷和苦悶化為“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坦然,自我超越,自我突破,自我完善,把庸常的生活提升到審美的高度。中國歷代文人在挫折和低潮之后,在郁郁不得志之時,都從蘇軾這里尋求精神資源,自我砥礪,曠達淡泊。
在文學的觀照下,人可以超越現實生活的桎梏,宗白華就提出以“藝術的人生觀”“靜照”人生,以此消泯因欲望不能滿足而產生的痛苦,重視文學對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叔本華認為,人生的本質是悲劇,其根源是欲望,欲望不能滿足就痛苦。現實世界總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欲望,沒有藝術的觀照,個體在欲望中無法自拔,就必然墜入悲劇的泥沼。人生總是有各種各樣的不如意,如果僅僅以功利的態度看待人生,而不是超然地看待功名利祿,就不能提高生命的質量,拓寬生命的寬度。文學具有無功利性,能夠超脫現實的負重,營造精神的彼岸,以審美心境看待對象,超越本能欲望和功利的束縛,詩意地棲居,達觀地生活,從容地應對,朝著臻于至善至美的境界前進。
王國維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因為詩人可以在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間自由跳躍,因此個體可以在挫折時從詩人那里尋求精神資源,輕浮時入乎其內,沉重時出乎其外;輕狂時入乎其內,壓抑時出乎其外,這才是一種健康的心理態度和科學的人生范式。
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欲望炙烤的無奈和利益糾葛的愁苦,人們如果能在文學中汲取營養,建構多維的精神大廈,就可以糾偏市場經濟的必然副產品——異化,李澤厚說,“一個人在人生境界所達到的最高水準,是把一個人的社會性的東西同生理性的東西融合在心理中,這就不僅僅是道德、功利的境界”。席勒認為審美可以改造人性,構建心理健康的通道,解決社會弊端,他說:“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完全是人。”“游戲”的重要方式即以文學的虛擬性和彼岸性達成完美人生。社會文明的進步從根本上是個體潛力發揮的集合,個體的生機和活力缺失必然導致前進的內在動力喪失,文學能夠展現個性,發掘自我不為人所見的另一面,生而為貧,可以勤勞;口才平庸,可以敏銳;外表普通,可以智慧。薩特認為,人是世界的他者,存在即是惡心,他人即是地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依然是支配這個世界的基本法則,競爭就必然會有成功和失敗,也就不可避免地在物質欲望中掙扎,個體的存在遮蔽,自我迷失,個性消泯。文學是有效的救贖方式,黑格爾說,“藝術的普遍而絕對的需要是由于人是一種能思考的意識,這就是說,他由自己而且為自己造成他自己是什么,和一切是什么。自然界事物只是直接的,一次的,而人作為心靈卻復現他自己,因為他首先作為自然物而存在,其次他還為自己而存在,觀照自己,認識自己、思考自己;只有通過這種自為的存在,人才是心靈。”通過文學,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意義和價值,獲得心靈世界的安寧,建構健康的情趣、本色的生命、完美的人格。
基于文學審美的策略與建議
1.重視文學閱讀習慣的養成。閱讀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刀耕火種到神九飛天,從龜甲記事到芯片儲存,盡管閱讀的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閱讀一直是人類解放自我的基本途徑,是實現人類靈魂救贖的精神世界凈化的良方。當前的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心理健康問題的根源從之前的感情問題、學習壓力問題,逐漸轉變為就業問題、深造問題、學術競爭問題、經濟壓力問題等,心理壓力增大,抑郁和焦慮等不良情緒產生。文學作品對心理的矯正和熏陶是一個逐漸滲透的過程,需要長期積累,細微浸潤。惟其如此,習慣性閱讀方能外顯為心理健康、胸懷開闊、性格堅韌、富于同情、懂得尊重,這正是文學教育潛移默化特性的體現。
2.選擇正能量的文學作品。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帶來正能量,使人情緒飽滿,心情舒暢,積極向上;壞的文學作品可以帶來負能量,使人精神壓抑,情緒灰暗。因此,具有勵志功能的文學作品對處于成長期的大學生培養健康心理至關重要。比如,對于一個失戀期間的大學生來說,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他可能沒有注意到主人公對黑暗社會的反抗,而是看到了一個失戀者結束生命的暗示性選擇,因此處于戀愛敏感期的大學生讀《少年維特之煩惱》不如讀《簡·愛》,從中體會那種自尊、自強與自立的精神。對于抑郁的大學生來說,讀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作品,不如讀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作品。現代主義憎惡現實,視現實為地獄;后現代主義調侃現實,視現實為黑色幽默,正處于青春期的大學生容易受到這些灰暗情緒的消極影響。
3.重視文學審美的詩性價值和思想意蘊。魯迅曾經指出,“凡是愚弱的國民, 即使體格是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這句話同樣適用于高校學生的心理健康治療,文學發展的歸宿依然是對人產生終極關懷,矯正不良情緒。促進大學生人格健全發展,《浮士德》中的浮士德“生而不息,奮斗不止”的精神,《約翰·克里斯多夫》中的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等等,均對學生的心理產生積極影響。約翰·克里斯多夫雖歷經困苦,卻永不妥協。從優秀的文學作品中,學生可以感悟到人生的意義、個體的責任、生命的擔當。因此,文學作品能夠緩解心理壓力、控制不良情緒、塑造健全人格、培養良好個性,重視文學作品的詩性價值和思想意蘊,對于樹立大學生健康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www.enorth.com.cn,《我國每13個人中有1位精神疾病患者》。
[2]自新華網,《我國精神病患者超1億 1600萬重癥患者監護不力》。
[3]葉郎:《胸中之竹——走向現代之中國美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頁。
[4]王國維:《人間詞話》,上海: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2頁。
[5](德)席勒:《美育書簡》,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7頁。
[6](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