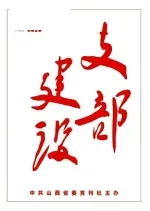大企業時代:引領中國經濟走向世界
■ 蔣 皓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從某種意義上講,新時期的國際競爭就是大企業之間的競爭。
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中國企業500強”報告,2012年中國企業500強的入圍門檻繼續大幅提高,比上年度提高了33.1億元,達到175.1億元;營業收入超過1000億元的企業達到107家,比上年度增加了27家。在群雄逐鹿的全球經濟戰場上,中國企業正勢不可擋地“群體性崛起”。
整合擴張 打造企業“巨無霸”
2012年,中國企業500強亮出了令人驚嘆的巨無霸型、戰斗型的“身材”。比如,中石化、中石油的營業收入已經突破2萬億元,其中中石油2011年營業收入達到了25519.5億元,較上年增長了29.6%;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成功收購沃爾沃汽車后,營業收入增長率已經連續兩年超過了100%。無論是國企巨頭,還是民企旗艦,一串串擲地有聲的數據向世界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已昂首步入大企業時代。
并購重組是中國步入大企業時代的必由之路。20世紀,美國經歷了五次大規模的并購浪潮,從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多元化并購、杠桿收購到跨國并購,形成了當前以美國為母國的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產業組織格局。美國通用電氣正是通過跨國并購確立了全球領先地位。在韋爾奇任CEO的近20年中,通用完成了993次兼并,市值從130億美元一路攀升到最高時的5600億美元,并連續9年保持增長率超過10%。
如今,中國大企業兼并重組的浪潮方興未艾。2012年,中國企業500強中,154家大企業共并購重組了1111家企業,并購重組活動持續活躍;鋼鐵、煤炭、建材、醫藥等行業的企業整合風生水起。中國企業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作為大企業時代的后來者,中國企業面臨的形勢又是嚴峻的。國外跨國企業在世界范圍內確立了強大的先發優勢,憑借知識、技術、原料、市場的壟斷,利用卓越的戰略與職能管理能力,咄咄逼人地在全球開展并購攻勢。
為應對這一挑戰,推行大企業戰略是后發國家的不二選擇。韓國和日本正是依靠電子、汽車等現代制造領域的大型企業集團迅速崛起的。以韓國為例,2011年,三星集團一家企業的年銷售收入就超過本國GDP的1/5。在全球競爭中,我國制造業市場大,開放時間較長而限制較少,早已經成為跨國公司覬覦的主要領域。中國企業要想立足本土、沖出國門,就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加速擴大規模,提高戰略和職能管理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更新的技術、更快的速度進行超趕。
根治“虛胖” 做精做強做優
大并不等于強。中國企業從“大而不強”走向真正的強大,依然任重道遠。
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大企業,在總資產收益率(ROA)與資本收益率(ROE)上,大都低于國際大企業的平均水平,品牌競爭力較弱,全球化水平較低。通過國際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大企業的形成機制、國際競爭力與國際其他國家的差別,而這種差別,正是中國大企業大而不強的原因。
中國有許多大企業患上了“虛胖癥”。虛胖是企業“亞健康”的表現。大企業時代,我們要鍛造的是真正筋強骨健的“金剛”型、巨無霸型企業。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王忠禹分析大企業虛胖癥產生的背景時表示:“當前,全球經濟貿易增長放緩,我國大企業長期高速成長所依賴的基本條件也正在改變,不少企業面臨較大的經營困難。”
企業“虛胖”有哪些癥狀?最突出的是,規模的擴張并沒有帶來效益的增長。2012年,中國企業500強的收入利潤率為4.7%,比上年下降1.07個百分點,低于美國企業500強2.3個百分點;資產利潤率為1.6%,比上年下降了0.32個百分點。從凈利潤看,雖然世界企業500強的凈利潤增速也明顯回落,但仍比中國企業500強快1.88個百分點。
虛胖還意味著企業免疫力低,不能有效地抵御世界經濟的寒冬。歐債危機持續發酵,世界經濟增速整體下滑,中國許多大企業也跌入了行業低谷。分析原因,由于過于依賴政府資源和政策,過于依賴大規模固定投資拉動,創新能力不足,企業管理粗放——這些都是導致中國大企業應對環境變化能力不足的原因。
如何切實有效地根治“大企業虛胖癥”?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開出了藥方:“簡單的合并、把盤子做大并不意味著核心競爭力的增強,企業要真正做強,必須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注重質量和品牌,堅持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加快轉型升級步伐。”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中國建材董事長宋志平對大企業的研究頗有心得,他結合自己做企業的實際,提出了“大企業虛胖癥”根治之道:“通過走市場化經營的道路,和民營企業融合在一起,我們共同形成中國的組團,來參與國際競爭,把自己做強做優。”
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加快做優做強的步伐,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擺在我國大企業面前的首要任務。
海外博弈 呼吁公平公正
隨著世界經濟地圖上的那抹中國紅越來越惹眼,西方的戒備與日俱增。2012年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下降到132家,日本企業也減少至68家。中國內地入圍企業數量為70家,成為世界500強企業的第二大來源地,其中,國有企業66家。這充分證明,中國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已經并且將繼續改變世界經濟的競爭格局。
中國進入大企業時代,并且在世界經濟舞臺上長袖善舞,深深地刺激了一些經濟大國的神經,尤其是引起美國政府的高度警覺。任正非在“雄赳赳,氣昂昂,跨過太平洋”海外拓疆之始,恐怕不會想到美國國會發表的一份報告,已引發全球多國對華為的猜疑。
所以,當中海油希望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的時候,美國政府拒絕的理由是:中海油作為央企是中國的國家代理人;當華為公司試圖收購美國3COM公司時,美國政府表示:華為的創始人是退伍軍人,和中國軍方“關系密切”;當和政府、軍方都不沾邊的三一重工收購4個美國風電場項目時,奧巴馬發布命令稱:出于國家安全考慮,阻止收購,并要求剝奪其所有權。顯然,所謂“國家安全”,只是一個外界難以考證的幌子,是美國政府用來打擊中國大企業的“萬能”理由,暴露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大企業的恐懼、對立與阻擊。
美國對中國海外企業的政治背景審查,觸及到中國投資者長期以來的抱怨話題:中國國有企業在西方投資時,經常遭遇不公正的歧視對待。盡管中國國有企業的高管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免,但這些公司都是獨立的商業體,根據商業原則決策,不受執政黨或政府的指令。手握重金的中國企業即將在未來數年內向海外投資數百億美元,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它們與執政黨的關系將持續受到關注。即便是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也在美國遭到是否與共產黨存在聯系的審查。
華為因“安全問題”所遭遇的傲慢與偏見,代表了中國優秀企業在國際化道路過程中最直接的問題和困難。或許,這些問題和困難不能依靠華為自己解決,而是需要中國政府來撐腰。2012年12月19日,參加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的王岐山對美國代表明確表示,中國投資者經常被美國政府審查同中國政府的政治關聯,這毫無理由。中美雙方應攻堅克難,兌現彼此的承諾。中方最關切并希望取得進展的是,美方應該公平對待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如在高技術對中國出口上解禁,對中國投資安全審查的透明、公正。
國企主導 與民企攜手共進
中國正在經受大企業時代孕育的陣痛。隨著大企業時代的到來,以大型國企為主體,不同所有制企業相互競爭、相互融合、攜手共進成為突破發展瓶頸的必由之路。
在大企業時代,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構成了國際范圍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者。大企業通過向貿易、物流、服務等領域的擴張,通過合作、外包等多種形式,帶動中小企業的加工、出口、創新和成長,是國際寡頭競爭時代的普遍模式。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工業化歷程都表明,后發國家制造業做大做強,離不開大企業集團。像我國這樣一個正在進行趕超的后發國家,大型國有企業理應成為積極的競爭者和合作者,成為聯合、帶動各種所有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火車頭。
一些人主張,國企應從營利性領域(不僅是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這是錯誤的,改革的方向不是依靠政府干預讓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更不是排斥企業規模化,而是要創造條件,讓國企與民企更加公平地競爭。國企數量減少了,但剩下的卻做大做強了,這樣的“進”理直氣壯;大批中小民營企業在嚴酷的市場篩選中消失了,這樣的“退”也是理所當然的。“雙方”都“有進有退”。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融合,國企與民企已形成了共生共贏的狀態。
大企業時代,加強國有企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有利于維護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大企業作為現代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形態,是各國制定重大政策的重要參與者,它們影響著國家內部和不同國家之間的資源配置和福利分配。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國有企業承擔了廣泛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在維護國內經濟社會穩定、緩解就業壓力、應對重大災難和金融危機、開展國際戰略合作等方面,都表現出巨大的優越性。
大企業時代要求國企與民企進一步攜手并進。通過聯合重組、控制權革命、股權多元化和招聘市場化等措施,國企的產權結構、管理方式、經營績效已發生實質性變革。許多國企已經或正在實現國企控股的社會所有制,管理的現代化程度總體上遠遠超過家族化經營的民企。中國國企的改革實踐以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理念,比分股到民、管理層收購等“私有化”的主張和“零和思維”要高明得多。
大企業時代下的中國企業仍任重道遠,需要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攜手,共同實現由大到強、由虛胖到做精做優、由海外受制于人到先發制人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