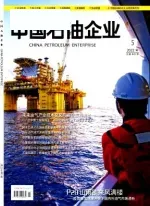依法規避用工多元化下的風險
□ 文/新疆律師協會律師 曉軍
本期案例主題涉及的議題正如案例開場白中所述,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社會關系—勞動關系,即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呈現出兼有經濟性與社會性、平等性與從屬性、沖突性與協調性的三個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按照市場化取向,開始并逐漸擴大市場化用工的規模和方式,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隨之出現了勞動合同工(有的又稱聘用工)、勞務派遣工和非全日制用工(臨時工)等各種用工方式。
這使得企業員工來源渠道復雜化。其中,派遣制員工中,一是由社會勞務中介機構招聘勞動人員(中介機構和其簽訂勞動合同),派往用工企業工作。二是多種經營企業面向市場招募員工,派往企業工作等方式。三是其他法人企業招聘員工,派往用工企業工作。國有企業在勞動用工方面的歷史遺留問題和新生問題也交織在一起不斷顯現,存在法律風險。
如何規避風險,本期案例中介紹的“T國集體勞動合同實踐”不失為可以借鑒的做法。就集體勞動合同而言,我國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是以權利爭議處理為中心的,對利益爭議的處理關注極少。“一調一裁二審”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是針對個別勞動關系和權利爭議的。《勞動法》集體合同的權利爭議和利益爭議分開處理。《勞動法》承認了權利爭議和利益爭議的不同。利益爭議是不可裁判的爭議,只能協商或行政調解處理。
由于利益爭議不涉及既存的法律法規和勞動合同的內容,缺乏司法裁判的法律依據,如出現爭議則由雙方談判來解決,由訂立集體合同的兩方—工會或工人代表和雇主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來解決。要解決利益爭議需要勞、資、政三方的共同努力。
對與在集體勞動合同中,擔當重要角色的工會組織,目前的確存在著如案例中所述的部分現象。就建立工會組織而言,國企與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相比已先行一步,然而相當部分國企的工會僅僅局限于為企業管理的有效性服務、慰問、開展問題活動的層面上,未能真正做到替職工維權。一些本來可由工會調解解決的簡單勞動爭議案件,因管理上的缺陷及人員素質達不到要求,無法得到及時處理。由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大量糾紛無法自行化解,而企業內部的工會職能弱化,行政調解的作用發揮得有限,大量勞動糾紛訴諸于勞動仲裁部門。
可以說,國有企業改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必然選擇,它對企業的經濟、政策、文化等各個領域將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在這個過程中工會組織也必然會面臨一些問題,如:職工就業方式多樣化,對協調勞動關系的要求增高、職工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使工會維權工作難度加大、企業持續重組和快速發展的新形勢與傳統的工會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不相適應等。由于企業工會無法獨立于企業,因而就會出現在勞動爭議中不能夠站在勞方利益一邊,而是傾向于做中間人、調停人的角色。
因此隨著形勢的變化,工會的改革也是勢在必行。
就勞動爭議來說,企業要在企業內部建立獨立的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不依附于企業的行政部門。其次,企業要注意內部溝通渠道的暢通,保障職工的民主參與權。比如:定期舉行職工代表大會,定期開展勞資雙方的意見交流會等。最后,企業要保障勞動者的精神生活得到滿足。可以開展一些活動或者進行一些教育培訓等。在提供勞動者的綜合素養的同時,增強勞動者的主人翁意識,以此建立穩定和諧的勞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