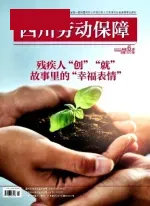觀 點
讓《勞動合同法》修訂的善意落到實處
新修訂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用工單位應當按照同工同酬原則,對被派遣勞動者與本單位同類崗位的勞動者實行相同的勞動報酬分配辦法”,同時賦予了人社部門對勞務派遣業務依法實施行政許可的權力。
由于門檻太低,一些原本不具有資質的企業進入了勞務派遣市場,不規范經營的現象比比皆是,在部分行業地區,勞務派遣卻成為主要的用工形式。用工單位青睞勞務派遣的緣由,除了壓低用工成本、規避《勞動合同法》所規定的相關法律責任之外,大量勞務派遣工的存在,可在統計上大幅拉低正式工的薪酬和待遇,勞務派遣遂成為其掩蓋隱形福利的極佳方式。
而最新《勞動合同法》,要求勞務派遣單位的注冊資本不得少于200萬元,并有與開展業務相適應的固定經營場所和設施,同時設立行政許可,顯然是為了抬高市場的準入門檻;規定“三性”崗位的具體標準,怎樣同工同酬也作了明確的規定,則是為了減小彈性操作的空間。
《勞動合同法》修訂的立法用意極佳,但有兩點不能不提:一是法律要得到嚴格的執行才會發生效用,二是需要警惕法條被規避的可能性。有媒體報道,為逃過新《勞動合同法》對勞務派遣的監管,一些企業把制作、加工等業務外包給自己管理的勞務公司,過去的“臨時工”變成了勞務公司的“正式工”,企業減少勞務派遣員工數量的同時,也沒有推高用工成本。
為了使《勞動合同法》修訂的善意不致落空,出臺《勞務派遣規定》等一些具體的配套法規應為當務之急。同時,鑒于企業成本短時期內無法壓縮的現實,以減免稅費等形式為企業減負的工作也許仍然不可或缺。
南方都市報
“探親假”,想說“愛你不容易”
7月1日,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實施,“不常回家看看”已被認定為違法,但是,基于各種原因,人們還是將“常回家看看”期冀于“探親假”。早在32年前,《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就正式頒布,規定職工可享受探望配偶、未婚職工探望父母、已婚職工探望父母等三類探親假,但在多年的實施中,卻大大失去了其原有的法律效力。
企業為求生存發展,千方百計降低勞動力成本,把壓力無形地轉嫁到職工身上。崗位是“一個蘿卜一個坑”,一個員工休息,就無人接替他的工作;每人每月皆有固定任務量,任務又與工資直接掛鉤,如果休假,勢必影響任務的完成,于是,雖有探親假也只有“主動”放棄。
國家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是為保證職工的合法權益,彰顯社會的公平和道義,力爭構建社會真正意義上的“和諧”,其出發點可圈可點。但這些剛性的法律條文,由于“沒有給出具體的懲罰措施”,導致“在操作層面上卻出現了問題”,使得“有法可依”卻難“執法必嚴”。于是,企業有了“空子可鉆”,不給職工探親假,也不會受到處罰。
其實,讓職工真正享受到“探親假”也不難。如果企業能“犧牲”點自身利益,職工不就能享受到“探親假”了嗎?如果國家能進一步細化法律處罰措施,“執法必嚴”,企業職工對享受“探親假”不就由“奢望”變為現實了嗎?
蔣延彬
“過勞死”立法該提上日程了
據報道,5月13日傍晚,奧美中國北京分公司員工李淵(化名)在辦公室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死亡,年僅24歲。前段時間他就有些不舒服,但還在連續加班,甚至在他死后很久,他的工作QQ還掛在線上。15日,搜狐公司17173網站一位年輕員工,也因為病毒性心肌炎意外死亡。
年輕白領的突然死亡,網上很多人將其歸因為“過勞死”。但我國目前勞動法規中,并沒有“過勞死”概念,員工的死亡、傷害,應由企業承擔責任的只有工傷 (包括視同工傷)和職業病兩種。
《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才能視同工傷,得到相應工傷的賠償;如果超過48小時,就不能按工傷處理。
一方面,《工傷保險條例》立法本意在于救助工作中的事故傷害,而不是員工發生的疾病,只是把“突發疾病”引發的48小時內的死亡,納入“視同工傷”的保護范圍。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現在白領的工作,往往短期壓力大,上班下班沒有明顯界限。顯然這種長時間壓力巨大的工作方式,對員工的健康造成了實質性影響,但這種“過勞”狀態,卻沒有像職業病那樣納入勞動保障的范疇。
所以,有學者建議修訂《工傷保險條例》,將“過勞死”作為“視同工傷”的一種情況,具體標準上,可以考察勞動者在生前最后6個月內,每月加班是否超過80小時,以此作為判斷“過勞死”的依據。
這也可以進一步倒逼企業保障員工的休息權,也可以作為中國勞工權利“漸進式改善”的一個可靠路徑。
法律工作者 徐明軒
大學生就業藍領化
按照 《基于事業統計和人口普查的教育結構與人才供求分析》報告顯示,2010年至2020年,中國預計將新增9400萬大學畢業生,由于同期市場提供的白領崗位只有4600萬,預計有一半以上的大學畢業生將入職藍領行業。
要知道,未來可預期的趨勢是中國龐大的就業市場并不能提供足夠多的原本符合大學生口味的“白領崗位”,而相應的,在商業服務人員、工人和新型農民領域,則將新增近5000萬個就業崗位。對此,報告也指出,新增的這些藍領崗位也將彌補白領崗位的不足,成為未來大學生就業的新選擇。
中國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突然開啟了長達十多年的擴招改革,并未細致考慮同期中國經濟的結構乃至就業市場結構的走向。1997年啟動的高校產業化改革,人為地實現了中國大學生數量翻番的目標,即從2001年的114萬上升到2013年的700萬。而同期中國經濟的結構依舊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符合大學畢業生預期的就業市場的增長速度遠遠跟不上大學擴招的速度。這就使得“上大學找不到工作”成為高校擴招所制造出來的問題。但如果這部分人不上大學,而是直接工作,他們的預期將不會是“白領”,所謂就業難也就自然消失了。
伴隨著中國人口紅利拐點的到來,人工價格勢必不斷上漲,藍領并不是過去印象中辛苦低薪的職業,而可能成為一個中等收入群體。更何況,隨著更多大學生的加入,藍領的形象也將得到提升,藍領的職業道路也將更加寬闊。更是基于這一點,大學生未來就業的藍領化問題,或許并不值得大驚小怪。
鳳凰網
別用就業壓力嚇唬大學生
最近,有機構發布了今年的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宣布今年的畢業生迎來了四年中最嚴峻的就業形勢,還說大學生的期望月薪已經降到3683.6元,比上年減少了近千元。
作為文科生,不太理解大學生期望中的月薪為何不能是整數,何以能如此精確?至于說四年來的就業寒冬之類,根本不足為據。將近20年來,幾乎每年都喊大學生就業難,要是按照這樣的情況推算,根本就不存在就業的春天。
對大學生來說,就業問題可以轉化為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怎么來面對理想、怎么來面對自己的問題。期望月薪值將近4000塊,算多還是算少?那肯定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來看。是不是多于這個數字就是幸福生活,少于這個數就跌入地獄?
現時的大學,能給予學生的東西真的很少。畢業后,投入社會歷練,只是一個開始的步驟。在這點上,絕對不是“三歲看到老”。這中間會有很多變化,當然也包括薪水。可到了一定階段,薪水多寡就不再是唯一標準。而這個“一定階段”,總會到來。
拿到文憑,獲得其中一塊“敲門磚”,至于敲開了什么樣的大門,可以帶著歡喜的心態去體驗。在就業這回事上,特別鄙視那些“恐嚇”大學生的行為。這事上,我更相信自己鼓勵自己。
正因為誰也不是你人生的導師,路有千萬條,怎么選都是一個緣分。這個時候,“就業壓力”還真算不上壓力。生活就是生活,要是把人的一生總惦記著“能不能就業”的選擇題,那可真是人生苦短。其實不必要。好好與自己相處,健康相處,就業壓力就是浮云。
丙申
“不加班”何以成吸引求職者的條件
明明說的8小時工作制,卻常常被公司要求加班,有時甚至還要把工作帶回家里做。這種隱性加班的情況,估計不少上班族都遇到過。近日,在武漢的一場大型招聘會上,武漢盛源天啟科技有限公司在招聘簡章上寫著“絕對雙休、絕對不加班”的字樣,以此吸引求職者。
從理論上來講,“不加班”,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不違背勞動者意愿或不超法定限度的加班,原本應該和欠債還錢、工作發薪一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在實際中,不雙休、經常加班的現象卻是司空見慣。不過,相對來說還只是“時有發生”的欠薪,被迫的“加班”卻是常常發生。對于欠薪,還常見一些勞動者采取各種手段追討,但對于被迫的加班,卻鮮有人為此主張權利,更少有人將單位訴至法庭。
其原因,一是因為加班問題不像欠薪那樣有過硬的證據,而在主張權利時處于不利位置;二是因為就像很多被欠薪者選擇忍氣吞聲一樣,被迫加班的勞動者為了保住手頭的工作,對于公司的加班要求,也會選擇忍氣吞聲。
在這種情況下,將原本應該天經地義的事情寫在招聘簡單上,進行強調,以吸引求職者,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保護勞動者權益問題上,無論是相關的法律工作者還是政府勞動部門,給出的建議往往是“勞動者可以向工會組織或勞動仲裁機構反映”,或者“保留證據訴訟維權”。問題在于,勞動者的相對弱勢地位決定了,他們中的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在維權部門上往往不會太“積極”,所以,改變這一現狀,還有待于勞動部門和工會組織更積極、更主動。
張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