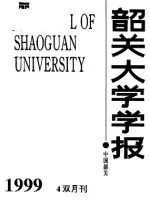“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考辨
莊東明
(1.暨南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2.韶關學院 韶州師范分院,廣東 韶關 512000)
“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考辨
莊東明1,2
(1.暨南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2.韶關學院 韶州師范分院,廣東 韶關 512000)
“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是國內學界權威、主流的提法,這個命題在邏輯上存在著迷誤。首先,馬克思沒有作出過這樣的判斷;其次,意識形態是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的特有屬性,但不全是它們的本質屬性。這個命題的迷誤可能源于蘇聯學者的迷誤和國內學者不恰當的翻譯。
文藝;本質屬性;意識形態;馬克思
“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這個命題是中國哲學、文藝學界權威、主流的提法,如“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對文學的一種基本看法”[1]、“藝術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2]等,該命題認為,按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等上層建筑的本質是意識形態(按照習慣的說法,本文將這五個對象簡稱為“文藝等對象”或“法律等對象”)。改革開放后,這個命題逐漸引起學界廣泛的爭論,以朱光潛、毛星和董學文為代表的質疑派和以錢中文、童慶炳、馮憲光為代表的捍衛派對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論爭,時至今日仍時有余波漾起。由于目前的一些權威的文藝理論教科書仍然采用這個命題,影響特別重大,所以有必要繼續對之進行廓清和討論。
一、“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的邏輯迷誤
我們認為,“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這個命題有明顯的迷誤,理由有兩個方面。
(一)馬克思沒有作出過“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的判斷
1.從最經典的闡述上看,馬克思并不認為“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
這個經典闡述如下:
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3]32
在“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者看來,這句話中,“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和“意識形態”都是“形式”的定語。因為:
法律的、政治的……(形式)=意識形態的形式所以:
法律、政治……=意識形態
這個看起來自然合理的推論可視為 “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的代表,但我們從句法和意義的角度理解這段話,則應有兩種理解。
第一種理解,馬克思認為社會革命包括兩種變革,一種是經濟基礎的變革,一種是上層建筑的變革。所以,如果要更清晰地理解這段話,或許應該做如下句法上的補足:“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變革,一種人們借以意識到……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哲學的(變革),簡言之,意識形態形式的(變革)。”我們的意思是說,“法律的……”后面應補足的是“變革”,而不是“形式”,并且“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后應補足“變革”。如果這樣的理解成立,上述的等式就應改為:
法律的、政治的……(變革)=意識形態的形式(的變革)
法律、政治……=意識形態的形式
第一種理解的結果是,在馬克思那里,法律、文藝等對象是意識形態的形式,而不是意識形態。
第二種理解。如果“法律的、政治的……(形式)=意識形態的形式”,那么“一種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的“它”(對象)是什么?是“法律的、政治的……形式”和“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然不合理,沒有“克服法律的形式”這種說法,更沒有“克服意識形態的形式”的說法。我們認為,需要克服的“沖突”應該是指“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發生(的)矛盾”[3]33,而“力求把它克服”的對象則應該是指法律、文藝等意識形式中舊的意識形態,人們應該用新的意識形態的形式替代舊的意識形態的形式。所以,第二種理解的結果同樣是:法律、文藝等對象是意識形態的形式,而不是意識形態。
2.從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來看,馬克思嚴格區分了“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形式(意識形式)”兩個概念,并認為文藝等對象是“意識形式”,而不是“意識形態”
據俞吾金、周民鋒研究,馬克思在論及意識形態的兩部最重要著作中,使用的不是同一個德文詞。馬克思在初創唯物史觀的原理時用過 “Ideologie”,而在正式闡述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理論時棄之不用,繼承了黑格爾的用語“Bewu?tseinsformen”,以及源自黑格爾和特拉西的“Ideologischen Formen”[4],但以前的翻譯和研究對此多沒有嚴謹的區分。綜合各家觀點,“意識形態(Ideologie)”是一種特定的意識,大致有以下四個互相關聯的含義:一是指各種社會思潮;二是“代表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觀念的總和”[5];三是曼海姆的“集體無意識”、普列漢諾夫的“社會心理”或“民族精神”;四是指“虛假意識”。有關例子依次分舉如下:
《德意志意識形態》;他們企圖用德國的,特別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意識形態(Ideologie),來闡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獻的思想。[6]21(社會思潮)
特別是對這個社會的上層階級諂媚奉承的人來說,就成了一個首要的任務。這在事實上就是從事意識形態(Ideologie)工作的階層(原文作“階級”,據俞吾金意見改)等等已經從屬于資本家的宣告。[7](統治階級意識)
德國唯心主義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識形態(Ideologie)沒有任何特殊的區別。后者也同樣認為觀念統治著世界……[6]16(社會心理)
……幾乎整個意識形態 (die ganzeIdeologie)不是把人類史歸結為一種歪曲的理解,就是歸結為一種完全的抽象。[8](虛假意識)
“Bewu?tseinsformen”和 “Ideologischen Formen”可分別譯為“(社會)意識形式”、“意識形態的形式”,二者的意思應該一樣,指的是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等對象,這些對象都會體現Ideologie的含義,換言之,這些對象的內核之一是Ideologie。前面“經典闡述”引文只是一個例子,類似的還有很多,如:
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 (gesellschaftlicheBewu?tseinsformen)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3]33
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Formen des Bewu?tseins),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6]41
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馬克思嚴格區分了“意識形態”和“意識形式”這兩個概念,前者指的是意識、思想觀念,后者指的是法律、文藝等對象,是前者的形式,也就是意識形態的形式。概言之,馬克思并沒有作出“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的判斷。
(二)意識形態是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的特有屬性,但不是它們的本質屬性
“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者認為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的本質是意識形態,這一論斷和不少相關立論有抵牾之處,其中的關鍵是:意識形態(Ideologie)的本質屬性是思想、觀念體系,而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的本質屬性并不全部指向思想、觀念體系。
從邏輯學的角度看,事物有多種特有屬性,但有一個屬性代表某類(或某個)事物的本質,這種屬性是本質屬性。事物的本質屬性一定是事物的特有屬性,而事物的特有屬性不一定就是事物的本質屬性。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歷史唯物主義是考察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及其發展動力的理論,其著眼點是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會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和制約。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范疇中,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考察文藝等對象是一種特有屬性的把握。這個特有屬性是不是本質屬性,這一點應該進行嚴謹的論證。不少論者都認為,馬克思并沒有從本質屬性意義上對文藝等對象進行考察,“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馬克思不是文學理論家或美學家,他無意為文學藝術下定義,只是提出了問題。”[9]“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意識現象本身。例如社會意識的內部結構和層次等,還沒有來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并引用恩格斯晚年的話為證[10]。而我們認為,意識形態是文藝等對象的特有屬性,但不是本質屬性。
1.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思想、觀念體系
第一,權威工具書對“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判斷都指向觀念思想體系。《辭海》、《詞源》、《中國大百科全書》等的解釋都大致相同,如《辭海》對“社會意識形態”的解釋為:
亦稱“意識形態”、“觀念形態”。系統地、自覺地反映社會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的思想體系。是社會意識諸形式中構成思想上層建筑的部分,表現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形式中。
這些工具書中,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都是觀念體系。當然,意識形態存在于文藝等對象之中,那只說明后者具有意識形態屬性,是特有屬性,而這個特有屬性是不是本質屬性則有待細究。
第二,有關專著對意識形態的定義也大都指向觀念思想體系。以我們目力所及,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還是后來的研究意識形態的著作,如湯普森的《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盧卡奇的《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俞吾金的《意識形態論》、宋惠昌的《當代意識形態研究》,這些著作對“意識形態”定義的關鍵詞大都是“觀念”、“思想”和“思想體系”。《德意志意識形態》主要是對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為代表的各式各樣唯心史觀思想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在這本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專門對文藝、宗教等上層建筑進行批判,這就說明意識形態主要是一種思想體系。事實上,為了避免“意識形態”概念所帶來的理解上的混淆,毛星認為應該把書名翻譯為《德意志思想體系》,這樣才更為切中,書名和內容才有一致性[11]。
第三,“意識形態”的最初意義是觀念、理念。“意識形態”的法文為 idélogie,英文為 ideology,德文為Ideologie,這些詞均源于希臘文Ide,意為觀念、概念、理念、思想;Ologie 是“學”、“學科”、“思想體系”之意,所以,ideology本應譯為“觀念學”、“觀念(思想)體系”[11],而不是文藝等上層建筑。
2.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的本質屬性并不全部指向觀念思想體系
第一,國內學界一般把文藝等對象的本質屬性指向意識形態。以《辭海》為例,首先,《辭海》直接點明“藝術”、“宗教”就是意識形態,認為“宗教”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而“藝術”是“審美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其次,對于“法律”、“政治”和“哲學”的解釋也強調了其意識形態性。其中,對于“哲學”和“政治”,沒有直接說明其意識形態本質,但認為“在階級社會里,哲學具有階級性”、“階級斗爭,處理階級關系成為政治的重要內容”;對于“法律”,有關解釋沒有涉及“本質”層面,但有“法律觀點”、“法律觀念”和“法律意識”等詞條,均強調“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法律觀點”(或類似話語)。并且,其他的論著和教科書大多直接點明法律的意識形態性,如“作為一種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的法律”[12]21。
我們認為,如果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那么就意味著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的本質都是一種思想觀念體系,這種表述并不能闡明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文藝之所以是文藝的質的規定性,因而容易引起人們的質疑 (阿爾都塞認為這幾個對象并不是一類事物,而有明顯的區別:“倫理學、公民教育、哲學”是“純粹狀態的意識形態”,而“法語、算術、自然史、科學、文學”是“經過主導意識形態包裝的‘知識’”[13]。可以看出,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和馬克思保持了一致性)。另外,令人疑惑的是,國內學界在很多場合使用“意識形態”時并不涉及其是文藝等對象的本質含義,而是僅僅當作“思想觀念體系”來使用,如“近代中國第一場意識形態戰爭”,這句話中的意識形態戰爭當然不是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的斗爭,而是思想觀念的戰爭,當然也包括一些文藝等對象的斗爭。“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者或許應該對這些用法進行詳盡的辨析,以釋疑惑。
第二,國外學界大多沒有把文藝等對象的本質屬性指向意識形態。以《不列顛百科全書》為例,該書對文藝等幾個詞條的解釋均沒有指向、甚至沒有提到意識形態,如“法律”詞條:由一個社會公認為具有約束力的該社會的習俗、慣例和行為法規組成的學科和專業。“文學”詞條:用文字記錄下的作品的總稱。常指憑作者的想像寫成的詩和散文……。“藝術”詞條:用技巧和想象創造可與他人共享的審美對象、環境或經驗。
從邏輯上看,對文藝等對象的認識應該有較大程度的全人類性,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對同一對象的同一屬性應該會形成大致相同的認識。我們在立論時或許應該和其他智者進行充分的對話,這樣才能使自己觀點的根基更加牢靠。以我們目力所及,幾本主流的文藝理論教科書在論述文藝本質是意識形態這個問題上,大都傾向于獨自深入、獨自立論,較少充分引用、論述各方權威、代表性的觀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二、“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迷誤原因
1.蘇聯學者的錯誤
問題出現在哪里?為什么會出現“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對文學的一種基本看法”、“社會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上層建筑”這些提法?根據毛星的研究,問題出在蘇聯人身上。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德語原文中,“意識形態”的本詞是“Ideologie”,“意識形態的形式(意識形式)”是“Bewu?tseinsformen”,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從俄文翻譯出版的米定·易希金柯主編的《辯證法唯物論辭典》、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都只有“Ideologie”的條目,而沒有“Bewu?tseinsformen”條目,如此重要的條目居然沒有收錄,我們只能猜測是蘇聯人誤以為兩者是同一個意思,所以二者擇其一。在米定主編的辭典中,對“藝術”條目的解釋是:“社會意識形式之一……藝術也像任何思想體系一樣……”。這說明,他們把“(社會)意識形式”和“思想體系”混為一談了,也就是把“Bewu?tseinsformen”和“Ideologie”混為一談了。據董學文的研究,蘇聯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編撰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的資料集的“出版者的話”中,明明講到“藝術作為社會意識形式”,可是,到了書的開篇目錄,卻又以“藝術是社會意識形態”作為第一部分的標題,而所列舉的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學的十一條言論,沒有一條可以表明應把“文藝”界定為“社會意識形態”。這本書于1962年由曹葆華譯成中文出版,對中國學者影響很大[14]。
2.“意識形態”的不合理翻譯的暗示
從一般的意義上看,意識形態指的是思想、觀念,是內在、內核性的范疇,但中文的“形態”一詞的意思的“形狀神態”、“表現形式”,多指事物的外貌外觀,是外在、表面的范疇,所以把“ideology”翻譯為“意識形態”是不合理的。胡為雄教授認為應該把這個主要源于郭沫若的誤譯改正過來,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時把“Die deutsche Ideologie”翻譯為《德意志意識形態》(節譯本),并于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1960年中央編譯局編輯該書新譯本時,本著“約定俗成”的原則,對該譯法未作改動,從優化漢語、保持漢語文化的優良性來說,應對此予以糾正[15]。可以作出推測的是,由于“意識形態”中的“形態”和文學等對象都有形式、外觀的特點,所以“意識形態”這個譯法給了國人一些持續的暗示,從而把“意識形態”和文學等對象等同起來。這恐怕是“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的一個潛意識的原因。
:
[1]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5.
[2]王宏建.藝術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23.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周民鋒.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兩個來源及其兩重含義[J].學術研究,2008(6):36-41.
[5]俞吾金.意識形態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9.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9.
[9]許嬌娜.審美意識形態:走出文學本質論——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爭的反思[J].文藝爭鳴,2008(3):80-88.
[10]曲洪志.論普列漢諾夫的社會心理學說及其作用[J].煙臺師范學院學報,2005(3):91-95.
[11]毛星.意識形態[J].文學評論,1986(5):88-93.
[12]胡世國.法律學基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13][斯]斯拉沃熱·齊澤克,等.圖繪意識形態[M].方杰,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155.
[14]董學文.怎樣看待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兼評“審美意識形態”說[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06(3):1-6.
[15]朱輝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理論亮點與難點——中央黨校哲學部第十四屆奇思論壇綜述[EB/OL],http://zhexue.ccps.gov.cn/PhyResearch/PhyForum/1745.html.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Proposition of“The Literature and Art Essence Ideology”
ZHUANG Dong-ming
(Teacher’s College,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0,Guangdong,China)
The proposi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s essence are ideology” is an authoritative and mainstream opinion in China academic circle.This opinion has some logic fallacy.Fist,Karl Marx had not made this judgment;second,ideology is the specific property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but not the essential property.This logic fallacy maybe came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inappropriate translations.
literature and art;essential properties;ideology;Karl Marx
I207
1007-5348(2013)03-0028-05
2012-12-11
莊東明(1971-),男,廣東雷州人,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生,韶關學院韶州師范分院高級講師,主要從事文藝美學研究。
(責任編輯:王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