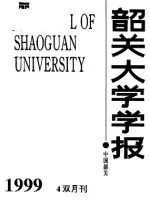人與文化的悖論——重讀經典《故鄉》
季 玢,魯 娟
(常熟理工學院 人文學院,江蘇 常熟 215500)
人與文化的悖論
——重讀經典《故鄉》
季 玢,魯 娟
(常熟理工學院 人文學院,江蘇 常熟 215500)
《故鄉》洋溢著濃郁的文化詩性意味。“我”與故鄉、閏土、楊二嫂三重關系的背后,隱含著“情感的失重”這一潛在的情感現象,這既是由于中年閏土、楊二嫂對中國傳統人倫道德的依附,也說明了在特定文化氛圍下知識分子身份的不確定性和有限性。小說借此深刻地反思了個體存在的孤獨與絕望,探討“人與文化的悖論”這一根本命題。
《故鄉》;情感的失重;人與文化的悖論
1921年5 月,小說《故鄉》在《新青年》發表,其后被收入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并引起極大反響,從此《故鄉》頻頻出現在各種文學選本和教材中。詩人朱湘評它為“《吶喊》的壓卷”[1],日本作家龜田勝一郎譽其為“東方產生的最美的抒情詩”[2]。所謂情深才更能入理,我們研習此文,以《故鄉》中人與文化的相互作用下所隱含的情感的失重這一潛在的情感現象為話語場,在“選擇”與“失去”的悖論中探究其精神世界,挖掘其文化意味。
一、情的失重:“我”、故鄉、閏土、楊二嫂
社會是一種組織結構,人類對天性中情感的自由與平等的不斷追求與實現是推動這種結構進步的巨大源動力。追本溯源,親情、友情和愛情起初都是一種美好的平衡,自由與平等是兩端相等的砝碼。《故鄉》一文中所表達的鄉情和友情似乎都失去了這種平衡,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作家魯迅創作中“多疑”的思維特點。錢理群認為,魯迅氣質和精神真髓就是“自我辯駁性質”,“他總是同時觀照、構想兩個(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觀念、命題或形象,不斷地進行質疑、詰難,在肯定與否定之間不斷往復,在旋進中將思考引向深入與復雜化。”[3]也正是這樣的思考,造就了《故鄉》的真實性與深刻性。
《故鄉》中,尋求理想中的精神故鄉的腳印直接反映在兩個意象中:帶有神異色彩的“夏夜刺猹”圖和現實中“沒有一些活氣的荒村”。其中的核心人物分別為少年閏土、中年閏土與楊二嫂等三個人物形象。可見,“我”與故鄉的情感關系最直接體現在“我”與閏土、楊二嫂等人的復雜的情感態度交叉中。關于故鄉,作品中的第四段提到“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只不過“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可是當他的母親提起他兒時的玩伴閏土時,作者卻用了這樣一句話,“似乎看到了我美麗的故鄉了”。原來主人公的故鄉情結中竟有著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紐帶——少年閏土。
緊隨其后,作者花了大量篇幅逼真地描寫了“夏夜刺猹”圖和“雪后擒雀”圖,少年閏土的“小英雄”形象呼之欲出。其實,無論是“夏夜刺猹”圖,還是“雪后擒雀”圖,都并非主人公所親身經歷,而是由少年閏土的描述所得。可貴的是,主人公“我”的記憶卻如此完整、珍貴。可見,這些畫面已經成為一個支撐“我”精神世界的神圣圖景,當“我”面對現實的故鄉時,它們便自然地凸顯了出來,形成強烈的對比。
“一個城市的魅力其實往往就僅在于那里的幾個熟人而已”,這樣的熟人不是高山流水的知音,不是兩肋插刀的摯友,也許只是生命情懷的一種點綴,刻進了生命里。“一個地方散布了幾個熟人,這個地方自然要在人心里真正扎下根來,占取一個空間。”[4]“熟人”,一個區別于知己、好友的代名詞。從深層次來講,少年閏土其實是“我”的一種生命情懷的點綴,是“我”心靈中美好的精神故鄉的一個象征。
《故鄉》中一共寫了兩堵墻,一堵是使“我”成為井底之蛙的有形的高墻,幸好少年閏土通過他豐富的生活經驗幫助“我”這位封建家庭的“少爺”“拆”了這堵墻。另一堵則是用古訓筑成的無形的高墻。這堵墻則是“我”與中年閏土一起筑成的,這是一堵隔斷心靈溝通的高墻,貼著人倫道德的標簽。不知從何時開始,人的身份、地位代替了人自身的存在,社會的集體意識、文明狀態對人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即是人的社會狀態和文明狀態對人的“異化”。
美好的東西固然值得回憶,但大多數時候,真正讓我們珍惜和感動的只是故事本身,不是人。我們對他人身份、地位的認同已模糊了昔日的情誼,一聲恭恭敬敬的“老爺”終于證實了“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了”。兩者對這層障壁的深層次的認可與保持才是最可悲的,而這就是人在文化面前的屈從。
如果說少年閏土是 “回憶中的故鄉”的代表人物,那么中年閏土與楊二嫂便是“現實中的故鄉”的代表人物了。進一步地說,盡管作者對中年閏土的外形作了描寫,但是有關他的個性、想法、生活等方面的描述或說明都不夠充分。相比之下,楊二嫂這一人物形象則更加生動與寫實。雖然她的表現有些讓人失望,她的出現卻使氣氛意外地晴朗起來,使“我”在“現實中的故鄉”與“回憶中的故鄉”的對比沖突之間找到某種平衡,引領“我”走進“現實中的故鄉”。
在分析“故鄉”這一意象時,中西達治認為,“我”之所以二十余年未曾回鄉探親的原因應歸結為對楊二嫂這等人物的嫌惡[5]。最后寫到不能讓后輩“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恣睢即任性放縱的意思,而這里的“別人”意指非常廣泛,楊二嫂大概可算是其中一種類型——潑悍、貧困而又貪圖小利的市井婦人。可見,作為進步知識分子的“我”對楊二嫂這等人物是持否定態度的。但值得深思的是,“我”在這樣一位市井婦人面前感到的是失語與隔絕——“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地站著”。“我”并不能真正走進民眾的世界,以楊二嫂為代表的民間社會有著其自身的自足性與自為性[6],作為一名闖入傳統鄉村模式的現代知識分子,即使有著一定的鄉村背景,也無法改變被抗拒、疏離的現實。同時由于“我”不闊的現實——“須將家里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加上精神上的漂泊無依,潛意識中的精神優越感帶來的是感到被楊二嫂這等人物歧視、掠奪的無奈感。更加可怕的是,楊二嫂代表的是一個巨大的群體,甚至有我們自身的影子。她“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系裙,張著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里細角伶仃的圓規”,我們在露出鄙夷的表情的同時不禁自問:我們自己在張揚、刻薄、得意之時不竟然也是這樣站立的嗎?
二、情的掙扎:“選擇”與“失去”
站在一個人的孩童時代看未來,我們會有很多繽紛的設想,他們延伸進不同的方向。而站在一個人的末端往回看,我們看到的卻只是一條線,那是真正的生命軌跡。抉擇太多,失去的只是更多。每一次的“選擇”都意味著又一次的“失去”,兩者相呼應。這些選擇與失去中,有些是歷史性的,有些是個人性的,它們都是在人與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誠如當代某位學者所言:“馬克思在寫 《德意志意識形態》時,堅持認為全社會不自覺地接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誤以為是普世性的自然真理。”[7]因此絕大多數人在對特定文化的接受與融洽過程中,選擇從屬于社會,從而逐漸喪失自我,“由一個虛偽的自我,取代真實的自我,與此同時也自動地與他人實現了同一化。”[8]聯系《故鄉》一文,魯迅正是發現了鄉村民間文化與傳統封建文化的“內在同構性”[9],從而造就了作品深刻的思想性。中國的農村保留著最完整的封建宗法體制,他們信奉“天人合一”,在肉體遭受痛苦時,精神也淪陷于人倫道德思想之中,失去了自我對生命的真實體認。面對生活,他們選擇一味地忍受與忍讓,相信這一切都由陰間的鬼神或外在的既成秩序掌控。因此中年閏土一方面要了香爐和燭臺來典藏他的希望,另一方面又小心地維護著封建禮法體制,謙恭地稱呼“我”為老爺。茅盾在《評四五月的創作》一文中指出:“豆腐西施”對“迅哥兒”的態度,似乎與閏土一定要稱“老爺”的態度相差很遠;而實則同有那一樣的階級觀念在腦子里[10]。可以說,故鄉不再僅僅是局限于“我”的故鄉,它表現的是一個完整的鄉土中國的概況。中年閏土、楊二嫂也不是具體的個像,而是兩個具有群像特征的人物,“麻木”、“恣睢”是鄉村文化的文化特質。
《故鄉》發表于1921年5月,正是先進的現代知識分子進行痛苦的精神轉型時期。他們感到與現實環境是一種“在”而“不屬于”的關系,內心充盈著無比深重的孤獨感、漂泊感和懸浮感,在創作中這種人生圖式便自然地被凸現出來[11],《故鄉》無疑是漂泊者孤獨之旅的精神文本。小說用“辛苦輾轉”來形容“我”的生活。然而真正的痛苦并非在于形式,而是隱含在背后的精神的失落與孤獨。更不可改變的是“我”“知道我在走我的路”,這是“我”在與文化的磨合中主動選擇與必然失去的。當乘船離去時,“我”感覺“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遠離了我”。一方面,從空間來說,“我”坐在船上,以船為靜止物,船在前行,山水便是倒退著,離“我”就愈來愈遠了。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卻是一份“逆流而上”的情懷,是“我”的選擇——“我”拒絕了故鄉。作為封建農村,故鄉深入骨髓的愚昧、守舊、落后、殘缺帶給“我”的不只是悲嘆與同情,更是靈魂深處對它的解構與摒棄。也正是這份勇敢的解構帶來了“我”的痛苦與孤獨,帶來了情感上的失重與信仰的失衡。
在《野草·希望》中,魯迅先生反復地重復這樣一句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而在《故鄉》中,作者對于后輩們提出了這樣的希望——“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但作者隨即又對此加以否定,將“我”的“希望”與閏土的偶像相提并論,因而感到這種“希望”的“茫遠”。這種悲涼的心境緣于魯迅深刻的歷史理性。魯迅有著極其強烈的“歷史中間物”意識,認為“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12],這意味著人類的歷史是無止盡的,個人的存在不可能有一個完滿的結局,終要留下瑕疵,所以這“希望”對于“我”來說不可能感到很切近實際,因此才發出這樣的感嘆:“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盡管作者依然相信要為下一代開辟新路,但是與其說這是一種信念,還不如說這是一種類似《藥》中的花環那樣的祈愿了吧。
許叔重《說文解字》謂“同志為友”,就大體說,交友的原則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即要求“友必同心”,即兩者的性靈同在一個水準上[13]。而《故鄉》中,面對已被生活折磨得“像一個木偶人”的閏土,“我”更早地認識到了兩者在性靈上的差距。這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與判斷,自然也是知識分子內心的優越感在作祟。但很快這份優越感便被楊二嫂的能說會道打破了。細細品味“我”與楊二嫂的對話便可以發現,一面是她的咄咄逼人、冷嘲熱諷,一面則是“我”的步步后撤,從“愕然”到“愈加愕然”到“惶恐”再到“無話可說”,只能說,“我”是真正的失去了故鄉了,再也不能體會鄉土中國的精神傳統以及閏土、楊二嫂這些“鄉人”的生存智慧了。從《故鄉》出發,魯迅在深入到鄉土中國最為幽暗之處的同時,也昭示了現代知識分子的自身的局限。
三、哲理的漩渦:人與文化的悖論
學者解志熙在其著作《生的執著》一書中指出:“魯迅的思考大體上是面對兩個方向展開的。一個是關于群體存在的問題,……,另一個是關于‘孤獨個體’的存在問題”,“沿著上述兩個思想方向,存在著兩個魯迅,這兩個魯迅雖然同為一身,但卻始終矛盾著,這兩條思路雖然有交叉但又并未完全統一。”[14]一般而言,前者指向社會問題,充分表現魯迅作為民族斗士的風姿;后者則特別富于現代哲學意味,深刻反思個體存在的孤獨與絕望,探討“人與文化的悖論”這一根本命題,《故鄉》自然屬于后者。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外來文藝思潮大量涌進,傳統文化受到了猛烈的沖擊。先進的現代知識分子由此認識到了中華民族對于人倫道德的過分推崇與依賴,它不僅造成了中國農村保留著最完整的封建宗法體制,更造成了國人在失去精神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自我獨立存在的價值。
在這樣的情形下,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像當年的魯迅先生那樣義無返顧地“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然而“獨在異鄉為異客”,當他們在極度的精神疲乏以及失落后,又對傳統文化的寧靜、優美充滿了依戀。可是,他們再也回不去了。因為在他們選擇新興文化的同時,就意味著失去了傳統文化對他們的庇護。再次回到鄉土,也只能被當作一個“文化異數”來對待。當先覺者們在思考啟蒙的限度,思考如何用現代哲學、科學來打破傳統時,他們會不自覺地站到傳統文化的審視者的高度來俯瞰蒼生,這個時候他們離故鄉、離傳統就更遠了。他們那份渴望獲得安寧、獲得撫慰的心只能更加沉重,更加漂泊無依。
在精神上收獲,在情感上遺失,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先覺者們必然要付出的代價,而這也正說明了他們的承擔。
由少年閏土的描繪加上“我”的想像加工出來的“故鄉”是美好的,深藍的天空、圓圓的月亮、海邊的貝殼……,這些畫面已經成為一個支撐“我”精神世界的心靈港灣。但回憶中的故鄉再也回不去了,以致于沉浸其中的“我”面對以中年閏土、楊二嫂為代表的現實的故鄉時就顯得手足無措。“我是誰?”“該如何尋找真正的自我?”此時的“我”被歷史和現實懸置了,他開始思考自己真正的身份。很顯然,他不再是昔日封建家庭的少爺,而是一個長年在異鄉辛苦謀生的漂泊者,因此并未發達,也就失去了 “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心理優勢。尤其重要的是“我”已然獲得了與“故鄉”的文化質素迥然不同、甚至是對峙的現代啟蒙文化,在“我”的眼中,“故鄉”是一個亟待被啟蒙、被改造的文化符號。現實的故鄉的一切仍然存在著,但于“我”已毫無意義,它已變為一個不可捉摸的荒誕的存在,不僅打破了“我”心目中的美好,而且使 “我”對自身的存在產生了一種根本性的焦慮——人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依據、目的和意義,不知自己是誰,從何處來,到何處去。人,無法回歸到從前,尤其是無法回到從前的美好,這是人的悲劇,也是人逃脫不了的命運。這個荒誕的存在即魯迅后來所捕捉的 “無地”(《影的告別》),“無物之陣”(《這樣的戰士》),它揭示了絕大多數現代人的“身份危機”。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干水,卻望并州是故鄉。”當“我”發現現實的故鄉從根本上說是一個荒誕、虛無、不可理解的世界時,“我”與閏土、楊二嫂之間也陷入了失語的障礙中。一方面是閏土、楊二嫂以維護傳統宗法倫理道德的視角將“我”對象化了,另一方面是“我”秉持著西方現代文明的“他者”的目光將故鄉與閏土、楊二嫂等人對象化,結果“我”愈是想使自己行動起來,就愈是發現自己的行動無意義。“我”成為了一個絕對孤獨的個人。“他人即地獄”,正是社會、文化對人的異化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隔絕、封閉。
人生是無止境的選擇和行動的過程。人的存在價值就在于他自己所設想的那種價值,人的本質是由主體自行選擇與造就的。正如當年“我”義無返顧的“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如今面對虛無、荒誕的故鄉世界,面對無法溝通交流的故鄉的人們,“我”選擇了斷然拒絕,勇敢地離開。但這種抉擇只能是一種“絕望的抗爭”,因為這種抗爭無法超越現實的荒誕性存在,同時也無法使得“自我”的身份得到確定性,“兩難的抉擇”和“身份的危機”將永恒有效。但是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他有一種倔強的自由意識,從來不放棄對必然性的超越。這也正是魯迅的精神本色: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這個世界的隔壁,并不都要空間的隔離。不需要空間的隔離,仍有人被丟棄在這個世界之外。”“有一種‘墻壁’摸不著當然也敲不響,那中間灌滿的不是沙子,而是歷經千年而不見衰頹的一種:觀念,甚至習慣。”[15]中年閏土和楊二嫂對中國傳統人倫道德的依附,對“我”作為一個“文化異數”的疏離與隔絕,這一切都說明了觀念對人的性格甚至命運的影響。同樣的,“我”由于接受了先進的現代西方文化,不自覺地將自身放到了俯瞰農民的精神狀態與生活道路的審視者的高度,造成了內心的孤獨感、懸浮感,這也是文化對人的異化的一個方面。可見生活在特定文化氛圍的人們對于主流觀念或習慣的接受乃至滲透,從而不自覺地形成了對情感認識的抑制,破壞了情感的平衡。這樣的遺憾堪比希臘神話中的“斯芬克斯之謎”,他們共同揭示了人類的生存困境:“人試圖把握自己的命運,但卻無力擺脫自己的命運。”在此,我們更能深刻地體會到那個時代的先覺者們的孤獨與困惑,更加欽佩他們的擔當。
:
[1]朱湘.吶喊——桌話之六[J].文學周刊,1924(145).
[2]楊劍龍,工藤貴正.“東方產生的最美的抒情詩”——中日學者《故鄉》談[J].魯迅研究月刊,1999(1):38-41.
[3]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75.
[4]李林榮.失重的歲月[J].散文,2007(4):50-51.
[5]尾崎文昭.“故鄉”的二重性及“希望”的二重性[J].魯迅研究月刊,1990(6):22-28.
[6]何平.《故鄉》細讀[J].魯迅研究月刊,2004(9):81-85.
[7]趙毅衡.神性的證明:面對史鐵生[J].開放時代,2001(7):62-71.
[8]徐強.文化和人格[M]//人格與社會.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210.
[9]羅關德.鄉土記憶的審美視閾——20世紀文化鄉土八家[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41-59.
[10]茅盾.評四五月的創作[J].小說月報,1921(8).
[11]韓傳喜.故鄉:漂泊者的精神之歌[J].皖西學院學報,2003(3):82-83.
[12]王學謙.魯迅《故鄉》新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2):182-189.
[13]朱光潛.談交友[M]//朱光潛談人生.北京:長安出版社,2006:139.
[14]解志熙.兩難而兩可的選擇[N].光明日報,1989-01-24(4).
[15]史鐵生.葵林故事: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236.
The Antinomy of People and Culture——Re-reading the ClassicArticle Hometown
JI Bin,LU 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215500,Jiangsu,China)
Hometown is full of literacy and poetic meaning.Behind triple relations of “me”,hometown,Run Tu,and sister-in-law Yang,we can see feeling of weightlessness which implicit in the text.These are Middleaged Run Tu and sister-in-law Yang of traditional ethics and moral dependency.Also explains Intellectuals’uncertain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al.By looking back “my” mentality,the article implied deep thinking of lonely individual which behind sad and dreary feeling.It investigated th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of“the antinomy of people and culture”
hometown;feeling of weightlessness;the antinomy of people and culture
I207
1007-5348(2013)03-0033-05
2012-12-20
季玢(1972-),女,江蘇東海人,常熟理工學院人文學院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博士后,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責任編輯:王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