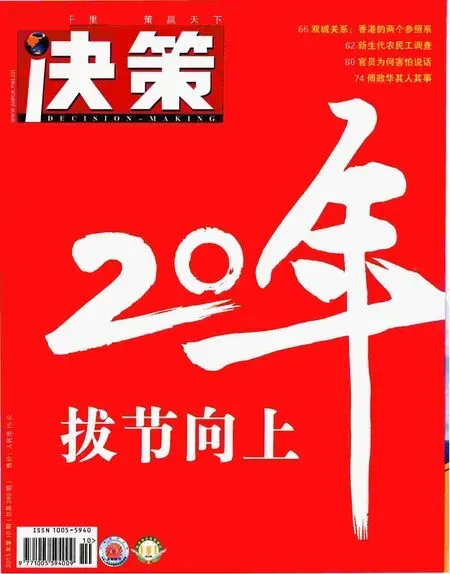溫嶺為什么能?
■本刊記者 楊 敏
9月峰街13道日一下間午會2:議30室,里浙已江經溫坐嶺滿市了橫人,橫峰街道視頻監控系統建設民主懇談會正在召開。
“才到了38個人,人數還不夠啊,”溫嶺民主懇談辦公室主任陳奕敏,提前半小時就來到橫峰街道。這位當地干部眼中的“陳懇談”,心中有把刻度精確的“尺子”,有關懇談會的任何細節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這場會,是1999年以來,溫嶺召開的近3000場民主懇談會中最普通不過的一次。舊村改造、環境治理、校網撤并、預算編制、三公經費……無論小事大事,溫嶺的老百姓都有機會發發言、放放“炮”。
14年,經歷5任書記、市長、人大主任,在中國基層創新仍然走不出人走政息怪圈的大背景下,溫嶺民主懇談的持續動力,成為值得一探究竟的話題。
在政府與社會的接口上做文章
橫峰街道懇談會現場,主席臺沒派上用場。
街道辦主任盧法友、副書記潘丹和公安局、派出所的幾位代表坐在矩形會議室的一端,27個村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銀行、幼兒園、企業等相關代表圍坐一圈。
“我們都用臺州方言開會”,細心的潘丹提出給記者找個“同聲翻譯”。
在簡單介紹視頻監控的重要性之后,街道派出所通報了近3年要安裝的440個高清攝像頭的選址方案。
會議一開始,中規中矩按照流程走。到了討論環節,會場頓時熱鬧起來。
祝家洋村支部書記提出,村里9只探頭不夠,還有一兩處地方沒有覆蓋到,而且三年建設周期太長,不如一次性完成;邱家岸村書記蔡永乾,則質疑方案中該村的11個探頭選址有問題,要求重新選址。
七八位代表,擠到會場張貼的一張視頻監控布局圖前面,仔細查看本村的探頭數量和選址地點。
大家發言越來越熱烈,從建設周期、財政補貼方式、探頭數量和選址方案,方方面面都提出了完善意見。“你看,大家都有話說,也都說到了點子上,會開得很有質量,”陳奕敏笑吟吟地說。
讓大家都有話說,就意味著議程設置必須與百姓生產、生活緊密相關。“橫峰街道企業較多,流動人口也很多,對社會治安問題,老百姓關注度高,所以才把這樣的工作拿出來懇談,”派出所所長蔡仁輝介紹說。
懇談,意味著哪怕一個小小攝像頭的安裝,百姓和政府都是可以商量的。盧法友現場承諾,會認真考慮村民關于縮短建設周期的建議,村里如對選址有異議,均可與派出所協商實地勘驗。
“會上提了很多不同意見,你們有心理準備嗎?”會后記者問。
“開這個會的目的,就是聽意見,然后再去完善工作方案”,潘丹說,“像今天這個會,如果不懇談,好事也不容易辦好,工作落實下去是罵聲而不是贊揚聲。當你聽取民意之后,哪怕這項工作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只要群眾參與了,大家就能支持、理解。”
市場經濟是培育和發展民主政治的溫床。一直關注溫嶺的學者李凡,將民主懇談議程設置稱為“找接口”。
他認為,溫嶺民營經濟很強,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自主、競爭、平等、公開、民主等符合市場經濟基本規則的新觀念,滲透和延伸到人們的政治生活領域。社會有改革的要求,倒逼政府在與社會的接口上做些文章。
“溫嶺民主懇談,就是這種接口上的改革,解決的是政府和老百姓的關系問題,這讓基層民主改革出現了對話,而不是生硬的體制內改革,”李凡說。
既然有接口,免不了就有磨合。在民主懇談這張制度的“會議桌”旁,政府曾經生澀過,面對火藥味很濃的現場,很多鄉鎮領導也冒過汗;另一方面,百姓也把懇談當成“吐槽會”,熱衷表達個人訴求。
1999年6月25日,當松門第一位村民拿起話筒倒出滿腹牢騷時,人們肯定想不到14年后,橫峰街道這場最普通不過的懇談會,能讓我們看到這樣的對話雙方:從容且充滿誠意的政府,理性又不乏熱情的公民。
民主是一場訓練,一邊是對權力的馴服,一邊是對權利的伸張。一張會議桌,讓政府和民眾在相互磨合中成長。
就在記者到達溫嶺前一天,新河鎮也剛剛召開一場披云山公園改造提升建設懇談會。
盡管在媒體人眼中,新河作為溫嶺民主懇談的標桿,是不容錯失的,但記者并無懊惱。原因在于,溫嶺已經在新河、澤國、松門、溫嶠等“盆景”之外,令基層民主蔚然成風、移步即景。
“民主懇談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停不下來了,”新河鎮宣傳委員陳瑤告訴《決策》,這不僅僅因為它已經成為政府的一種工作方式,更成為老百姓一種生活方式。

制度化推演
民主建設像個陀螺,讓它動起來,既需要自身運動的慣性,也需要外部給力。這種保障其動力不衰的力量就是制度。
制度是什么?是規矩和準則。
“14年來,溫嶺市委已經相繼發布了10個文件,去一步步規范完善民主懇談制度。”陳奕敏介紹。
這10個文件,當屬2002年和2004年最具有節點意義。
早在2002年10月,第一份市委文件就明確提出,“全市各地各部門都要把民主懇談作為重大決策的必經程序”。從此,民主懇談不僅僅從寬泛民生議題轉向決策性議題,更從幾個鄉鎮的“自選動作”成為全市鄉鎮、街道的“規定動作”。
2004年《中共溫嶺市委關于民主懇談的若干規定(試行)》,對民主懇談的議題提出、參與者產生和程序流程等進行全面規范,如此,民主懇談能夠用“一把尺子量到底”,為考核提供了依據。
有了制度就可以制度化?
2004年,恰恰是陳奕敏最感困惑的時期。決策性民主懇談施行初期,就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民主懇談是體制外的,沒有法律地位,不能成為公共決策的主體。
李凡認為,對于決策主體政府來說,對民意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因此,如何將這種體制外的創新同既有體制相結合,使群眾在關于公共事務的決策中擁有最終的發言權,成為溫嶺民主懇談進一步向前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
盡管陳奕敏一直認為,民主懇談不存在體制內、體制外的問題,但他還是在學者的幫助下,尋找一個體制內切口——人大主導下的參與式預算改革。
“激活人大”,是記者在溫嶺采訪聽到最多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的另一面則是人大代表從二線走向一線。
財政乃庶政之母,參與式預算說到底,就是老百姓幫助政府一起管好錢袋子,決定錢怎么花。有兩個人的故事,能夠說明人大代表是怎樣走向“一線”的。
陳元方,是新河鎮路邊村黨支部書記、鎮、市兩級人大代表。當記者問他,在這雙重角色中,哪個說話更有分量。陳元方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人大代表”。
據陳元方回憶,參與式預算試點之初,2005年新河鎮有5800萬財政赤字,他揣測這或許是政府決定要管好錢袋子的原因。
參與式預算的流程大致是:第一步,政府提出財政預算草案;第二步,鎮人大主席團以及新設立的人大財經小組、各代表團團長、自愿參加的公眾進行初審,吸納眾人意見后提出初審報告;第三步,在人代會上,代表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具體的預算修正議案提交大會表決,一旦表決通過,政府就必須按照議案做出修改。
陳元方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自己和其他代表聯名否決掉一個政府購車項目。
西城居委會主任吳笑菊,與陳元方一樣,也是人大代表中的活躍分子。2008年,吳笑菊聯合10名代表,第三次提出了“預算修正議案”,建議政府增加100萬元支出,用于老城區所有道路的改造。
然而在最后的無記名票決中,議案沒有通過。“我當時傷心地哭了,因為這個議案代表了全體老城區人民的利益”。
2009年,吳笑菊在政府年度財政預算中發現,社會事業支出中包括了“老城區道路改造”這一項,吳笑菊又笑了。
陳元方和吳笑菊的故事,從兩個側面說明了參與式預算的成果,對政府財政支出這塊“蛋糕”來說,三公支出“切塊”越來越小,民生投入卻越來越多。
《決策》記者瀏覽“溫嶺參與式預算網”發現,2013年溫嶺市部門、鄉鎮預算和三公經費已經全部公開。在2008年就已經消滅財政赤字的新河鎮,財政支出的盤子越來越大,但是三公支出則越來越少,2012年為245萬,2013年則縮減為161.9萬。
新河不是孤案,《決策》記者發現,16個鄉鎮街道三公經費均呈逐年遞減之勢。“2010年,參與式預算在全市推廣,這就是一個非常直觀的變化”,陳奕敏說。
李凡認為,不管是什么制度改革,一定要能帶來一些成果,這個成果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也可以是解決財政赤字。“改革不僅僅談論一個價值觀念。只有改革能帶來點東西,才能讓人有想法、有希望往前走。”
顯然,經過制度推演,溫嶺民主懇談經歷5任書記、市長,已經形成“接力棒效應”,而不是主政者靈機一動的創新。
堅持中求變
在溫嶺采訪,陳奕敏一直被記者追問,有沒有最新的亮點讓記者去看看。“去塢根,那是全新的東西”,他信心滿滿。
9月14日上午9時,塢根鎮人大主席劉永標和副主席阮風華在辦公室已等候多時。塢根鎮成為全市唯一參與式決算的試點,還有一個機緣巧合的故事。
2012年下半年,陳奕敏已經做好了參與式決算試點方案,但是放在哪個鄉鎮去試呢?他找到新河,新河很猶豫。在一次會上,他與劉永標談及此事,兩個人一拍即合。
為什么在這個時間,去推動參與式決算?
“民主懇談也好、人代會也好,我們花那么多功夫做預算,政府執行的到底怎么樣,如果僅僅只是人代會上簡單羅列一下,陳述資金情況良好,這不是一句空話嗎?”劉永標說。
“十八大報告中提到要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為此我們就在考慮怎樣把參與式預算向執行情況的監督進行延伸”,阮風華補充道。
8月20日上午,溫嶺市塢根鎮政府會議室內,50余名與會者人手一份“塢根鎮2013年上半年財政收支預算執行情況”,輪番向該鎮干部發問。
這是溫嶺市首次實行參與式決算,由市、鎮兩級人大代表和群眾代表共同對政府預算執行情況進行監督。
“‘彩化塢根’工程上半年投入7.8萬元,完成計劃1.56%,為什么這么低?”溫嶺市人大代表、坑潘村村民潘宗球指著預算表問;“村級復墾指標補助完成預算支出計劃189.48%,怎么超這么多?”……
《決策》記者手中有一份塢根鎮第二季度參與式決算表,這20頁紙,細化到每個項目支出進度。以植物防治支出為例,具體到松線蟲病防治8.8萬,上半年完成比例為1.14%。
這是一個不需要太多財會知識就能看懂的財政賬本。劉永標確實是個行家,這位從1986年就擔任鄉鎮總會計的“老財政”,對參與式決算這樣的技術活稔熟于心。
試點為什么在塢根?
“今年我們財政資金1.2個億,對試點參與式決算來說,是一個規模適中的盤子”,劉永標更愿意從客觀條件去回答如上問題。
“有了塢根的參與式決算,溫嶺改革可以說是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創新系統”,陳奕敏評價。
一項做了14年的民主懇談,《決策》記者三次報道,每次都能看到變化、看到新意。逢山開道、遇水搭橋,不斷完善改革技術。其背后,是對基層治理規律最客觀的遵從。
領導干部對政聲的追求,是任何治理結構中的客觀存在。如何正確引導這種訴求,搭建新載體,尋找新切口,在堅持中求變,搭建不斷完善的創新空間,是溫嶺協商民主“事業長青”的改革技術。
盡管陳奕敏一直強調,溫嶺協商民主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創新系統,但《決策》記者相信,參與式決算絕非溫嶺改革的最后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