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說到電影——從受眾心理看《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改編
□文/景平康,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碩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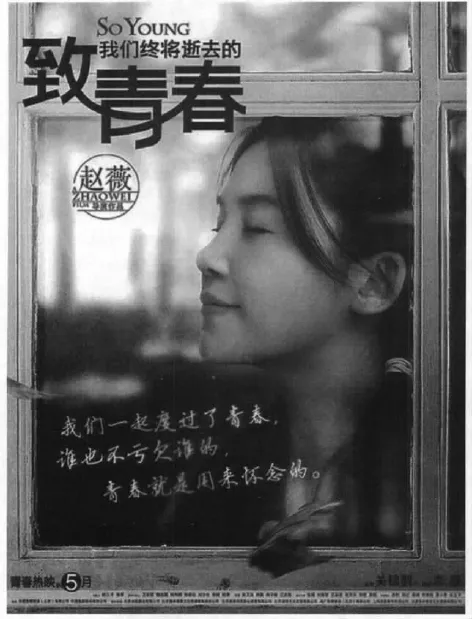
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海報
小說是文學藝術,電影則是影像藝術,不同的藝術形式決定了改編需要考慮諸多因素。巴拉茲認為:“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影片制作者在著手改編一部小說時,就會把原著僅僅當成為未經加工的素材,從自己的藝術形式的特殊角度來對這段未經加工的現實生活進行觀察……”(《電影美學》,貝拉·巴拉茲著,何力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年版,280頁)《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導演趙薇也對原小說進行了深層次的解讀,在保留原小說基礎上,做了一定的刪減和重組,改編有成功也有不足。
一、改編的成功之處
1.人物設置的變化
從受眾的認同心理看,觀眾對電影中人物形象認同程度越深,產生的情感共鳴就越強烈。尤其是青春懷舊類影片,正值青春或已經歷過青春的觀眾都能在影片中看到曾經的自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在人物性格上大部分與原小說基調一致,但也做了調整。
首先保留了小說中象征著大學中敢愛敢恨的女生形象的鄭微;執著于愛情的校花形象的阮莞;出身貧寒、一心向上的“鳳凰男”形象的陳孝正;能說會道、小人物形象的老張以及高傲形象的曾毓。朱小北由小說中“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好學生,成為一個性格直爽的假小子形象,許開陽由小說里靦腆害羞變得外向甚至有點輕狂;八卦與現實的黎維娟在電影里更加突出了她的現實和拜金。這些人物改編前性格大多屬于內斂型的,同時都是副線人物,戲份遠不足于鄭微等主線人物,所以很難出戲,而改編后的人物性格張揚活潑,甚至與小說中性格相反,這樣人物形象更有張力,出戲也容易。同時刪除了性格比較平淡的卓美和何綠芽,使副線人物變得集中而有特色,更具典型性,吸引了觀眾眼球。另外,改編使人物形象之間對比更加強烈,比如輕狂的許開陽與安分的陳孝正,正因為他們彼此性格不和,才出現了電影中許開陽毆打陳孝正這場戲,增加了矛盾沖突,讓電影更具看點。
電影中人物的命運相對于小說改編也較大。如小說里鄭微從小就將林靜當成夢寐的結婚對象和精神寄托,最終她放棄陳孝正嫁給林靜,給人感覺最后還是回到了那個從小就照顧她的男人的懷抱。而電影里她并沒有嫁給林靜,這樣安排使鄭微與林靜的那段青春如片名所寫的那樣徹底逝去了,讓觀眾看到了鄭微由當初天真可愛的女生到如今成熟穩重的女人的蛻變。許開陽和曾毓的結局也是個亮點,在大學里這兩人分別是鄭微和陳孝正的追求者,雖然他們的追求都以失敗告終,但電影最終卻安排他們兩結婚,有一種反諷的意味,更表露出兩個家庭背景相當的人,在經歷感情失敗后,都理性的選擇了婚姻,這樣的改編充滿戲劇性,使觀眾出乎意料,眼前一亮。
2.時代背景的更換
懷舊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本能,《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也是打了張“懷舊牌”。無論電影還是小說,都是講述了以鄭微和陳孝正為主線的一群大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工作的故事。從開學登記到參加社團,從生活瑣事到激情戀愛,從上課自習到畢業求職,這確實喚起了人們的回憶,似乎重溫了大學生活,但小說故事發生的年代離現在很近,沒有時間距離感,人們的懷舊點僅僅是逝去的大學生活和剛畢業的那些事。而電影將故事中大學的時代背景鎖定在90年代中期,給觀眾在心理上產生年代感,從黑白電視機、磁帶收音機、阮玲玉海報等等都可以找到那個年代的影子,不僅是對大學美好生活的懷舊,更是對一個時代的懷舊,雙重懷舊牢牢鎖住了觀眾的心。
3.故事情節的調整
小說沒有嚴格的文字容量和閱讀時間限制,而電影必須在兩小時左右的時間內完成一段完整的敘事。布德.舒爾伯格曾說:“電影沒有時間表達我所要的‘枝蔓’……電影必須按不斷上升的方式,從重要的事件走向更重要的事件。”(李麗:《<風聲>:從小說到電影》,載《電影評介》2010年7期)這就要求電影必須對原小說的故事情節進行修改和刪減,使其簡單明了。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故事情節調整主要表現為如下幾點:
(1)情節緊湊集中
為了使故事緊密,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對原著情節的刪除主要有三種方式:首先,刪除了一些與主題關系不密切的事件。比如刪減了人物的家庭背景介紹,還有鄭微跟隨陳孝正回家等一些無關于校園里發生的事情。還刪去了鄭微和陳孝正在宿舍里做愛的內容,畢竟那個年代還是相對保守的,電影里出現這樣的內容似乎有點露骨,有損他們莘莘學子的人物形象,不利于觀眾的審美接受。其次,對單個事件進行壓縮,也就是保留原小說中某個事件,但是刪除這個事件里的一些細節,使其簡單化。比如刪除了鄭微、陳孝正和林靜三者在建筑公司感情糾葛的細節,但他們三者之間愛情故事這條情節線并沒有被刪除,這樣安排使故事簡練集中的同時也點到了核心內容。最后,大幅縮減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過渡情節,以不至于故事過于拖沓,使觀眾產生疲勞感。例如由鄭微上古代建筑史課到她在男生宿舍初見陳孝正這兩個事件,小說中穿插了鄭微在圍棋社等一些生活瑣事,而電影中間沒有任何情節,直接用老張在宿舍看碟片作為轉場鏡頭,使兩件事銜接得緊湊自然。
(2)增強故事趣味性
當今社會充滿競爭和壓力,受眾往往會通過電影等媒介中的娛樂獲得暫時的輕松感,減輕和緩釋現實生活所帶來的心理壓力,(田莉莉:《從“使用與滿足理論”分析娛樂節目走紅原因》,載《廣西大學學報》2007年12期)所以電影中富有趣味點更容易滿足受眾的娛樂心理。與小說相比,電影里的趣味點更多。比如將許開陽向鄭微表白地點由飯館改成游船上,許開陽被拒后氣憤的跳進水里,當他剛做出游泳的動作時,觀眾認為他會游到河岸,這時他突然站了起來,發現水深不過膝蓋,然后憤怒的走出水面。再如小說里鄭微是在林靜的枕邊找到了象征著他們倆友誼的童話書,而電影里鄭微沖進宿舍時,那名舍友只穿著內衣,將放在桌上的童話書拿來遮住重要部位,鄭微伸手上去搶書,兩人搶書的畫面頗具喜感。
(3)增加懸念的設置
電影是時間的藝術,懸念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在時間上拉開距離,使注意力在這段時間內保持住,(《電視觀眾心理學》,金維一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139頁)因此設置懸念更能吸引觀眾注意力以及好奇心理。小說中寫到鄭微和陳孝正去水族館,但并沒有敘述進入水族館后發生的事情,電影將進水族館后設計成看海豚,鄭微想摸海豚,然后陳孝正去同馴獸員說了句話后,馴獸員便同意了,這段的亮點就是導演采用遠景拍攝陳孝正同馴獸員對話,鄭微和觀眾都不知道他怎樣說服馴獸員的,增加了懸念感。正因為這個懸念的存在,所以電影的結局與小說結局大有不同,小說的結局是鄭微與林靜結了婚,電影結尾是鄭微和陳孝正再次來到水族館,采用了閃回的方式道出了當年陳孝正對馴獸員說的話:“我今天想向她求婚,可是我沒錢買鉆戒,她最喜歡海豚了,能不能讓她摸一下?”電影最后定格在了當年鄭微開心的與海豚嬉戲的畫面。雖然到電影結束那刻,我們依舊沒看到鄭微和陳孝正在一起,但導演留了開放式的結局,答案完全根據觀眾心理判斷,這是電影的結局同時也仿似另一段故事的開始,給觀眾畫外想象的空間,看完后仍回味在劇情中。
二、改編的不足之處
1.個別人物形象刻畫力度不夠
雖然電影刪除了一些人物,但副線人物的瑣碎小事描述的還是過多,使得一些重要人物的描寫顯得有點單薄,在電影中體現最明顯的便是林靜。小說里林靜與鄭微和陳孝正共同組成故事的主線人物,他當初不想面對自己父親與鄭微母親的私情,毅然離開大學來到美國深造,歸來后他變得沉著冷靜,以成熟姿態回到了鄭微身邊,最終贏得了鄭微的信賴。而電影中他戲份不多,臺詞更少,儼然變成一個配角,放棄了出國留學,從他經常與施潔發生爭執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略顯浮躁,做事不夠果斷,在愛他的人和他愛的人之間猶豫不決,最終無奈的接受鄭微的離開。
雖然在大學期間,林靜沒有出現過在鄭微的生活里,但為了不讓觀眾對林靜的印象減退,就算在鄭微和陳孝正戀愛期間,小說也會通過諸如陳孝正在鄭微宿舍發現了林靜留下的童話書等細節讓林靜的形象重回讀者眼前,為后面林靜的出場做好情緒鋪墊,而電影沒有做任何描述,再加之他的戲份甚少,所以他的每次出現都顯得十分唐突,也使得林靜這條情節線變得脆弱無力。
2.部分敘事過于突兀
電影在敘事時雖然可以表現得跌宕起伏,但是這些變化都是在觀眾心理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因此故事的轉變一定是合情合理、循序漸進的,以免觀眾產生跳躍感,出現情緒斷裂的現象。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具體表現有兩點:第一,人物性格轉變缺少鋪墊。比如電影中鄭微的性格從學校的輕松活潑瞬間變成工作中的低沉穩重,工作后的第一個鏡頭就是她在訓斥一個下屬,這種性格變化跨度較大,而小說里鄭微的成熟是在上司的正確指導和復雜的工作環境中慢慢練就出來的。第二,情節的轉變缺少鋪墊。比如畢業后觀眾還在感傷鄭微失去了陳孝正,這時鄭微與林靜重逢,并打算和他結婚,觀眾的情緒剛剛適應了他倆要結婚,鄭微又突然放棄了林靜。鄭微的每次轉變都讓觀眾覺得不可思議,這都是情節上缺少了必要的鋪墊,故事看上去才很跳躍。
3.部分情節不合邏輯
電影觀眾和其他傳播受眾一樣對傳播信息具有求真心理,這種心理是基于人類的視聽經驗的,是一種追求事物發展的真理所在和尋找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心理。(《影視創作心理》,秦俊香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版,35頁)所以電影在敘事上如果不符合生活的客觀規律,不具有一定的邏輯性,也就不能真實的打動觀眾。比如電影中某些生活片段的人物對白不夠生活化,朱小北在保衛科與商戶爭吵時,在異常氣憤下突然說出“你們這是對我人權的踐踏,對我人格的強奸”,這句話更像是書面用語,所以觀眾聽起來較別扭,而《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就是想通過真實再現大學生活感動觀眾,但一些不生活化的臺詞使觀眾覺得有加工的痕跡。再如電影將小說里林靜和施潔兩者戀愛關系表現得很牽強,兩人之前素不相識,一次簡單事故施潔就徹底愛上林靜了,這讓人覺得很假。另外,從林靜給施潔不友好的喂藥等細節也看的出他并不愛施潔,既然這樣為何還要選擇跟施潔戀愛?施潔單方面愛林靜并不代表林靜一定要接受這份愛,這些有違人們正常的戀愛邏輯。類似于這樣的情節,帶給觀眾的真實感不強,無形中拉遠了與觀眾的心理距離。
結語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改編是對原著小說的一種繼承也是一種突破,它的成功之處在于對一些人物形象及人物關系的巧妙處理,對細節的把握準確到位,增加了趣味和懸念,但對部分人物的塑造不夠立體,敘事也有突兀之處。總而言之,無論是成功還是不足,小說改編成電影一定要契合受眾的觀影心理和當下社會審美心理主流,這樣才會被觀眾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