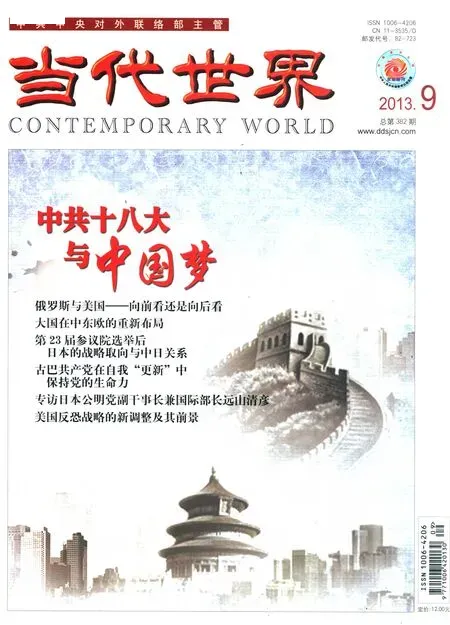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與印度國大黨的發展
■ 宋麗萍/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政黨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具體的社會體系,政治體制、政治文化、社會變遷等都是政黨發展過程中無法避開的社會現實,也是政黨自我調適,實現健康發展的推動力,這對成立已有125年歷史的印度國大黨來說更是如此。印度政治社會的變化與國大黨的沉浮息息相關。因此,將國大黨的發展置于印度政治生態下予以考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其沉浮的歷程及原因,同時也可以加深對印度民主制度、政黨政治和百年來印度社會變遷的認識。
一、國大黨所處的政治生態環境
獨立前,印度是英屬殖民地的一部分,國家獨立是印度各階層的共同奮斗目標。雖然它們的主張不盡相同,但由于有共同的外部斗爭對象,印度民眾能夠保持相對統一,不分種姓、宗教、階級都團結在國大黨旗幟之下。獨立后,國大黨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主張的多元化與公民政治意識的增強
獨立后,國大黨領導人把世俗主義和民主政治作為建國的基本原則,堅持社會公正、經濟平等經濟政策。印度政治精英成為國家政治發展的主導,這些人一般都有西方教育背景,眼界相對開闊。但20世紀60年代后,印度政治精英結構發生變化,土地改革和綠色革命中富裕起來的農民日益活躍在印度政治舞臺。這批農業精英在國內接受教育,鄉土觀念濃厚,對世俗主義和現代民主制度的認識缺乏全民族的視野,積極維護地方利益。
隨著社會集團分化的加劇,不同政治組織的頻繁建立,印度公民的政治意識也日益增強,出現了所謂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發生在1989年以后。1989—2004年是印度政治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這一階段3M成為印度政治發展的中心議題,三者代表政治集團意識對抗的三種意見,以三者為中心,環境整治、婦女等政治議題也逐漸進入政治議程之內。傳統單向度的國大黨一統或者左右分野的意識形態對抗被不同層面具體問題的對抗所取代。這也使政治發展更接近民眾,民眾參政意識日益提高。在后國大黨時代,低等種姓和低等階級、婦女、部落民參政熱情高漲,而作為印度政治發展主流和引導者的傳統精英參與政治的熱情則有所降低。
(二)社會分化加劇,矛盾沖突增多
印度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宗教、種姓、語言眾多,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面對日益緊張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各集團之間利益爭奪日益公開化,對抗也越來越激烈。在這些社會集團中,對國大黨非常重要的社會集團有表列種姓、其他落后種姓和階級、穆斯林集團,它們都是國大黨的傳統支持基礎,但在發展過程中,這些集團慢慢從國大黨的支持基礎中剝離。
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表列種姓一直是國大黨的忠實支持者。國大黨政府改善表列種姓集團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舉措都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支持。但20世紀80年代之后,針對原賤民的暴力事件不斷增加,引發其對國大黨政策的不滿,并建立賤民政黨。其他落后階級則是因為經濟地位提高,在政治上向高等種姓發起挑戰。1990年,維·普·辛格政府決定實行曼達爾報告。此令一下,隨即引發了印度社會高等種姓和低等種姓的兩極分化。正如《經濟和政治周刊》所說,“整個印度教高種姓突然變得堅如磐石,原教旨主義的和世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和甘地主義的、城市的和鄉村的高種姓,都從來沒有過那樣團結一致”。低等種姓政黨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也在逐步增強,成為一些重要邦的執政黨或者執政聯盟成員。種姓政治的發展對國大黨的打擊是致命的:其他落后階級的政黨和表列種姓政黨將低等種姓和表列種姓從國大黨的社會基礎中拉走了;印度人民黨則奪走了高等種姓對國大黨的支持。這樣,國大黨作為全民政黨的社會基礎大大萎縮了。
國大黨另一倚重的社會集團穆斯林也因為國大黨公開利用教派主義和印度政治中教派主義傾向的增強而逐步走向極端化。20世紀60年代開始,穆斯林政治組織日益活躍。80年代初,國大黨為了選舉利益,公開利用教派主義情緒,此舉引發穆斯林集團的分化,尤其是沙·巴諾案件和阿約迪亞寺廟之爭促使印度穆斯林重新思考國大黨保護者的角色。他們已不再單純依靠國大黨的力量,而是尋找可能在選舉中獲勝的全國性世俗政黨和地方性世俗政黨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保護集團利益。
以種姓和宗教為單元所造成的社會分化,瓦解了國大黨的社會基礎,同時也為邊緣集團提供了進入政治舞臺中心的機會,他們積極參與政治加劇了印度政黨政治的碎片化。
(三)地方主義思潮的發展和聯邦政治的地方化
1964年尼赫魯去世后,國大黨逐步失去了對政局的掌控,開始是邦政權,接著在聯邦政權上失守。與此相對應,地方政黨日益活躍。地方政黨的興起對國大黨社會基礎的鞏固和擴張卻起到了負面的作用,因為地方政黨的興起分割了國大黨的全民社會基礎。對國大黨而言,從獨立運動以來,它一直以印度民族代表的身份活躍在政治舞臺,反對以種姓、宗教等社會要素分割印度民族。無論在選舉政治中,還是聯合政治中,國大黨都不像其他政黨那樣公開利用地方因素和感情,通常以比較隱蔽的方式來進行。這樣的社會動員方式當然無法與地方政黨赤裸裸利用地方感情開發政治資源的競爭方式相抗衡。
1989年之后,聯邦政權進入聯合政治時代,政治競爭結構也發生改變。在1989年之前,聯邦政治始終是印度政治發展的主流,控制著印度政治發展方向。但1989年之后,邦政治成為政治選舉和政治對抗的主要領域,由于不同邦在社會結構、發展程度等方面的分殊,選舉競爭已不再是全國范圍內的競爭,而只不過是邦選舉結果的聚合,1998和1999年全國大選進一步加劇了聯邦政治地方化這一趨勢,邦政治成為決定聯邦選舉政治和政黨命運的有效競爭單元。每屆內閣總理都試圖建立新的政治操作空間以扭轉這一趨勢,維·普·辛格政府提出曼達爾報告,力圖吸引其他落后階級的支持,拉奧政府拋出經濟改革的議題,力圖以解決經濟問題為自己加分,然而因為經濟改革政策和效果的時間差而下臺。瓦杰帕伊以核試驗重振國威,提振士氣,然而最終也避免不了下臺的命運,他們都無法成為英·甘地那樣能夠操控民意的領袖。
(四)政黨政治的變化與政黨意識形態主張的模糊化
在1989年之前,除了國大黨是全民政黨外,其他政黨基本持一種意識形態而排斥其他意識形態。但20世紀90年代后,每個政黨在意識形態主張上日漸模糊,因為經濟改革的原因,目前各個政黨都在談論社會公正,多數派和經濟自由化。如印度人民黨不再反對私有化,而主張積極的私有化。印共(馬)雖然反對自由化,但在其執政的邦也執行自由化政策。賤民也不只是談論保留制,還強調種姓平等。政黨政治領域主要游戲者開始變得界限模糊,政治責任感缺失。原來的邊緣集團進入核心領域后并不要求進行社會和政治變革,一些敏感政治議題反而被束之高閣,動蕩并沒有帶來政治轉型。不同政黨所賣的都是同樣的商品,這對品牌商標的忠誠支持者是一個打擊,但在一定程度卻增加了國大黨這樣持多元主張的政黨的政治回旋余地。
(五)威權政治模式向績效模式的轉變
隨著政黨之間意識形態主張上差異的日漸模糊,民眾對政黨的評判越來越集中在績效上而不是口號或意識形態差異上,這對于在聯邦政治上競爭最為激烈的國大黨和印度人民黨而言,自然有利于國大黨。因為印度人民黨的上臺主要的依賴力量是國民志愿團,而國民志愿團是一個認同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的機構,而對于政治動員的認同度非常之低,失去國民志愿團的支持,印度人民黨的力量將會大大削弱。而對于國大黨來說,因為其多元主義的主張,并不集中特定社會集團,而可以從中漁利。
二、國大黨的應對
政黨的首要目標是奪取政權,面對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國大黨從政治戰略和自身建設上做出積極回應。
(一)在政治戰略上,國大黨依據形勢變化,調整政黨決策模式、動員模式和選舉戰略
其一,政黨決策從合意模式轉變為威權模式。在尼赫魯時期,國大黨的決策機制是多年以來形成的一致同意模式。英·甘地并不具備尼赫魯的領袖氣質,尼赫魯去世后,受到辛迪加派的控制,她采取手段切斷了這些實力派人物的權力來源,然后推行與民眾單一交流的模式,國大黨各級人員任命都由她來決定,甚至小到區一級的領導都要由國大黨中央任命。這一趨勢在其后的拉·甘地和拉奧時期都沒有發生改變,二人也同時兼任國大黨主席和國家總理。威權模式的另一個表現是國大黨領導選擇模式的家族化。1975年的桑賈伊和1980年的拉·甘地都是以火箭般的速度進入國大黨領導機構,擔任要職。現在國大黨力推的拉胡爾也是尼赫魯家族的接班人。在社會利益主張多元化的條件下,只靠個人是無法拯救一個政黨的,因此,國大黨如果要在政治上有大的發展,必須擺脫家族政治的陰影。

1986年10月2日,印度總理、國大黨主席拉吉夫·甘地和夫人索尼婭·甘地在新德里參加圣雄甘地誕辰117周年的紀念活動。索尼婭·甘地于1998年3月14日被推舉為印度國大黨主席。
其二,國大黨政治動員模式的轉變。英·甘地在操縱政黨的同時,也在選舉動員方面大展身手。1971年選舉,她高舉社會主義旗幟,提出消除貧困的口號,與此同時,她也令聯邦和邦選舉同時舉行,這樣地方的選舉也全部由國大黨中央主導。1980年英·甘地第二次執政時邁出了更危險的一步,棄世俗主義政策于不顧,公開迎合印度教民族主義者。1982年初,英·甘地在阿吉米爾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說,印度教“達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1983年,在比旺迪,她非但沒有譴責濕婆軍領導煽動暴力的行為,反而要求印度的少數派學會適應環境。國大黨的政治動員走上了另一條軌道。拉·甘地的上臺并沒有過多改變國大黨的這一政策。1986年,國大黨政府通過了《穆斯林婦女(離婚權利保護)法案》,規定離婚穆斯林婦女在沒有任何親屬和生活來源的情況下由各邦瓦克夫集團負責其生活費。這一法案實質上維護了穆斯林個人法的現狀。巴布里清真寺也是在拉·甘地執政時期開放的。
其三,選舉戰略從最初的單打獨斗到現在的選前聯盟。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6年以來印度政治和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但國大黨卻沒有根據社會的變化做出適當的調整,依然相信只靠自己的力量獨自參選即可達到半數以上的多數席位,而不采取建立選舉前聯盟的政策,后來的結果證明,國大黨并沒有得到民眾如此的青睞。當國大黨意識到單獨執政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時,不得不改變選舉策略,開始與地方政黨聯合,例如在比哈爾邦、安德拉邦、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泰米爾納杜邦。2003年年底,國大黨甚至拋棄了對中央權力分享的反對而開始致力于選前聯盟。
(二)在自身建設上,國大黨也歷經起起伏伏
其一,在組織建設方面,國大黨從最初的民主機制轉向威權體制。英·甘地取消了黨內民主機制,地方領導的選擇都由英·甘地來控制,她挑選地方領導的標準是服從自己。這樣導致一批地方實力派人物退出國大黨,另組新黨。與此同時,他們也帶走了國大黨的地方社會基礎。拉吉夫在擔任國大黨主席的時候,力圖恢復政黨內部的民主運作,宣布1986年舉行黨內選舉。但是,拉·甘地擔心黨內選舉可能出現偽造選票,不可能達到凈化黨組織的目的,而且實力派人物主導選舉,可能導致自己在黨內地位的下降。因此黨內選舉被無限期拖延,拉·甘地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也被束之高閣。1987年,國大黨在一些邦的選舉中落敗,拉吉夫遂采取權宜之計,加強國大黨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依靠青年國大黨為自己服務,但這些措施導致黨內一些宗派領導的不滿,一些國大黨成員加入到反對黨,宗派斗爭削弱了國大黨的力量。
拉奧就任國大黨主席后,因為并非來自尼赫魯家族,沒有領導魅力的光環,而且其政治基礎主要在安得拉邦,因此許多地方實力派人物均想取代拉奧。為了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拉奧沿襲了英·甘地以來的政黨建設策略。在就職后,拉奧曾宣布舉行黨內選舉,重新恢復國大黨的民主作風。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空口許諾。1991年人民院選舉后,拉奧認為國大黨中央工作委員會的某些成員勢力過于強大,不易控制,因而利用自己國大黨主席的職位,以工作委員會內部缺少婦女、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成員為借口,強迫其中的一半成員辭職,這些成員中包括來自馬哈拉施特拉的帕瓦爾和來自中央邦的阿瓊·辛格,他們都是國大黨內的實力派人物。之后,拉奧拒絕建立國大黨議會委員會和中央選舉委員會,而依靠實力較弱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和邦國大黨委員會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力,拉奧的這些措施非但不能加強國大黨內部的凝聚力,反而使黨內更多人對他非常不滿,國大黨內部的民主進程和凝聚力在繼續下滑。組織建設依舊是國大黨的一個軟肋。
其二,在意識形態建設上回歸多元主義。國大黨是全民政黨,其宗旨是為印度人民謀求福利,以和平手段建立一個以議會民主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國家里,所有人機會均等,享有同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但是在政黨發展過程中也有曲折。尼赫魯是世俗政策的創始人和堅定的支持者。但其女兒英·甘地卻以權力為導向, 20世紀80年代初公開利用教派主義情緒,損害了政黨的世俗主義主張。拉·甘地和拉奧時期試圖繼續走英·甘地的路線,但是,教派主義開發并沒有帶來實際的選舉利益,反而替印度人民黨搭橋。1998年后國大黨又重新強調堅持多元主義的政治原則,強調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在2004年選舉中,農業集團在擊敗印度人民黨聯合政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大黨在執政后,強調增加農村信貸,以緩解農民不滿,但效果有限。對一個政黨來說,最重要的是民眾的期望,尤其是現今社會,資源有限,所以生存安全是所有社會集團最優先考慮的方面,如果哪個政黨無法為民眾尋找就業機會,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那么風向會立即轉變。如今國大黨缺少的恰恰是有能力、有責任感、有活力的領導。
三、小結
政黨的存在離不開具體的社會環境。就國大黨而言,印度特有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環境鋪就了國大黨調適與發展的道路。然而,國大黨發展的歷程也反過來影響印度政治發展的方向與軌跡,而且,后者對印度政治發展的影響甚至大于前者,這反映了第三世界民主政治發展的不成熟和制度建設方面的缺陷。隨著賤民、其他低等階級、表列部落等邊緣人口成為活躍的參政力量,政治與社會兩大生態系統的良性互動,印度政治發展也將逐步走向成熟。
由于印度社會多元性和復雜性,按照語言、宗教、種姓、部落等基本單元形成的區隔使政治結盟成為重要的選戰手段,以國大黨和印度人民黨為首的選戰聯盟鼎立的局面還會存在很長一段時間。國大黨復興的路還很長,它必須在政治戰略方面作出調整,緊緊依靠家族政治是無法挽救國大黨的。
就國大黨與政治生態環境的關系而言,其必須尊重自己賴以生存的客觀社會政治系統。如果不顧客觀條件,一味以強權手段調整政黨的政治戰略,其結果必然是悲劇性的。例如,國大黨不顧印度多元社會的性質,不尊重少數集團,迎合教派主義的主張,最終導致落后種姓、表列種、穆斯林集團等傳統支持基礎的背離。
[1] 3M 即曼達爾(mandar)、寺廟(mandir)和市場(market)。
[2] 印度教有四個主要種姓,即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除上述外,在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傳統上稱他們為“阿丘得”,即不可接觸的“賤民”,有的也稱其為第五種姓,今天稱之為“哈里真”或“表列種姓”。
[3] 高鯤.印度的保留政策和種姓矛盾.南亞研究, 1992(2). 6.
[4] Prakashi Chandra, Changing Dimensions of the Communal Politics in India, Delhi, 1999: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