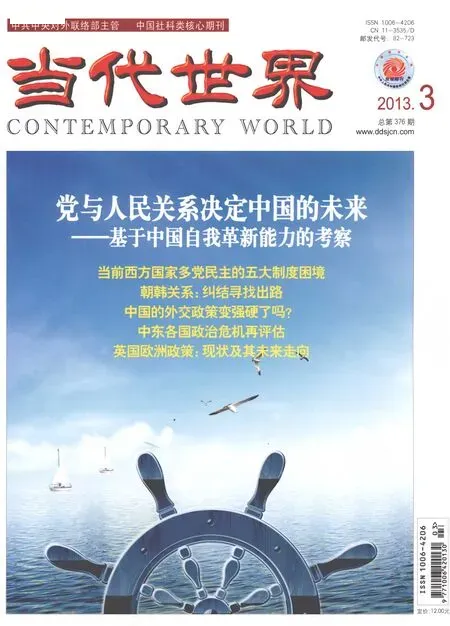金磚國家仍是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引擎
■ 徐建國/文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經(jīng)濟與發(fā)展研究部副研究員)
2013年3月26日至27日,第五次金磚國家(BRICs)領導人會晤將在南非港口城市德班舉行。此前,基于“團結(jié)、合作、共贏”的理念,已先后在俄羅斯、巴西、中國、印度舉行了四次領導人會晤。本次會晤將進一步加強金磚國家伙伴關(guān)系,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鞏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增進與非洲的互利合作。這不僅符合金磚國家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利益,也有利于整個世界經(jīng)濟的平穩(wěn)發(fā)展。
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以來,金磚國家在帶動世界經(jīng)濟復蘇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歐債危機久拖不決,美日增長不力,西方國家總體需求不振,世界經(jīng)濟下行風險猶存,金磚國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拖累。2011年下半年起,各國經(jīng)濟增速普遍放緩。有人驚呼:“沒有金磚國家,誰來拯救世界?”進入2012年后,唱衰金磚國家之聲不斷,諸如“金磚撞上了墻”、“金磚已然失色”等等。不過,從最近半年的增長軌跡和未來趨勢看,金磚國家增長普遍高于發(fā)達國家和世界平均速度,仍是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要動力。
金磚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動力不減
一、各國經(jīng)濟已呈現(xiàn)企穩(wěn)回升的勢頭
2012年,世界經(jīng)濟總體呈下行趨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全球增長率從2011年的3.8%降至2012年3.3%。金磚國家增速也普遍下滑。中國GDP增長率從2011年的9.2%降至2012年7.8%;印度從6.8%降至5.6%;南非從3.1%降至2.3%;俄羅斯從4.3%降至3.6%;巴西從2.7%降至1%。但是,除巴西外,其余各國均遠遠超過發(fā)達國家1.3%的平均值。而且,金磚國家在2012年下半年紛紛進入觸底回升軌道。中國GDP增長率從第三季度的7.4%迅速回復到第四季度7.9%;同期印度從5.3%略升至5.4%;巴西四季度估計增長達2.1%;俄羅斯和南非也從年底開始呈現(xiàn)回升跡象。IMF預測,2013年中國GDP增長率將回到8.2%,印度5.9%,俄羅斯3.7%,南非2.8%,巴西3.5%,除南非外,均高于世界平均3.5%的增速,并且都遠高于發(fā)達國家1.4%的平均速度。
二、后危機時期,金磚國家引領世界經(jīng)濟增長
IMF稱,金融危機發(fā)生以來,世界經(jīng)濟增長的70%靠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金磚國家占半壁江山。發(fā)達國家平均公共債務與GDP比重從2007年的77%上升到2010年104%,202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126%,經(jīng)濟增長將長期受到困擾。相反,2014年至2017年,巴西、南非將保持4.1%左右的增長率,俄羅斯3.9%左右,印度在6.4%至7.0%間,中國8.5%,均高于發(fā)達國家2.2-2.5%的平均增速。
值得一提的是,金磚國家快速增長不僅帶動了全球復蘇,還通過南南合作帶來其他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共同發(fā)展。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金磚國家的迅速復蘇使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提高0.3到1.1個百分點。來自金磚國家的投資正推動非洲基礎設施改善和制造業(yè)發(fā)展,促進非洲經(jīng)濟平穩(wěn)增長。IMF估計,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2012年經(jīng)濟增速達4.8%,未來幾年將保持在5.7-5.8%。
三、從遠景看,金磚國家仍是世界經(jīng)濟的火車頭
20世紀,美國、西歐、日本等西方大國和地區(qū)長期是世界經(jīng)濟的火車頭。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特別是金磚國家等新興大國在全球經(jīng)濟中的地位顯著提高。按購買力平價(PPP)估算,1989年冷戰(zhàn)結(jié)束時,金磚國家五國GDP總和占世界的比重還不到8%,2000年達16%,2010年25%。早在2003年,高盛公司就預言,到2050年,世界經(jīng)濟格局將重新洗牌,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將先后超越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與美國、日本一起躋身全球六大經(jīng)濟體。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而成為第二大經(jīng)濟體,巴西超過意大利,印度超過加拿大,均快于大多數(shù)機構(gòu)預期。經(jīng)濟重心向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轉(zhuǎn)移已成為21世紀的長期態(tài)勢。世界銀行指出,2000年至2008年,金磚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達55%,未來將提高到60%,意味著世界經(jīng)濟增長的近三分之二要依靠金磚國家。經(jīng)合組織(OECD)則預測,2060年前,金磚國家等新興大國增長將始終快于發(fā)達國家。
發(fā)展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
一、金磚國家長期快速增長的兩大基礎
與西方大國相比,金磚國家充當世界經(jīng)濟火車頭,有兩個特有的現(xiàn)實基礎:
一是龐大的內(nèi)部市場。2010年,金磚國家人口總和約29.4億,占世界總?cè)丝诘?3%。隨著經(jīng)濟持續(xù)強勁增長,人民群眾的購買力日益壯大,帶來旺盛的消費需求和國際貿(mào)易。2001年到2010年,金磚國家之間貿(mào)易量年均增長28%。2011年內(nèi)部貿(mào)易總額達3200多億美元,2015年將達5000億美元。IMF稱,后危機時期,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的內(nèi)需增長量將占全球需求增長的一半以上,進口增長量將占全球貿(mào)易增長量的40%。有人估計,2010年中國、印度中產(chǎn)階級分別約1.7億和60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2.5%和5%,合計占世界中產(chǎn)階級的不到10%;到2025年,兩國合計將占全球中產(chǎn)階級的45%,為世界經(jīng)濟提供空前的市場潛力。
二是金磚國家總體上還處于工業(yè)化與城市化進程的中期,產(chǎn)業(yè)發(fā)展、基礎設施開發(fā)、教育和科技創(chuàng)新、社會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等各領域都有巨大的發(fā)展空間。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和生活性服務業(yè)是中國未來發(fā)展的重點。印度“十二·五”規(guī)劃提出重點發(fā)展制造業(yè),以解決每年上千萬新增勞動力的就業(yè)問題,并將在未來五年內(nèi)對基礎設施投資1萬億美元。巴西、俄羅斯、南非也都提出了重振制造業(yè)的思路。目前,中國和印度的城市化率分別在50%和35%左右,還有大量的農(nóng)村勞動力需要向工業(yè)和服務業(yè)轉(zhuǎn)移。如果中國外出打工的2億多農(nóng)民工都能在城鎮(zhèn)定居,其工作和生活需求將帶來巨大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jié)摿ΑRICs一詞的創(chuàng)造人奧尼爾最近也表示,金磚國家長期高速增長的“最大發(fā)動機就是城市化”。
上述兩個特點使金磚國家的火車頭作用更加具有長期性和可持續(xù)性。

二、面臨內(nèi)外兩重挑戰(zhàn)
一是經(jīng)濟增長的外部環(huán)境惡化。首先,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fā)達國家“去杠桿化”和“再工業(yè)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貿(mào)易保護主義抬頭、游資四處投機,影響到金磚國家貿(mào)易環(huán)境、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通脹壓力和經(jīng)濟增長的穩(wěn)定性。特別是資本流動的態(tài)勢正在發(fā)生改變。流入包括金磚國家在內(nèi)的新興經(jīng)濟體的私人資本,從2011年的9100億美元下降至2012年約7460億美元,下跌18%。俄羅斯2011年資本凈流出就達842億美元;2012年前9個月,資本凈流出約579億美元,全年估計達670億美元。印度2012年上半年總體上亦呈資本凈流出態(tài)勢。
其次,美國提出的“再平衡”可能導致全球總需求增速放慢,制約金磚國家出口增長。美國希望通過“再平衡”控制無節(jié)制的個人消費,增加國民儲蓄。據(jù)估算,美國私人儲蓄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私人消費將減少大約1000億美元。全球總需求、尤其是美國需求的減速對金磚國家經(jīng)濟增長產(chǎn)生了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美國提出“再平衡”,還要求順差國增加消費,減少儲蓄。金磚國家大多對美國存在順差,面臨美國各種貿(mào)易保護主義措施。
與此同時,發(fā)達國家為加快經(jīng)濟復蘇和維持增長,先后推出多輪“量化寬松”政策,不僅政府開支和債務有增無減,而且向國際市場釋放大量儲備貨幣。量化寬松的根本目的是利用“金融抑制”機制,引起世界性通貨膨脹,進而通過負實際利率稀釋政府債務。結(jié)果,既影響到金磚國家外匯資產(chǎn)的保值,又加重各國通貨膨脹壓力,沖擊到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性。
二是急需轉(zhuǎn)變增長和發(fā)展方式。金磚國家在各自的發(fā)展進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增長方式,中、印、俄、巴、南分別享有“世界工廠”、“世界辦公室”、“世界加油站”、“世界原材料基地”、“黃金之國”的稱號。在發(fā)達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中,形成了中國出口制造業(yè)產(chǎn)品、印度出口IT服務和制造業(yè)產(chǎn)品、俄羅斯和南非出口資源型產(chǎn)品及大宗商品、巴西出口自然資源和制造業(yè)產(chǎn)品的局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后,這些增長方式的不足迅速暴露出來。表現(xiàn)在對發(fā)達國家市場高度依賴,易受外部沖擊;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不協(xié)調(diào),受到資源、環(huán)境問題、基礎設施瓶頸等諸多制約;收入分配不平衡擴大,民生問題突出。俄羅斯嚴重依賴能源生產(chǎn)和出口,2012年1—10月能源產(chǎn)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70.6%;印度還有約3億窮人,8000萬人生活在貧民窟中;南非的失業(yè)率在25%左右徘徊;巴西陷入大起大落的“雞飛式”增長,1.9億多人口中仍有1600多萬貧困人口。印度、巴西、南非還長期面臨“雙赤字”(經(jīng)常項目赤字和財政赤字)問題,制約了應對外部沖擊的政策空間。2010年,俄羅斯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位于全球第65位,巴西第73位,中國第89位,南非第112位,印度第121位,說明不僅在人均收入方面仍低于發(fā)達國家,在教育、衛(wèi)生、醫(yī)療等民生指標上也遠為落后。
金磚國家都認識到轉(zhuǎn)變增長方式的迫切性,紛紛出臺政策和改革措施,如通過各種刺激消費措施,擴大內(nèi)需,降低對外需的依賴;改革稅收制度,促進對基礎設施投資和吸引外資;加快醫(yī)療、教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改善民生等。深化改革則是各國成功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IMF認為,俄羅斯如能加快改革進程,可以使經(jīng)濟增長率從目前的3.5-4%提高到6%左右,國有企業(yè)改革是其主要難點。印度要解決每年上千萬的新增勞動力就業(yè),需要保持年均7%的增長速度,但政黨斗爭導致改革難以為繼,成為最大障礙。中國收入差距問題突出,面臨分配體制改革的深水區(qū)。

全球主要銀行和機構(gòu)經(jīng)濟學家有很多認為中國經(jīng)濟2013年將成功軟著陸。圖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
加強合作是金磚國家的共同抉擇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已成為新興大國在經(jīng)濟、金融和發(fā)展領域交流和對話的重要平臺,成為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模式、不同文明攜手合作的范例。作為世界經(jīng)濟的火車頭,金磚國家應繼續(xù)在三個層面上開展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
一、推動國際經(jīng)濟秩序和治理結(jié)構(gòu)改革
金融危機暴露出了全球治理的缺失,金磚國家首先要促成二十國集團(G20)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臺,從以下方面推動全球治理結(jié)構(gòu)改革:一是國際金融監(jiān)管的改革,二是IMF、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gòu)改革,三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四要督促發(fā)達國家重視其量化寬松政策等對全球的負面溢出效應。印度學者認為,金磚國家應在國際關(guān)系中形成一個壓力集團,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新秩序的主要推動力。近年來,金磚國家在IMF和世界銀行改革、WTO談判、聯(lián)合國氣候談判等方面充分協(xié)調(diào)立場,在G20內(nèi)加強磋商和合作,推動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提高了新興大國在多邊談判中的話語權(quán),維護和擴大了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
二、拓展內(nèi)部經(jīng)貿(mào)合作規(guī)模和深度
經(jīng)過四次峰會,金磚國家在金融、貿(mào)易、農(nóng)業(yè)、能源、技術(shù)合作等諸多議題上達成了共識,發(fā)表了行動計劃。
未來一段時間,一要加大成員間“引進來、走出去”力度,促進產(chǎn)業(yè)合作和貿(mào)易發(fā)展。2011年,中國與其他四個金磚國家貿(mào)易總額占整個對外貿(mào)易總量的7.5%,與東盟貿(mào)易的比重達10.1%。金磚國家內(nèi)部經(jīng)濟關(guān)系還有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Α_展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和全面經(jīng)濟合作協(xié)定談判,探討建立雙邊和金磚國家自由貿(mào)易區(qū)的可能性。同時要利用各成員國間資源和產(chǎn)業(yè)的互補性,推動投資和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促進各國服務業(yè)、制造業(yè)、基礎設施共同發(fā)展。二要通過貨幣互換、本幣結(jié)算、建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深化金融和貨幣合作。金磚國家外匯儲備總額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面臨如何避免“美元陷阱”的問題,在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改革上有廣泛的共同利益。貨幣互換能為各成員國穩(wěn)定匯率和金融市場提供基礎。貿(mào)易和投資的本幣結(jié)算能減輕對美元、歐元等的過度依賴,并節(jié)省交易成本。成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不僅能對成員國項目合作提供資金保障,對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改革也有長遠意義。三要著力推動落實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通過的行動計劃,特別是加強能源、農(nóng)業(yè)等領域的合作,提高各國能源、糧食安全水平。俄羅斯、巴西、南非自然資源豐富,中國和印度進口需求巨大,但定價權(quán)長期掌握在發(fā)達國家手中,且這一格局在短期內(nèi)難以重新洗牌。金磚國家開展互利合作,不僅能確保供求穩(wěn)定,也利于逐步贏得國際市場上的定價權(quán)。
三、加強金磚國家南南合作戰(zhàn)略和政策的協(xié)調(diào)
金磚國家長期探索形成的“中國模式”、“印度模式”、“巴西模式”越來越受到關(guān)注,激發(fā)了南南合作的加速發(fā)展。冷戰(zhàn)結(jié)束時,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歷史在終結(jié)”的論斷。但20年后,人們看到的是日趨多極化的世界。金磚國家日益成為重要的市場,西方國家在世界進口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南南貿(mào)易重要性增強。2009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非洲的主要貿(mào)易伙伴。“金磚四國”與非洲的貿(mào)易占非洲外貿(mào)比重從1993年的4.6%提高到了20%多。南非加入金磚國家后,金磚國家在南南合作中的意義更加明確。OECD的報告甚至斷言,南南貿(mào)易將是未來10年世界經(jīng)濟的主要增長引擎。在南南合作方面,一要深化金磚國家間雙邊戰(zhàn)略與政策協(xié)調(diào),如中印非洲事務磋商、中印拉美事務磋商等;二要探討“中非合作論壇”、“印非合作論壇”、“印度—巴西—南非論壇”等各種機制的協(xié)調(diào)和整合;三要通過聯(lián)合項目開發(fā)在能源和資源、援助和發(fā)展等方面加強合作。據(jù)南非外交部稱,第五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主題將是“BRICs與非洲:發(fā)展、一體化和工業(yè)化伙伴”。峰會的成功召開,將為南南合作及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共同發(fā)展提供新的契機和動力。
[1] http://www.wallstreetdaily.com/2011/12/27
[2] "India's economy":A BRIC hits the wall,the Economist, 31 May,2012.
[3] Fleming,S,"The Brics’ Growth Story Start to Lose its Way",The Times,2 January,2012.
[4]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23rd January 2013.
[5] Deutsche Bank Research (2011),Public Debt in 2020: Monitoring Fiscal Risks in Developed Market.
[6]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2.
[7] Issouf Samake and Yongzheng Yang,Low-Income Countries' BRIC Linkage: Are There Growth Spillovers? WP/11/267,IMF,November 2011.
[8]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2.
[9] Wilson & Purushothaman,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Goldman Sachs,2003.
[10] World Bank,Bridging the Atlantic--Brazil and Sub-Saharan Africa: South-South Partnering for Growth,December 14, 2011.
[11] OECD,Looking to 2060: Long-term global growth prospects,Economic Policy Paper No.3,November, 2012.
[12] Kharas, H,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in E Ghani (ed.), Reshaping Tomorrow,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3] Eurobank Research,Emerging Markets Outlook: Growth to remain robust, despite the ongoing slowdown,Global Economic & Market Outlook,March 2,2012.
[14] Sergei Dubinin,Time for Financial Repression,http://eng.globalaffairs.ru/,24 September, 2011.
[15] UNIDO,Structural Change,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BRICS,November 2012.
[16]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17] Odd Per Brekk:Economic Outlook and Policy Challenges for Russia in 2012,RIA Novosti,January 26, 2012.
[18] Brahma Chellaney,BRICS in the Wall,http://www.hindustantimes.com,March 29, 2012.
[19] Hanson, G,Changing Dynamics in Global Trade, in M Haddad and B Shepherd(eds.), Managing Openness: Trade and Outward-Oriented Growth after the Crisis, World Bank,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