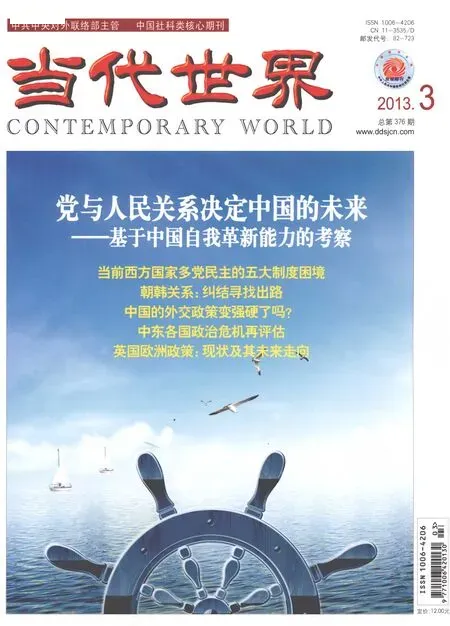阿拉伯學者談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
于 穎/文
阿拉伯學者談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
于 穎/文
肇始于2010年底的中東地區動蕩至今已過去了兩個年頭。期間,已有四個國家發生了政權更迭。起初,包括阿拉伯知識階層在內的國際各大智庫皆對事態發展持樂觀預期,認為它是一場推動該地區向前發展的正向行動,并賜之以“阿拉伯之春”的美稱。然而,時隔兩年,當事國不僅沒有實現其預想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經濟發展與繁榮、社會祥和與開明,反而隨著事態向縱深發展,各種矛盾引發的沖突將該地區形勢帶入到了任何人事先都未曾預料到的動蕩混亂境地:地區伊斯蘭政治力量借機強勢崛起,并在許多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主角;西亞北非地區亂局外溢效應波及周邊國家和地區,引發民族分裂和教派爭端所導致的血腥仇殺。昔日洋溢在樂觀派臉上的笑靨不見了,當初的愉悅心情已被焦慮不安所代替,他們疾呼:昔日充滿希望的“阿拉伯之春”已幻化成為冷酷無情的“阿拉伯之冬”。值此輪阿拉伯地區動蕩兩周年之際,一批有良知的阿拉伯學者或親歷了此次社會風暴,或自始至終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并緊跟形勢發展的進展,撰寫了大量相關文章,從不同角度對事件進行解讀與剖析。這其中有受西方影響主張自由民主的世俗代表,也有受伊斯蘭文化影響頻深的保守派。為較全面客觀地反映阿各界人士的觀點,編譯者在摘編文章時注意兼顧兩者之間的平衡。以下觀點皆摘自阿拉伯專家學者,不代表編譯者個人立場,僅供參考。
一、各方對“阿拉伯之春”發展至今產生的社會效益普遍表示失望與不滿,但認為要將運動進行到底。
1、總部設在科威特的“海灣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阿齊茲·本奧斯曼在2013年1月14日《中東網》網頁上發表題為《“阿拉伯之春”第三年,從樂觀走向失落》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阿拉伯之春”的經驗在于它成功推翻了世襲獨裁統治,并實現了通過票箱贏得選舉的“民主”制度。但是以這種方式上臺的新當權者卻采取了比其前任更為暴烈的獨裁,其具體行為是通過對前任變本加厲的討伐與懲治,來樹立新政權的權威。判斷一場革命的成敗可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標準:從歷史角度衡量要看它是否產生新理念和新原則,如法國大革命使“自由、平等、博愛”等引領時代進步與發展的觀念深入人心,其影響力延續至今;從現實角度看它是否有利于促進政治變革、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阿拉伯之春”以狂飆突進開始,以地區國家經濟衰落、社會分裂告終,既沒有建立現代民主制度,也沒有營造穩定的社會環境,更沒有向青年人提供其所企盼的就業機會,這勢必使“希望的春天”轉化為“沮喪的冬天”。
2、受西方自由派思想影響較深的突尼斯裔美國學者、《半島網》專欄作家蘇海爾·格努西在《阿拉伯革命兩周年,經驗與教訓》中寫道,“阿拉伯之春”已持續兩年多時間,它雖然推翻了多個國家持續數十年的強權統治,但在該運動經過初期勢如破竹的風潮后卻逐漸走向迷茫,廣大民眾對現狀極度失望,原以為革命后政治、經濟會出現改觀,生活水平有望得到提升。然而,在為其付出高昂代價后,一切如故,甚至今不如昔,一些人開始懷念前朝政權的統治時光。突尼斯形勢并不樂觀,政客們瘋狂爭權奪利,導致國家陷入混亂,國家重建的過渡期被迫延長。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新總統穆爾西醉心于擴大總統權限,導致國內政局持續動蕩,反對派質疑他可能成為又一個穆巴拉克。敘利亞政府軍與反對派之間正進行著你死我活的廝殺,敘已墜入內戰和民族分裂的泥潭不能自拔。
3、沙特阿拉伯資深外交家,后任多個阿拉伯電視臺政治評論家賈馬勒·哈什格吉在近期發表的標題為《“阿拉伯之春”已結束,但不能容忍走回頭路》的文章中認為,雖然目前阿拉伯各國面臨著多重挑戰與困難,但無論前途多么艱險也要勇敢地走下去,絕不能走回頭路。文章說,“阿拉伯之春”結束了嗎?是的,它的狂熱浪漫期已結束,轉而面對殘酷悲涼的現實世界,經濟凋敝,官員瀆職,社會怨聲載道。從這個角度看,“阿拉伯之春”的確結束了,但阿拉伯革命仍在繼續,它所產生的變革沒有停止。樂觀的分析家們看到了埃及市民在示威后自動回到解放廣場,將便道打掃得干干凈凈,一名利比亞武裝組織的青年聽從利新政府的號召,向政府繳械,并投身于國家重建進程中,并以此預言阿拉伯人汲取歷次革命的教訓,正行走在振興的道路上。悲觀的或稱現實主義分析家則唱衰此次運動,并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為例證,預言即使是此次革命的最大贏家埃及,也需要至少十年時間才能恢復穩定,要將埃及的社會體制變為西方民主制度至少需要數十年時間。但無論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都一致認為,絕不能開歷史倒車。以埃及為例,現任總統穆爾西政權有可能倒臺,并被迫提前舉行總統選舉,但埃及絕不會退回到穆巴拉克時代,即使埃及軍隊接管政權,也只是暫時現象。并預言未來即使埃及實行民主制度,穆斯林兄弟會也不會退出政治舞臺,任何人都無權再次對其進行封殺,同樣,各種世俗自由派力量也會不受限制地存在下去,未來的阿拉伯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寬容與理智。
二、專家們試圖從歷史、政治、社會等層面剖析造成此種結局的原因。
1、巴勒斯坦政治學教授、《半島網》專欄作家阿卜杜勒·斯塔爾·卡西姆認為阿拉伯民族落后的部族制度與現代民主政治難以融合。他認為現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名為“共和國”,但其政治文化中逐水草而居的部落意識和血親仇殺的沙漠文化根深蒂固。主要表現:一對本部族的認同超過對國家的效忠,唯部族首領和酋長馬首是瞻,為維護部族利益時刻準備與外族展開仇殺,由此造成嚴重的社會分裂;二是唯我獨尊,剛愎自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是思想極端、思維偏狹,缺少理性與克制,體現在政治行為上便是對政敵及反對意見的零容忍。當前,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生態仍然酷似部落族群,議會、總統選舉像極了酋長推選,獲勝者的首要任務是回饋本部族成員,想方設法滿足其合理或不合理的各種需要,而不是回應全體國民的政治訴求,保障其物質需要。當今阿拉伯社會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組織和領袖人物,更缺乏帶領全體國民實現政治變革、民族自強的核心力量。
2、蘇海爾認為,“阿拉伯特色”的政黨政治導致各政治力量只顧爭名奪利,罔顧民眾利益。蘇認為20世紀50—6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反帝、反殖運動風起云涌,民眾把殖民主義者趕走后,并沒有自己當家作主的意識,而是將政權交予當時的社會精英,認為可以依靠他們建立民主政權,實現國家與民族的復興。殊不知沒有限制的權力導致了另一種形式的專制制度的誕生,即“阿拉伯特色”政黨政治的產生和畸形發展。20世紀伴隨民族解放運動一同產生的民族主義政黨,與其推翻的殖民主義者一樣缺乏政治度量,利用權力對伊斯蘭政黨進行殘酷打壓和封殺。后者被迫轉入地下,為爭取生存權與當局進行著激烈斗爭,將推翻現政權并取而代之作為終極目標。這種政治生態使得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無法正常發育,也就無法產生眾望所歸的政治領軍人物。各黨領導人均將本黨私利置于所有考量之上,“國家”是其渴望得到的獵物,“民主”則是其獲得統治權的方式和工具。目前包括埃及在內的中東多數國家形勢持續動蕩,其深層原因就在于此。
3、《中東網》在2013年1月15日紀念“阿拉伯之春”兩周年的社論《變革的種種猜想》一文認為,此次阿拉伯世界爆發全局性動蕩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國家政治體制長期以來存在的結構性缺陷,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這些國家政治領導人昏庸無能,缺乏政治敏感性,不能體察、洞悉時代潮流發展的走向,準確判斷國家、地區乃至國際形勢發展動向,并順應歷史潮流采取應對的政策與策略。最典型的例證莫過于薩達姆家族的覆亡。20世紀90年代初,時任伊拉克總統的薩達姆就是因為錯誤地估計了國際形勢,并悍然發動侵略科威特戰爭,導致了其覆滅的結局。其次是各阿拉伯民族缺乏凝聚力,盡管阿拉伯國家人多勢眾,但卻如一盤散沙,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無所作為,致使巴勒斯坦問題成了多個組織,其中有民族主義的、左派自由主義的,以及伊斯蘭宗教色彩的形形色色組織進行幕后交易和討價還價的砝碼,和建立獨裁統治和政治賭博的借口。第三,早在此輪社會動蕩前,一些阿拉伯國家的統治階層就將國家財富揮霍殆盡,而沒有將其用于經濟發展、文化建設和國民素質的提高。國際人類發展報告顯示近十年來,阿拉伯世界的發展水平除少數非洲窮國外為世界最低。
三、普遍認為只有實施全方位、深層次、循序漸進式的改革才能實現阿拉伯民族的復興。
阿拉伯學者普遍認為,要實現阿民族復興的夢想并非朝夕之功,需幾代人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艱苦努力才能實現。
1、敘利亞籍自由撰稿人、《半島網》專欄作家納比爾·阿里·薩利赫認為,要實現阿拉伯民族復興,首先政治上要實施民族和解政策,盡快恢復國家穩定。“阿拉伯之春”使蟄伏了數十年的伊斯蘭政治力量異軍突起,并在政治舞臺上扮演主角,伊斯蘭政黨與世俗自由派博弈加劇,這在埃及、突尼斯兩國表現得最為突出。為了阿拉伯民族團結與統一的根本利益,宗教與世俗兩派須摒棄在政治理念、治國方略上的對立,形成一股合力。這方面執政黨應率先垂范,顯示出足夠的政治智慧與勇氣,對反對黨采取包容政策,搭建平等對話的平臺,就制度創新、經濟改革、社會公正等問題展開對話,從而建立互信,實現社會各界觀念互動與融合。其次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取信于民。大多數阿拉伯民眾投身于“阿拉伯之春”,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此運動改變困窘艱難的生存狀況,他們對于新政權的主要期待就是盡快提高生活水平。為此,應調動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制定符合各自國情的發展規劃,逐步改善經濟狀況,并努力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此外,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兼顧社會效益,處理好效率與公正之間的關系。第三是進行思想啟蒙與社會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知識水平與文化素養。要實現阿拉伯民族的全面振興,須制定明確的、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目標,并動員、組織廣大民眾廣泛參與其中,要以改選民眾的思想為先導,改變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渾渾噩噩,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樹立積極向上,樂于奉獻的精神風貌,加強愛國主義、公正、誠信等現代正能量理念的灌輸,使阿拉伯社會逐步從部族社會走向公民社會。
2、蘇海爾認為鑒于青年是社會的未來,為實現阿民族美好未來,應著力加強對青年一代的培養。他在文章中表示,公允地講,讓前朝政客擔負起反專制統治、實現民族復興的重任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因為這些人本身就生長在暴政統治下,政治的潛規則告誡他們一旦失去權柄,使會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們從未踐行過自由與民主,不諳政務公開、團隊合作等現代社會的通則,更不知輪流執政為何物,他們是暴政的實施者,也是受害者。因此,要實現令人期待的社會變革只能依靠朝氣蓬勃的青年一代,他們信仰自由,渴望機會均等,正因如此,在此輪革命中,阿拉伯各國的年輕人表現得最為搶眼。但要使其真正擔負起民族振興的重任,他們還要經歷多重磨練與考驗,并經受嚴格的教育,使他們在思想上剔除前朝保守思想的余毒,同時逐步樹立諸如秉公、誠信等具積極進步向上的理念,使其成為有引領時代潮流的具有嶄新面貌的新一代。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西亞北非局)
(責任編輯:魏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