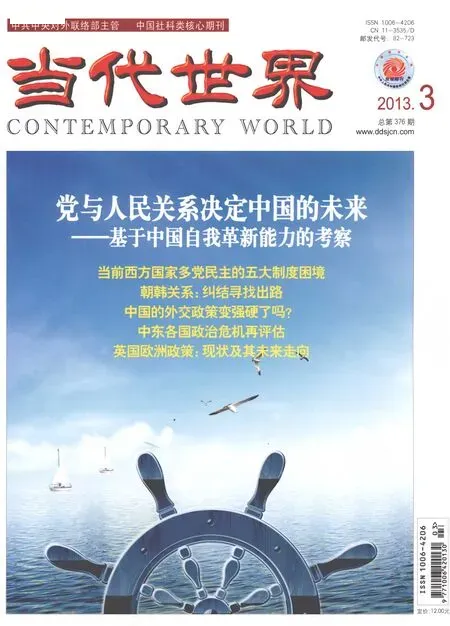中東各國政治危機再評估
■ 王京烈/文
(作者系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
所謂“阿拉伯之春”的性質
自2010年底以來,中東各國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的政治浪潮,其中夾雜著程度不同、形式各異的暴力沖突,使局勢急劇動蕩。國外媒體將其稱之為“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革命”。其實,持續兩年多的政治浪潮是中東國家出現的嚴重“政治危機”,是“原生性”的、以改善民生為起始,帶有一定的民主訴求、同時夾帶著某些宗教教派和部族沖突的“政治危機”,但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有選擇性的干預下”,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結果:有的國家很快平息了危機,但有的國家則出現了政權更迭,實際上被納入了多年前美國提出的改造中東的“大中東計劃”框架內,并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其主要依據是:
——中東各國的政治危機或動蕩風潮基本上都屬于“三無產品”,即“沒有一呼百應的政治領袖或領導集體,沒有嚴謹、縝密的政治組織和目標明確、切實可行的政治綱領,也沒有廣泛、堅實的群眾基礎”。例如,有些國家的反對派領導人此前并無人知曉,常年流亡國外,臨時進行“遙控”或匆匆返回國內參與活動;反對派組織往往是臨時拼湊起來的,派系繁多,內部紛爭混亂,其斗爭目標和政治綱領也反復更改;卷入到政治危機中的人員也極為復雜,不僅有一般的民眾,也有種族主義或教派勢力,甚至還有宗教極端主義分子和恐怖主義分子或基地組織成員。這一切都加劇了政治危機的復雜性。
——中東國家的所謂“民主改革”是在西方國家“有選擇性的干預下”進行的,并沒有對部分帶有封建色彩的君主制國家進行改革。相反,在兩年多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中,君主制國家的王權并沒有受到強力沖擊。海灣富有的君主國一方面大幅提高民眾的福利待遇,就像西方媒體說的那樣,“阿拉伯政府滿街撒錢”,破財消災;另一方面,動用美國提供的先進武器,甚至聯手鎮壓了民眾的示威游行(例如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GCC成員國向巴林派出武裝部隊),鞏固了君主制政權。
——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的政權更迭也只是“人去政留”,并不是推翻舊政治體制、建立新政治體制之革命。所謂“新政府”的政策也只是做了某些改良和調整。目前看來,突尼斯的振興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下屬的政黨自由正義黨等先后執政表明,伊斯蘭力量不僅迅速崛起,而且部分已掌握了國家政權,但未能使中東國家翻開新的歷史篇章。埃及總統穆爾西執政后,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修改憲法、整頓軍隊、調整立法、司法、執法三權關系,但實際上是強化總統的權力。因此,招致埃及民眾的極大不滿,紛紛上街游行,抗議、譴責穆爾西太過專權。對埃及而言,并沒有實現兩年前推翻穆巴拉克時設定的目標,穆爾西本人也被示威民眾稱為“新法老”。
考察近現代中東政治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總體而言,中東國家政治發展要經歷三個發展階段:傳統專制主義階段、過渡政治階段、現代民主政治階段。中東大多數國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獨立,并形成了中東獨立民族國家體系。擺脫了殖民主義統治的中東國家,相繼進入了社會發展的轉型期,即由傳統、落后向現代、發達社會過渡的社會轉型時期。
社會轉型時期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目前,絕大多數中東國家均處于過渡政治階段,即處在由傳統專制主義或集權主義向現代民主政治體制過渡的轉型時期,除少數國家屬于分權制約的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外,大多數中東國家均屬于集權主義或半集權主義政治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東國家相繼出現了一系列“政治危機”,其中比較重要的有:1992年開始并持續了七年的阿爾及利亞政治危機,2005年發生的黎巴嫩“雪松革命”和毛里塔尼亞軍事政變,2004年和2009年先后在伊朗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期間發生的政治危機等。所以,目前中東出現的社會動蕩是其發展進程中一系列政治危機的一部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從其結果來看,也沒能給中東國家帶來穩定與發展。總體來看,目前中東國家的發展也沒有處在民主革命“前夜”的歷史變革轉折點上。
中東政治危機的后果和影響
盡管中東這場政治危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這場政治危機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其代價是十分昂貴的、且負面影響更大。中東政治危機造成的諸多后果和影響遠不是這篇短文可以囊括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幾點。
——彰顯要求改善民生、推進民主的民意。中東國家大規模的民主革命當然不會在一夜之間形成,其孕育、發展必然要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此番政治危機的積極意義就在于:使民眾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政治參與熱情,為未來的民主革命積蓄能量。
在此次政治危機中,幾乎各國都有十多萬到幾十萬人先后走上街頭,卷入了示威游行的浪潮中。盡管參加示威游行的民眾來自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背景、既沒有什么嚴密組織、訴求也不盡相同,但都表達了要求改善民生、要求變革、反對專制的民意,對各國政府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沖擊。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執政24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執政30年,但當民眾走上街頭要求變革、要求民主時,他們也被淹沒在民眾政治訴求的洶涌浪潮中,不得不放棄權杖。盡管突尼斯、埃及發生巨變有多種原因,但民眾意愿的沖擊無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東國家在經歷這場政治危機之后,各國民眾表現出的民意和對民主政治的訴求,以及在政治生活的作用,是任何統治者都無法忽視的問題。
——伊斯蘭力量乘勢崛起有其必然性。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東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仍是比較落后的(少數石油富國也只是靠出口原料過上了富足的生活),求新求變、期盼更美好的生活是各國民眾的普遍心態。由于多種社會歷史原因,中東國家的公民社會并不發達,除執政黨外,其他政黨和政治組織不甚發達;與此同時,伊斯蘭教在中東地區則是無處不在、根深蒂固的。所以,無論是統治者還是反政府勢力都在借助宗教的力量。也正因為如此,當世俗的民族主義政權被推翻、出現權力真空之后,伊斯蘭力量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遇。伊斯蘭力量憑借其自身深厚的宗教傳統、在民眾中的廣泛影響和獨特的社會組織和動員功能,不僅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政權更迭的國家能夠執掌權柄,在其他中東國家也同樣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當然,這一現象并不意味著中東社會發展必須走伊斯蘭復興帶動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模式,但也反映出中東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復雜性,加劇了日后教俗之間的矛盾沖突。
——美國等西方國家采取了新的干預方式。殖民主義似乎是一種早已遠離現今社會的國際壓迫,但是弱小國家仍在“被賣出買進”,仍在被大國隨意操縱、干涉。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影響和在中東國家政治危機中“推波助瀾”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西方干預理論的支持下,歐美等西方國家利用中東形勢適時推出了新的干預模式,為其所用。先是利用新媒體(手機+互聯網)散布消息、鼓動民眾走上街頭,形成對政府的壓力;而后再進行有選擇性的干預,以達到自身的目的。到目前為止,西方的這種干預模式對實現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目標還是有效的,以較小的代價實現了戰略目標,頗似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提出的“巧實力”運用。2011年西方國家發動“利比亞戰爭”,創立了冷戰后干預、顛覆他國的“利比亞模式”。雖然已經推翻了卡扎菲政權,但戰后利比亞形勢并不樂觀,也沒能建立起新的有效政府,利比亞已陷入新的動蕩之中。在顛覆敘利亞過程中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留下了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破爛攤子,反對派武裝與政府軍的沖突、戰亂仍在繼續。大國粗暴干預破壞了中東國家自身社會發展進程,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其負面影響將長期作用于中東地區。
——政治危機使各國政局動蕩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和恐怖主義泛濫。
目前中東國家處在社會發展的“轉型期”本身也是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而持續兩年多的政治危機則進一步加劇了局勢動蕩。動蕩局勢不僅使社會不穩定,還直接導致相關國家經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早在2011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報告就顯示,中東地區安全局勢發生的重大變化不僅導致國際油價飆升,并給受影響的國家造成至少55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目前為止,就是按照保守的估算,經濟損失也要超過上千億美元,還不包括外資投資、旅游等方面的損失。此外,在局勢動蕩和戰亂的國家還造成了大量人員的死亡,例如敘利亞戰亂不僅造成近百萬難民流離失所,還使約7萬人喪失了生命。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西方國家對中東政治危機“有選擇性的干預”還導致流血沖突頻仍、暴力肆虐、恐怖主義泛濫。目前中東國家局勢動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極端宗教主義、種族和部族勢力以及基地組織參與到與相關國家政府對抗的戰亂中所導致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毒瘤,一旦擴散就將形成比經濟停滯等社會問題更難解決的痼疾,形成對中東社會乃至中東以外地區的負面影響。
中東政治危機發展態勢和各國面臨的挑戰
席卷中東的政治危機已歷時兩年多,且尚未終結。雖然彰顯了民意,但目前的現實距離民眾的訴求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在有的國家,民眾提出了“二次革命”的口號,而有的國家仍處在戰亂之中,中東國家依然面臨著諸多嚴重的挑戰。
敘利亞戰亂及其外溢效應。敘利亞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敘利亞原本就是一個充滿教派紛爭、種族和部族矛盾的國家,而阿薩德家族借助組織嚴密的復興黨、軍隊等強力機構牢牢掌控著國家,保持了數十年的穩定;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中東政治危機堅持要推翻巴沙爾政權,為此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和反政府武裝;反政府勢力則派系繁多,既有主張和平斗爭的,更有力主暴力奪權的(目前后者占上風),在反政府軍事力量中不僅有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甚至還有基地組織成員,各種力量還得到國外勢力的支持。雖然戰亂已經持續了近兩年,但如果沒有西方國家的直接軍事干預,巴沙爾未必就能倒臺。由于2014年敘利亞將舉行總統選舉,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太可能“等不及了”而冒戰爭的風險。目前,敘利亞已經成為中東政治漩渦的中心,其外溢效應必將影響阿以沖突、黎巴嫩局勢、庫爾德問題、伊朗核問題、伊拉克局勢等重大問題。
埃及局勢與教俗勢力之爭。埃及總統穆爾西執政后,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卻多次引發民眾和司法系統的抗議。2013年以來示威游行的規模進一步擴大,示威民眾稱穆爾西為“新法老”也只反映出一面,而另一面是“伊斯蘭長老”。穆爾西與埃及民眾的沖突不僅僅是政治訴求的差異,它折射出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在國家治理觀念上的沖突。實際上,埃及的沖突也是中東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沖突的縮影,在中東頗具代表性。伊斯蘭教承載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即宗教與非宗教功能尚未分離。實現政教分離不僅是一般宗教發展的基本規律,也是世界各國發展進程中的必由之路,當然也是中東國家步入現代化必須解決的歷史命題。目前中東各國伊斯蘭力量的發展則預示著中東教俗勢力博弈的長期性和復雜性。
君主制國家可能成為下一輪政治危機沖擊的目標。與共和制國家相比較,君主制無疑是相對落后的政治體制。此次中東君主國能夠幸免,原因是多樣的:石油高收入國家采取高福利政策;“食利國”(Rent State)對大批外來勞工實行嚴格監管政策和定期“輪換”政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著良好合作關系,并得到這些國家“有選擇性干預”的保護。海灣石油富國甚至還向巴林派出了軍隊與巴林政府聯手鎮壓了游行的民眾,保衛了海灣地區的君主制國家。但這些都無法改變其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如果君主制國家不采取相應的政治變革、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那就不可能永遠這樣幸運了。
中東各國面臨的嚴峻挑戰。首先,解決社會財富合理分配問題和監管機制缺乏及腐敗問題。中東國家的基尼系數并不算太高,但也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財富的問題。而缺乏監管、濫用公權和腐敗問題是中東國家的普遍現象。這不僅是引發中東政治危機的動因,更是各國在制度建設層面的長期、艱巨任務。其次,加強民族國家認同與民族國家建設。消除中東國家普遍存在的教派紛爭與種族和部族矛盾,避免由于“認同差異”引發沖突和產生“離心力”,成為分裂主義和動蕩的策源地。黎巴嫩“教派分權”、困擾多國的庫爾德民族問題等表明民族國家建設的任務仍很艱巨。再次,政治合法性與繼承危機問題。這絕不是政治領袖個人的去留問題,而是直接關系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問題,即如何從制度層面保持權力平穩過渡和政策的連續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多數國家的政治合法性都將逐步由傳統向現代化過渡,最終建立現代法律體系。
結 語
“和平、發展、民主”是當今世界的潮流,也是絕大多數民族國家建立之后,政治、社會、經濟循序漸進、遞次發展的基本規律。民主的大廈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有堅實的經濟發展基礎,而和平與穩定則是前提條件。簡言之,沒有和平與發展,民主就只能是虛幻的海市蜃樓。毫無疑問,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絕不是僅靠熱情與沖動和上街游行幾次就能實現的。中東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建設有賴于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和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實施。所以,中東國家距離建立起現代民主政治體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 See "Throwing Money at the Street",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38.
[2] 王京烈. 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東[M].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 7.
[3] 引自商業部網站消息,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110/20111007793348.html.
[4] 新華社據聯合國難民署消息,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2/17/c_124351218.htm.
[5] 據俄羅斯網站消息, 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shehui/20130213/43690484-print.html.
[6] 王京烈.伊斯蘭世界的命運與前途[J].國際問題研究,2004 (1).
[7] 即便在法制程度較高的以色列也時而爆出從總統到總理和部長等高官濫用公權和腐敗的丑聞,而其他國家情況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