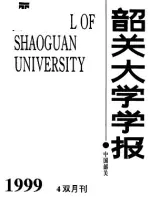產業集聚、環境污染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基于廣東省21個地級市數據的分析
趙 麗,劉芳娜
(韶關學院 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產業集聚、環境污染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基于廣東省21個地級市數據的分析
趙 麗,劉芳娜
(韶關學院 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利用2001-2010年廣東省21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分析研究產業集聚、環境污染、產業結構等因素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產業集聚程度、環境污染強度、非農產業比重影響區域經濟增長。但是,在不同地區這些影響因素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向與程度存在差異。
產業集聚;環境污染;產業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時,區域發展失衡問題日益凸顯,成為全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從省際間的角度看,地區經濟差距在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呈現短暫的下挫,而后于20世紀90年代又呈現持續上升的局面[1]。到了21世紀,雖然人均GDP的Theil指數總體上呈下降趨勢[2],但地區發展差距過大的矛盾仍困擾著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對于區域之間的差距,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解釋,有人將地區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本原因歸于第二產業的高產值份額和非農產業在空間上的不平衡分布[3],也有學者認為產業結構和工業化水平的差異程度是形成地區差距的重要原因[4]。隨著產業集聚效應的顯現,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受到廣泛關注。一些學者將產業集聚與區域差距聯系起來,認為區域發展差距的擴大與產業集聚密切相關。范劍勇實證分析了1980年和2001年中國地區專業化和產業集中率的變化情況,發現中國現階段處于“產業高集聚、地區低專業化”的狀況,致使制造業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難以向中部地區轉移,從而導致地區差距不斷擴大[5]。劉軍、徐康寧運用1999-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產業集聚對區域差距的影響,結論是產業集聚顯著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導致了區域差距的產生[6]。此外,產業集聚的環境外部性問題亦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有學者認為產業集聚雖然促進了經濟發展和一定程度上的區域協調,但也帶來了亟待解決的環境問題[7],高密度的產業集聚造成了生態環境的惡化[8]。也有學者認為如果簡單將生態環境惡化歸咎為產業集聚未免有失偏頗,一些城市生態環境的惡化是由粗放型的生產方式等原因造成的[9]。而閆逢柱等通過對產業集聚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實證考察,證明短期內產業集聚發展有利于降低環境污染,但長期內產業集聚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10]。總之,基于我國國情的產業集聚與區域差距、環境污染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由于研究個案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有較大分歧。廣東省是我國地區差距顯著的區域之一,也是產業集聚最明顯的區域之一,已有的研究證實產業集聚是廣東省地區差距的重要成因之一[11]。產業集聚有助于區域經濟增長,但產業集聚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環境污染問題,這是否會抵消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仍有待深入探討。本文重點關注產業集聚、環境污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們的研究將利用廣東省21個地級市的相關數據,研究產業集聚、環境污染等給區域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
一、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情況的測度
(一)產業集聚程度
制造業是廣東省產業集聚比較明顯的行業,利用廣東省制造業的集聚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廣東省的產業集聚狀況。通常,產業集聚程度測度的方法有空間基尼系數法、區位熵法等,考慮到從區域角度分析產業集聚程度的需要,本文采用區位熵法計算各地的產業集聚指數。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LQij為i地區j產業的區位熵,qij為i地區j產業總產值,∑qij為全省j產業總產值之和,qi為i地區工業總產值,∑qi為全省工業總產值之和。一般而言,LQij值越大,表明j產業在該地區的集聚程度越高。
根據以上計算公式,利用21個地級市2001-2010年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各區域制造業區位熵(如表1所示)。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選擇了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以及規模以上制造業總產值數據對制造業區位熵進行測算。結果顯示,廣東省的制造業集聚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是制造業集聚程度最高的區域,2001-2010年間,除個別年份外,絕大部分時間該地區的制造業區位熵都大于1,而粵東、粵西和北部山區的制造業區位熵都在1以下,說明珠三角地區的制造業集聚程度比較高,而粵東、粵西和北部山區的制造業集聚程度則明顯低于珠三角地區。從各個區域內部來看,不同地級市之間也存在差異,珠三角地區除個別地級市的區位熵在1以下外,大多在1以上,而粵東、粵西、北部山區則是絕大多數地級市的區位熵都在1以下。

表1 2001-2010年各區域制造業區位熵
(二)污染物排放強度
產業發展不可避免地產生污染物,如廢水、廢氣、廢渣等,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張,污染物的排放量就會增加。從這個角度來看,產業集聚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即產業集聚導致環境負外部性問題產生。近年來,隨著廣東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產業規模的迅速擴張,全省污染物排放總量也呈上升趨勢。據統計,2010年全省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比2001年增加了7億多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增加了14 638億標立米。與此同時,燃燒廢氣、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增多,致使部分地區空氣質量下降、酸雨頻發,環境污染嚴重。為了進一步了解各地區的環境污染強度,本文選擇以單位工業增加值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等作為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標,并使用極值化方法對相關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得出各區域單位工業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如表2所示)。從中可以看出,2010年與2001年相比,四大區域的單位工業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均有所增加,其中粵東地區是污染物排放強度上升最快的區域,10年間該區域單位工業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增加了8倍之多。盡管如此,北部山區仍是污染物排放強度最高的區域,排在第二位的是粵西地區,其單位工業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水平一直高于珠三角和粵東地區。究其原因,主要還是與當地產業的高碳特征密切相關。而珠三角和粵東兩地比較,2001-2007年珠三角地區的污染物排放強度一直高于粵東地區,2008年以后,珠三角地區的污染物排放強度開始低于粵東地區,這主要應歸功于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升級以及環境規制的作用。當然,各區域內部地級市之間也存在較大差異,以2010年為例,肇慶的污染物排放水平比珠三角平均水平高出3倍多,汕尾大約是粵東平均水平的2倍,陽江、韶關則分別是粵西和山區平均水平的1倍多。

表2 單位工業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水平
二、產業集聚、環境污染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檢驗
(一)模型構建
產業集聚、產業規模擴張導致的環境負外部性對區域經濟增長會產生何種影響?為了回答這一問題,下面我們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產業集聚、環境污染和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探究。考慮到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因素較為復雜,區域經濟差距的產生與產業結構的差異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為了精準反映產業集聚、環境污染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我們將產業結構(以非農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衡量)變量引入模型。于是,模型以人均GDP作為被解釋變量,制造業區位熵、單位工業增加值污染物排放水平、非農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為解釋變量,其中人均GDP指標取對數形式。面板數據模型的一般形式設為:

其中,Yit為i市t時間的人均GDP的自然對數值,Xit為各地級市各年度的制造業區位熵、單位工業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水平、非農產業增加值比重,α為常數項,βi為變量系數,μit為殘差。
為了建立有效的面板數據模型,我們首先通過Hausman檢驗確定模型存在固定效應,然后通過F檢驗確定建立變系數模型更加有效。因此,本文最終采用變系數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二)回歸結果分析
在模型估計中,本文采用同時對截面單元異方差性和同期相關性進行修正的廣義最小二乘法,選擇跨截面殘差的協方差作為權數,估計軟件為Eviews6.0,得到的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可以看出,回歸方程調整的 R2達到 0.99,F 為 244.87,Durbin-Watson檢驗的DW值為1.89,模型擬合較好,除了佛山和茂名的區位熵系數、梅州的污染物排放強度系數外,其他地區的各個變量系數均能通過t檢驗。回歸結果呈現以下特點:首先,區位熵對不同地區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在19個顯著的區位熵估計值中,有8個為負值,即整個考察期內區位熵對這些地區人均GDP的影響是負向的,說明產業集聚還沒有發揮其集聚效應;其次,20個顯著的污染物排放強度估計值中僅有6個為負值,也就是說大多數地區環境污染因素對人均GDP的影響與通常的預期相反,這可能與環境污染影響的滯后性有關;第三,非農產業比重,除茂名外,其他地區都對人均GDP有正向影響,但在不同地區其影響程度有著顯著的差異,深圳、珠海、廣州等地產業結構因素的影響系數極大。三個解釋變量比較,除肇慶外,其他地區都表現為非農產業比重的影響程度大于區位熵和污染物排放強度,說明產業結構因素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表3 變系數模型的估計結果
三、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產業集聚、環境污染、產業結構給區域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的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幾點結論和啟示:
首先,理論上講,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具有正向影響,提高產業集聚水平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但是,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在部分地區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或是表現出統計上的不顯著,說明這些地區尚未形成各種生產要素集聚、協調發展的格局,產業集聚還沒有完全發揮集聚效應。事實上,產業集聚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政府部門出于經濟增長的考量而人為規劃形成的產業集聚往往不符合發展規律,企業數量雖然增多了,但企業間互有聯系的合作關系并不存在,產業集聚優勢沒有形成。因此,對于產業集聚發展,政府應該著眼于創造有利于企業合作與分工發展的環境,加強基礎設施、金融服務、技術支持服務、法律服務、市場營銷服務、教育培訓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促進企業“自發”形成適合自身發展需要的產業網絡,形成產業集聚優勢,從而保障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環境污染是一個帶有明顯滯后影響的因素,一些亟待解決的環境問題對區域經濟增長的阻礙作用在短期內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如果忽視環境影響效應的行為繼續存在,那么,污染物排放強度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負向影響勢必全面顯現。在全球低碳經濟背景下,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張、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多,低端高碳產業面臨巨大的減排壓力,環境問題成為各地發展必須攻克的一大難題。從生態文明和環境保護的視野上看,加快產業升級步伐,促進低碳產業集聚,應是各地區避免環境負外部效應的必由之路。當然,環境問題的解決還必須以環境規制作為保障。
第三,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表現為非農產業占的比重越大,越能提高人均GDP水平。因此,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是現階段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時期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升級是區域發展的迫切需要。各地區應抓住機遇,引導資源合理配置,一方面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農業產業化,夯實農業的基礎地位;另一方面要著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現代產業體系。
: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轉型的地區差距分析[J].經濟研究,1998(6):11-16.
[2]馬穎憶,陸玉麒.基于變異系數和錫爾指數的中國區域經濟差異分析[J].特區經濟,2011(5):273-275.
[3]范劍勇,朱國林.中國地區差距演變及其結構分解[J].管理世界,2002(7):37-44.
[4]張義彩,閆榮國.產業結構工業化程度與地區差距的實證分析[J].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19-23.
[5]范劍勇.市場一體化、地區專業化與產業集聚趨勢——兼談對地區差距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2004(6):39-51.
[6]劉軍,徐康寧.產業集聚、經濟增長與地區差距——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0(7):91-102.
[7]李偉娜.產業集聚、環境污染與區域協調發展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10(3):47-48.
[8]馮薇.產業集聚與循環經濟互動關系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4):166-172.
[9]王崇鋒,張吉鵬.制造業產業集聚對生態城市建設影響的定量研究——基于CR4指數的實證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4):140-144.
[10]閆逢柱,蘇李,喬娟.產業集聚發展與環境污染關系的考察——來自中國制造業的證據[J].科學學研究,2011(1):79-83.
[11]李勝會,馮邦彥.地區差距、產業集聚與經濟增長:理論及來自廣東省的證據[J].南方經濟,2008(2):3-18.
The Influence on the Region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Base on the Data of 21 Prefectare-leve Cities of Guangdong
ZHAO Li,LIU Fang-na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es Management College,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Using the data of 2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of 2001-2010,it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n the region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The results showed industry cluster degree,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and proportion of blame farming industry influenc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irection and degree in different region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environmental pollu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F127
1007-5348(2013)01-0081-05
2012-10-28
趙麗(1963-),女,內蒙古通遼人,韶關學院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應用經濟學研究。
(責任編輯:陳景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