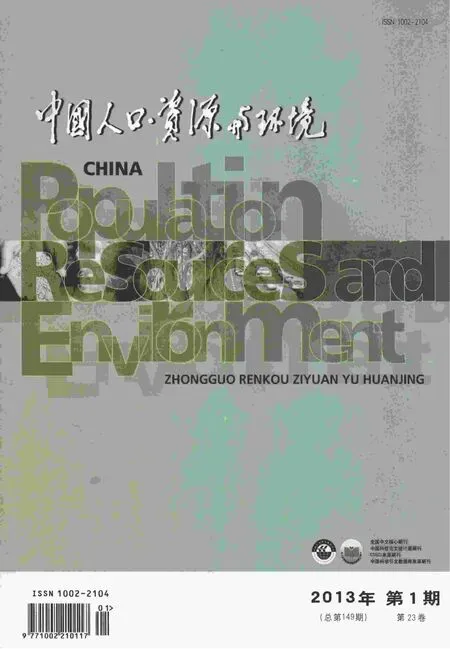基于生態足跡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中國西北部地區生態安全分析
付 偉 趙俊權 杜國禎
(1.蘭州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甘肅蘭州 730000;2.云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云南昆明 650201)
發展是人類歷史社會永恒的主題,其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復雜辨證關系催生出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從生態、經濟、社會等不同角度對其進行延伸研究。其中生態安全評價就是可持續發展研究的一個新領域。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Brown L R)最早在1997年將環境引入安全概念,他認為“目前對安全的威脅,來自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較少,而來自于自然之間關系的可能較多”[1-2]。我國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對生態安全進行研究。周毅[3]在對中國環境生態安全的研究中得出,我國每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4%。
生態安全評價是一種多學科交叉的實踐,隨著研究的深入,其在評價方法已由最初定性的簡單描述發展為現今定量的精確判斷,可歸結為數學模型法[4]、生態足跡法[5]、景觀模型法[6]、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法[7]4 種。
中國西北部地區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資源相對匱乏,生態安全問題也是其今后發展的關鍵。甘肅地處黃河上游,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內蒙古高原的交匯地,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生態安全的重要性。本文以甘肅為例,分析中國西北地區的生態安全狀況。
1 研究方法
“生態足跡”方法由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 Willam Rees[8]在1992年提出并在1996年由其博士生Wackernagel[9-10]完善。生態足跡又稱為生態占用、生態痕跡、生態腳印等,其定義是:任何已知人口(某個人、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生態足跡是生產這些人口所消費的所有資源和吸納這些人口所產生的所有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生產面積(包括陸地和水域)[5]。該方法通過計算支持特定區域人類社會所有消費活動所需要的土地(生態足跡)與該區域可提供的生物生產性土地(生態承載力)相比較來判斷區域發展的可持續性[11]。生態足跡最大的貢獻在于在經濟和生態系統之間建立了一種投影關系,將經濟系統中不同屬性的資源和服務投影成生態系統中標準化的土地面積,并且可以與實際生態系統的標準化土地面積進行比較[5]。生態足跡的概念在1999年引入國內,由徐中民、張志強等[12-13]學者首次利用它開展實證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生態足跡的應用已遍及世界、國家、地區及各個產業等多個層次。
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EF)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需求,這種需求以生態生產性土地的面積來衡量。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EF表示總的生態足跡;Aj表示第j類生物生產性土地的面積;EQj表示均衡因子;EPij表示全球平均的單位j類型土地生產第i種資源的量;Cij表示與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對應的i種資源消費量;nj表示與第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對應的資源種類。這樣就得到了總的生態足跡,再除以人口即得到人均生態足跡。
2 甘肅省2001-2010年生態足跡的計算
根據生態模型的計算方法,對甘肅2001-2010年的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生態盈余和萬元GDP生態足跡進行實際計算,結果見圖1。甘肅的生態足跡計算主要包括生物資源的消費和能源的消費。由于數據的限制,本文沒有考慮貿易對甘肅生態足跡的影響。本文采用以往國內的絕大多數研究中普遍采用 Wackernagel[14]1997年最早計算52個國家和地區時采用的均衡因子,即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和建設用地的均衡因子分別為:2.82、0.54、1.14、0.22、1.14、2.82。在計算化石能源用地時,利用 Wackernagel等[9-10]所確定的煤、石油、天然氣和水電的全球平均土地產出率分別為55、71、93、1000GJ/hm2,將能源消費所消耗的熱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能源土地面積。

圖1 甘肅人均生態足跡、人均生態承載力及生態赤字變化圖(2001-2010年)
3 結果分析
3.1 10年的變化趨勢分析
近10年來,甘肅總量生態足跡平均為6117.486萬hm2,人均生態足跡平均為2.383 hm2,人均生態承載力平均為1.119 hm2,人均生態盈余平均為 -1.264 hm2。其中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所占的比例最大,平均占人均生態足跡的46.747%和43.323%;其次是草地和林地,平均分別占人均生態足跡的8.391%和1.084%;水域平均人均生態足跡最低,只有0.168%,這說明受甘肅的地理位置和飲食習慣的影響,對水產品的需求很低。
甘肅的人均生態足跡在過去的10年間從1.89 hm2增長到2.90hm2,呈持續增長態勢(見圖1)。不同類型生態足跡比例也發生了變化(見圖2),其中耕地資源逐漸減少,而化石能源所占比例逐漸增至最大,接近50%,說明甘肅工業化進程中能源消耗大幅增加,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化石能源的消耗,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轉型和優化;草地生態足跡所占比例也有所增加,從7.316% 增長到9.432%;林地、水域和建設用地生態足跡很少,水域和建設用地更是微乎其微。生態赤字增加較快,甘肅2001年人均生態赤字為 0.422 hm2,2010年就增長為1.759 hm2,是2001年的4倍多,說明甘肅的生態環境處于不安全狀態。

圖2 甘肅不同生產性資源人均生態足跡變化趨勢(2001-2010年)
3.2 結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資源的利用效益分析
萬元GDP生態足跡反映了經濟發展與資源利用效率的關系。萬元GDP生態足跡大,則表明資源利用效率低,相反,萬元GDP生態足跡小,則表明資源利用效率高。過去10年來,甘肅萬元GDP生態足跡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迅速減少(見圖3),由2001年的4.537hm2/萬元降低到2010年的1.805hm2/萬元,由此可以看出,過去10年來甘肅的資源利用效率得到了迅速提高。
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消耗的關系可能會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使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處于倒U型曲線的右半部[15],而實現環境的生態安全也應該使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盡快平穩向右移動直至出現穩定下降,實現天人和諧的局面,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成為實現環境生態安全的有力保障,創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而實現這一路徑的首要任務就是加強科技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萬元GDP生態足跡。

圖3 甘肅萬元GDP生態足跡、人均GDP和人口變化圖(2001-2010年)
4 結論與建議
以甘肅為例,通過生態足跡模型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分析中國西北部地區的生態安全,由于近10年來,甘肅的生態足跡不斷增大,遠遠超出了生態承載力,生態赤字不斷增大,說明甘肅的環境處于不安全狀態。但萬元GDP生態足跡隨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大,說明甘肅的資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
雖然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說明了在發展與資源環境的普遍關系,為了實現倒“U”型曲線頂點的跨越,經濟的發展降低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萬元GDP生態足跡不斷減小,尋找這種變化的原因和動力至關重要。這種變化主要來源于內生動力、外生動力和輔助動力三個方面。內生動力主要指人們發展觀的變化和消費觀的變化;外生動力主要包括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輔助動力指人口增長率的減緩(見圖3)。
中國西北部地區的生態安全問題應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預警機制,即驅動力(driving forces)→資源環境壓力(press)→環境質量(environmental quality)→響應(response),簡稱為 DPER機制(見圖4)。內生動力、外生動力和輔助動力都歸結為驅動力,一種推動著工農業生產、城市建設和旅游交通運輸等領域的發展動力,對環境保護有利的驅動力為正向驅動力,反之為負驅動力,兩者之間的博弈將直接或間接地導致資源環境壓力的增減,從而影響環境質量,如果環境惡化,人類的生產環境受到影響,會迫使社會對上述因素的變化作出判斷并出臺相應的政策手段。但我們不能再受到負面影響時才作出反應,而是對影響驅動力的各個因素及時作出判斷和響應,通過調整發展觀念和消費觀念、發明新技術、尋找替代資源、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控制人口增長等措施減輕資源環境壓力。

圖4 DPER機制圖
經濟發展資源環境呈現倒U型的發展規律,但這并不表明我們可以先發展經濟,再治理環境。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要真正地實現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要實現中國西北地區的生態安全就應將DPER機制貫穿于經濟發展之中,注重其內生、外生和輔助動力,人口的壓力減輕能緩解人類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創新可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而發展觀和消費觀的轉變則規定了技術進步的方向。
[1]萊斯特·R·布朗.建設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4.
[2]孫儒泳主編.生態學進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周毅.中國生態環境安全[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68(2):1 -5.
[4]Norton S B,Rodier D J,Gentile J H,et al.A framework for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at the EPA[J].Environ Toxic Chemi,1992,11:1663-1672.
[5]潘玉君、袁斌.區域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上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6]王志強,張柏,于磊,等.吉林西部土地利用/覆被變化與濕地生態安全響應[J].干旱區研究,23(3):419-426.
[7]陳星,周成虎.生態安全:國內外研究綜述[J].地理科學進展,2005,24(6):8 -24.
[8]Rees W E.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J].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2,4(2):121-130.
[9]Wackernage L M,Rees W E.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M].Gabriola Island: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6.
[10]Wackernage L M,OnistoL,Bello P,et al.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J].Ecological E-conomics,1999,29:375 -390.
[11]劉宇輝,彭希哲.中國歷年生態足跡計算與發展可持續性評估[J].生態學報,2004,24(10):2257-2262.
[12]徐中民,張志強,程國棟.甘肅省1998年生態足跡計算與分析[J].地理學報,2000,55(5):607-616.
[13]張志強,徐中民,程國棟,等.中國西部12省(區市)的生態足跡[J].地理學報,2001,56(5):599-600.
[14]Wackernage L M,Onisto L,Bello P,et al.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Nations[M].Commissioned by the Earth Council for the Rio+5 Forum.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Toronto.1997.
[15]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著.發展的基礎—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資源、生態基礎評價[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