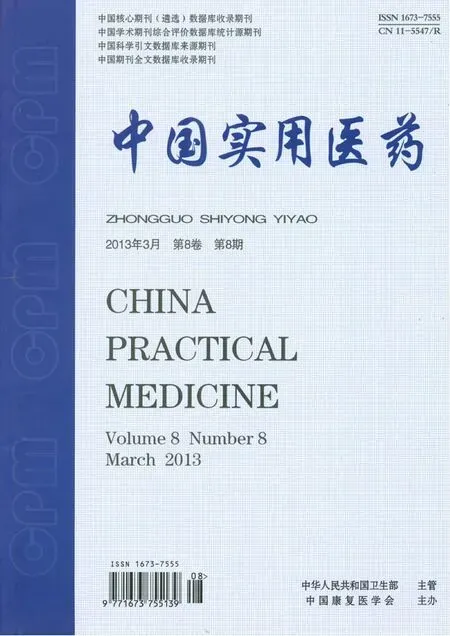炎癥性腸病的骨骼病變研究進展
羅澤香
炎癥性腸病(IBD)是一種病因尚不明確的慢性復發性胃腸道炎癥性疾病,包括潰瘍性結腸炎(lUC)和克隆病(CD)。IBD我國近十年來發病呈增加趨勢[1]。隨著對本病發病機制和病因學的深入研究,IBD的診斷和治療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同時對其在臨床上復雜的腸外病變表現及并發癥有了深刻的認識[2]。IBD腸外病變在發病學上具有病變累及范圍廣泛、變化不一、危害后果嚴重等特點,需要臨床醫師在接診IBD患者時引起高度重視并及時給予正確的診斷和治療[2]。
IBD患者中大約有有6%~36%表現為至少一種腸外病變表現(EIM)[4-6],主要分布在骨關節、皮膚、眼眶、口腔等部位,與活動性腸炎有關。部分患者則表現為膽石癥、腎結石和尿路梗阻、小腸功能紊亂等。骨關節損害和骨量減少、骨質疏松在炎癥性腸病的腸外表現中較為常見,本文對近年來IBD骨骼病變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骨關節病
骨關節病變是一種常見的EIM表現,其發病機制仍不十分清楚。可能與下列因素相關[6]:遺傳基因易感性、自身抗原表達異常及自體抗體形成、免疫復合物、細胞因子失衡、微生物感染等。
關節病變在EIM中發病率約為4%~23%,其中在潰瘍性結腸炎的發生率略低于在克隆氏病中的發生率,包括兩種類型:外周(非軸向性)和骶髂和脊柱(軸向性)關節病。臨床上排除其他特異性肌病、關節病變后才能作出本病的診斷。1.1 外周(非軸向性)關節病 外周(非軸向性)關節病可分為兩型(表1),1型表現為大關節的輕微病變,與IBD活動期有關,2型表現為多處小關節受累,與IBD是否處于活動期無相關性。

表1 IBD外周骨關節病變的特點
1.2 軸向性關節病 軸向性關節病主要包括骶髂關節炎和強直性脊柱炎,發病常先于炎癥性腸病癥狀或同時出現,其病程與炎癥性腸病不平行,男性較女性更為多見。骶髂關節炎可表現為休息時骨盆部位的疼痛,活動后緩解。患者雙側骨盆邊緣受壓時骶髂關節出現不適癥狀,這一現象具有一定的提示診斷意義。約一半以上的克隆氏病患者可以發生無癥狀性骶髂關節炎,但放射學檢查已有異常改變。強直性脊柱炎的主要癥狀是持續后背疼痛,多自30歲以后發病。臨床檢查表現為腰椎前凸消失,脊柱彎曲受限。常規腰背部放射檢查在早期并無異常發現,脊柱CT和放射性核素骨掃描較平掃更為敏感,但MRI檢查結果更具有診斷價值(金標準),即使在無癥狀的患者也可顯示病變。進展期病例中可以出現“方形椎體”、形成邊緣韌帶骨贅和骨化,使脊柱呈典型的“竹節樣”改變。雖然HLA B-27陽性與大多數軸向性關節炎發病相關,但在IBD無關性強直性脊柱炎患者中少見表達。
IBD相關性骨關節病的治療主要包括止痛、非甾體類抗炎藥、硫氮磺吡啶、局部皮質激素注射和理療等。
1型外周關節炎的治療重點在于抑制IBD活動性病變,包括使用皮質激素、免疫調節劑和TNF單抗等,可使病情得以緩解。治療2型關節炎的首選藥物為硫氮磺吡啶,非甾體類消炎藥(NSAIDs)、選擇性環氧化酶抑制劑、止痛藥、休息和理療等方法也可以緩解癥狀。使用NSAID類消炎藥物雖然有加重結腸炎的風險,但根據在臨床上大量應用的經驗來看對結腸炎復發的影響有限。局部注射激素內藥物常常能起到短期迅速緩解病情的效果。
對脊柱關節炎的治療方法包括加強理療并使用甲氨蝶呤和硫氮磺吡啶等藥物。藥物試驗表明,英夫利昔單抗是一種特異性阻斷TNF-α的人鼠嵌合型單克隆抗體,目前用于強直性脊柱炎的安全性和療效已被臨床研究所證實。
2 骨量減少和骨質疏松
骨量減少和骨質疏松在IBD患者常見,文獻報道的發生率不盡一致,約在15% ~50%之間。骨掃描測定T值<2.5時可診斷為骨質疏松。超聲檢查也可用于本病的篩查。IBD患者骨質疏松引起骨折的風險顯著增加,經常會發生脊柱自發性骨折,有時輕微外力作用即可引發骨折,但僅約1/3患者脊柱骨折有臨床癥狀。脊柱骨折的高危影響因素包括高齡、激素治療、吸煙、運動量減少(包括由于住院治療引起的運動減少)、炎癥因子,骨囊腫切除術等。
骨密度降低(T值<1.0)可能進展為骨質疏松癥。骨質疏松的治療方法包括負重和柔韌性訓練、戒煙和控制飲酒過度并保證鈣攝入1 g/d以上;激素替代治療由于存在輕度增高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對絕經期后女性患者不再建議使用。常規治療包括雙膦酸鹽、降鈣素及其衍生物、雷洛昔芬(一種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等,可用于減少骨鈣進一步流失。對男性患者可通過檢查血清睪丸激素的水平監測治療效果。
UC和CD是一種全身多系統疾病,病變部位以胃腸道為主,但也可以表現為多種腸外病變,骨骼病變是常見的臨床表現之一,已經成為嚴重影響IBD患者生存和生活質量的不良因素。對IBD骨關節目前尚無可靠的實驗室檢測標準,需要結合臨床癥狀、影像學改變并排除各種原發骨關節病之后才進行本病的診斷。對活動期IBD本病的治療是緩解骨骼病變的關鍵措施。TNF拮抗治療(英夫利昔單抗、阿達木單抗、塞妥珠單抗等)是一種能迅速緩解大多數IBD及其腸外病變的治療手段,除此之外,已有越來越多的不同劑型和藥理作用的新藥被用于臨床試驗研究,為提高IBD患者的治療提供更多的方案[7]。臨床醫生早期識別和診斷IBD相關的骨骼病變并聯合多學科合作,在診斷、藥物治療、預防藥物不良反應和康復護理等方面積極采取干預措施,對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和降低本病的總體病死率至關重要[2,4,8]。
[1] 冉志華,劉文忠.炎癥性腸病.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0,1:292-305.
[2] 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炎癥性腸病學組.炎癥性腸病診斷與治療的共識意見(2012年廣州)中華內科雜志,2012,51(10):818-831.
[3] Levine JS,Burakoff R.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Gastroenterol Hepatol(N Y),2011,7(4):235-41.
[4] Hamilton MJ,Snapper SB,Blumberg RS.Update on biologic pathway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their therapeutic relevance.J Gastroenterol,2012,47(1):1-8.
[5] Maloy KJ,Powrie F.Intestinal homeostasis and its breakdown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Nature,2011,15,474(7351):298-306.
[6] Lakatos PL,Lakatos L,Kiss LS,et al.Treatment of 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Digestion,2012,86 Suppl 1:28-35.
[7] Triantafillidis JK,Merikas E,Georgopoulos F.Current and emerging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Drug Des Devel Ther,2011,5:185-210.
[8] Stallmach A,Hagel S,Bruns T.Adverse effects of biologics used for treating IBD.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2010,24(2):16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