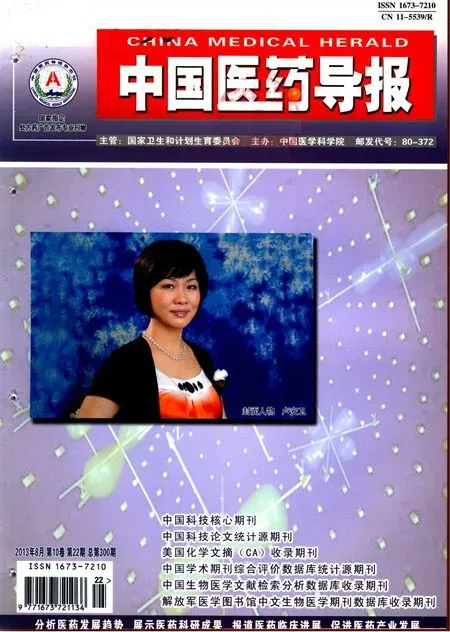腸寧方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臨床觀察
潘寧平 廖 進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中醫醫院,廣西桂林 541002
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種常見的腸道功能紊亂性疾病,其分為腹瀉型、便秘型、腹瀉便秘交替型。據報道[1],兩廣地區的IBS患者中多以腹瀉型為主,占整個IBS發病率的74.1%。腹瀉型IBS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加重了患者的身心壓力。桂林市中醫醫院(以下簡稱“我院”)采用協定方劑腸寧方治療腹瀉型IBS,經過多年的臨床實踐,有良好的治療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診斷標準
1.1.1 西醫診斷標準 參照羅馬Ⅲ診斷標準[2]診斷前出現癥狀至少有6個月,就診之前3個月內,每個月至少有3 d出現反復腹痛或不適癥狀,且必須符合:水樣便或稀便所占比例≥25%,塊狀便或硬便所占比例<25%。并同時具備下列中的2項或2項以上:①伴隨排便頻率的改變(≥3次/d);②排便后癥狀緩解;③伴隨糞便性狀的改變(水樣便或糊狀便)。
1.1.2 中醫診斷標準 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3]和根據中華中醫藥學會脾胃病分會發布《腸易激綜合征中醫診療共識意見》[4]擬定,分為脾虛濕阻證、肝郁脾虛證、脾腎陽虛證、脾胃濕熱證4種證型,即:①脾虛濕阻證。主癥:大便時溏時瀉,腹痛隱隱。次癥:勞累或受涼后發作或加重,神疲納呆,四肢倦怠,舌淡,邊有齒痕,苔白膩,脈虛弱。證候確定:主癥必備,加次癥兩項以上即可診斷。②肝郁脾虛證。主癥:腹痛即瀉,瀉后痛減,發作常和情緒有關,急躁易怒,善嘆息。次癥:兩脅脹滿,納少泛惡,脈弦細,舌淡胖,有齒痕。③脾腎陽虛證。主癥:晨起腹痛即瀉,腹部冷痛,得溫痛減,形寒肢冷。次癥:腰膝酸軟,不思飲食,舌淡胖,苔白滑,脈沉細。④脾胃濕熱證。主癥:腹痛瀉泄,泄下急迫或不爽,肛門灼熱。次癥:胸悶不舒,煩渴引飲,口干口苦,舌紅,苔黃膩,脈滑數。
1.2 納入標準
①符合羅馬Ⅲ診斷標準,且為腹瀉型IBS,同時符合中醫診斷標準中脾虛濕阻、肝郁脾虛、脾腎陽虛、脾胃濕熱4種證型之一;②經過結腸鏡或鋇劑灌腸檢查證實無腸道器質性病變;③肝腎功能、血尿常規檢查屬正常范圍;④自愿作為受試對象,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排除標準
①不符合腹瀉型IBS;②排除慢性腸胃炎、潰瘍性腸炎、外腸道腫瘤、類癌綜合征等疾病引起的腹瀉;③妊娠或哺乳期婦女;④合并有腦、肝、腎和造血系統等嚴重原發疾病、精神病患者;⑤過敏體質或對多種藥物過敏者。
1.4 一般資料
觀察病例均來自2008年7月~2012年12月我院門診患者,共75例,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38例,男21例,女 17 例;平均年齡(38.66±10.50)歲;病程 10 個月~13 年;其中脾虛濕阻證9例,肝郁脾虛證10例,脾腎陽虛證10例,脾胃濕熱證8例。對照組37例,男17例,女20例;平均年齡(36.08±12.36)歲;病程 1.5~17 年;其中脾虛濕阻證 10 例,肝郁脾虛證8例,脾腎陽虛證11例,脾胃濕熱證9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方案經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1.5 治療方法
1.5.1 治療組 以腸寧方治療(我院協定處方,由制劑室提供,農本方由南寧培力藥業有限公司生產)。處方:黃芪15 g、黨參 12 g、茯苓 12 g、白術(炒)10 g、山藥(炒)15 g、肉桂 6 g、補骨脂 9 g、延胡索 10 g、白芍 10 g、木香 12 g、赤石脂(煅)9 g、甘草(炙)15 g。1劑/d,水煎 400 mL,分早晚 2次服用,每次200 mL,溫服。1周為1個療程,共3個療程。觀察期間停服其他治療胃腸道的藥物。
1.5.2 對照組 水口服匹維溴銨(法國蘇威制藥廠生產),50 mg/次,3次/d。療程3周。
1.6 觀察指標
1.6.1 中醫證候觀察 大便次數、大便性狀、腹痛、腹脹、排便不盡感、黏液便、舌象、脈象等中醫證候。癥狀分級量化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的標準修訂[2],分為無癥狀、輕、中、重 4 級,分別計 0、1、2、3 分。
1.6.2 實驗室指標 采用放射免疫法在治療前、治療后測定患者血清中5-羥色胺(5-HT)及胃動素(MOT)水平。
1.7 療效判定標準
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①臨床痊愈:臨床痊愈泄瀉癥狀消失,大便成形,每日1~2次,中醫證候的主癥、次癥消失,舌苔基本恢復正常,證候積分減少>95%。②顯效:大便次數每日2~3次,近似成形,或便溏每日僅1次,中醫證候的主癥、次癥改善程度在2級以上,證候積分減少>70%。③有效:大便次數和質、中醫證候的主癥、次癥均有好轉,證候積分減少>30%。④無效:癥狀、體征均無明顯改善,甚或加重,證候積分減少不足30%。總有效率=(臨床痊愈例數+顯效例數+有效例數)/總例數×100%。癥狀療效、證型療效標準根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的標準修訂的癥狀分級量化標準擬定。
1.8 統計學方法
用SPSS 16.0軟件進行統計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不同時間點數據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給藥治療3周后,治療組臨床痊愈為47.4%,總有效率為92.1%,對照組分別為24.3%和81.1%。兩組比較,治療組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
2.2 兩組中醫證候總積分比較
經過3周治療后,治療組的中醫證候總積分為(8.52±3.43)分,而對照組為(13.01±2.50)分,兩組中醫證候都得到比較大的改善(P<0.01),兩組間比較,治療組中醫證候改善優于對照組(P<0.01)。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總積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總積分比較(分,±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1;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P<0.01
對照組治療組37 38 19.54±4.02 18.82±3.22 13.01±2.50*8.52±3.43*#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后
2.3 兩組各中醫證型療效比較
兩組各中醫證型總有效率比較,治療組的總有效率好于對照組,其中脾虛濕阻證、肝郁脾虛證、脾胃濕熱證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脾胃濕熱證兩組療效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4 兩組5-HT、MOT變化比較
兩組在治療后,血清中5-HT、MOT的水平顯著降低(P<0.05),表明治療組和對照都能降低5-HT、MOT表達。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降低5-HT、MOT水平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4。
3 討論
腹瀉型IBS由多種因素誘發,目前多數認為與胃腸動力異常、內臟感覺異常、腦-腸軸改變、情緒焦慮抑郁、細菌感染等有關,有研究表明,5-HT、MOT在體內水平與腹瀉型IBS具有密切的關系[5-6]。特別是5-HT內臟感覺異常、腦-腸軸改變、情緒焦慮抑郁密切相關[7],近年來的臨床和基礎研究發現,選擇性5-HT可通過改變IBS患者內臟痛覺傳入神經及胃腸道轉運時間等機制改善患者的腸道功能及精神心理癥狀,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8]。5-HT是腦腸神經遞質大家族中的一種,參與人體多種生理功能。在腸道,不僅調節腸道動力、感覺和分泌功能,同時還是痛覺傳導系統中的重要調節物質;在中樞神經系統,與心理異常有重要關系。5-HT合成、釋放、與相應受體結合以及重攝取等信號轉導系統中任何環節的異常均可導致胃腸道動力及分泌功能異常和內臟高敏感性的產生。有研究表明[9],腹瀉型IBS患者活動期血漿5-HT含量明顯高于緩解期,而緩解期血漿S-HT含量仍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血漿5-HT水平與IBS病情程度呈正相關。MOT為多膚,由22個氛基酸組成,其在腹瀉型IBS發生過程中,也起到非常重要作用。MOT升高可引起奧狄括約肌及膽囊收縮,結腸運動與十二指腸運動加強[10],從而使水電解質通過腸道時間縮短,導致了腹痛、腹瀉癥狀的產生。這與腹瀉型IBS患者出現的腹痛、腹瀉癥狀相一致。多數研究發現[11-12],IBS-D患者空腹血漿胃動素濃度統計學意義升高,表明血漿MOT升高可能是腹瀉型IBS發病因素之一,它也能作為評價藥物療效的客觀指標應用于臨床。本研究也表明,腸寧方能有效地抑制腹瀉型IBS患者體內的5-HT、MOT,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1),這可能是腸寧方治療腹瀉型IBS的作用機制之一。

表3 兩組各中醫證型療效比較(例)
表4 兩組 5-HT、MOT變化比較(±s)

表4 兩組 5-HT、MOT變化比較(±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P<0.01;與對照組比較,#P<0.05,##P<0.01;5-HT:5-羥色胺;MOT:胃動素
對照組(n=37)5-HT(μg/L)MOT(ng/L)治療組(n=38)5-HT(μg/L)MOT(ng/L)528.9±63.6 367.4±27.4 540.6±48.0 356.1±30.5 433.4±72.6*240.1±11.8**314.1±60.7**##203.1±22.4**#組別 治療前 治療后
中醫無“IBS”之病名,其屬于“泄瀉”“腹痛”“郁證”之癥。其初多為肝脾不和,氣滯致脾虛,久則可引起疲、濕、痰等病因,繼而出現虛實夾雜、寒熱錯雜等病機,病久及體弱年老多以脾胃虛弱,脾腎陽虛為主。特別是腹瀉型IBS,泄瀉之本在于脾,多以脾虛為主,而脾腎關系密切,脾為生氣之源,腎為生氣之根,氣來源于脾腎。脾為后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脾主運化水谷精微,脾之健運,化生精微,須借助于腎陽的溫煦,治療上還應補腎。腸寧方由黃芪、黨參、茯苓、白術、山藥、肉桂、補骨脂、白芍、延胡索、木香、赤石脂、甘草。方中黃芪能補脾益氣,用于氣虛乏力、食少便溏、中氣下陷、久瀉脫肛、氣虛水腫等癥;黨參具有補養中氣、調和脾胃之功效;茯苓具有利水消腫、滲濕、健脾、寧心之功效;白術具有健脾益氣、燥濕利水、開胃、去痰涎、除寒熱、止下泄之功效;山藥具有補脾養胃、生津益肺、補腎澀精之功效;木香具有理氣止痛之功效;延胡索具有活血、利氣、止痛之功效;白芍具有肝火、酸斂逆氣、緩中而止痛之功效;肉桂具有溫中散寒、補脾腎之功效;補骨脂具有補腎助陽之功效;赤石脂固澀下焦,煅用更增其止瀉、止血之功;甘草具有補脾益氣、緩急止痛、調和諸藥、清熱解毒之功效。方中人參黃芪、黨參、茯苓、白術健脾胃滲濕為君藥;配以山藥助其以健脾益氣,兼能止瀉,為臣藥;肉桂、補骨脂溫補脾腎,白芍、延胡索調和氣血,止痛;木香行氣散結,散寒止痛;赤石脂固澀下焦,煅用更增其止瀉、止血之功,以上均為佐藥,甘草緩急,調和諸藥為使。綜觀全方,補中氣,滲濕濁,行氣滯,使脾氣健運,濕邪得化,水谷精微生化恢復,則諸癥自除。
本研究對腸寧方的臨床療效表明,腸寧方可有效改善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的臨床癥狀,其作用機制可能與調節患者體內的5-HT、MOT水平表達有關,而其是否還有其他的機制,還需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1]熊理守.廣東省腸易激綜合征的流行病學調查[J].Chinese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2003,8(6):11-12.
[2]Drossman DA.The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sand the RomeⅢ process[J].Gastroenterology,2006,130(5):1377-1390.
[3]鄭筱萸.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336.
[4]中華中醫藥學會脾胃病分會.腸易激綜合征中醫診療共識意見[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0,25(7):1062.
[5]梁榮新,鄭琴芳,梁列新,等.腸易激綜合征與胃腸激素的關系[J].中國綜合臨床,2004,20(8):702-703.
[6]唐洪梅,房財富,廖小紅,等.神經膚Y和5-羥色胺在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模型大鼠中表達的研究[J].中國藥理學通報,2012,(7):916-920.
[7]張麗妍,陳勝良.5-羥色胺與腸易激綜合征的內臟高敏感性[J].胃腸病學,2009,(8):502-504.
[8]賴瑞敏,曹立穎,喬麗娜,等.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治療腸易激綜合征療效的系統評價[J].世界華人消化雜志,2012,20(22):2106-2110.
[9]黃適,林壽寧,談馳,等.安腸湯結腸水療對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血漿胃動素和 P物質的影響[J].遼寧中醫雜志,2009,36(7):1150-1151.
[10]費曉燕,謝建群,鄭昱,等.疏肝飲對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模型大鼠胃動素和膽囊收縮素的影響[J].上海中醫藥雜志,2008,42(4):63-65.
[11]張超,王景杰,盧王,等.失眠伴便秘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睡眠特征及胃動素、生長抑素的臨床觀察[J].胃腸病學和肝病學雜志,2009,18(8):735-737.
[12]張志雄,鄭琴芳,梁榮新,等.腸易激綜合征乙狀結腸移行性運動與胃腸肽膽囊收縮素、胃動素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實用內科雜志,2006,26(18):1427-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