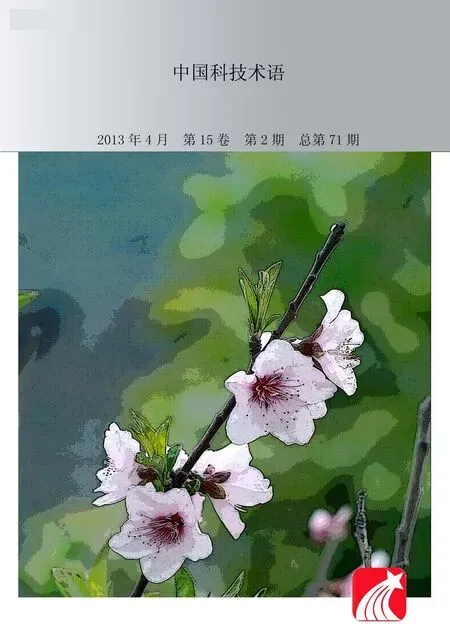淺論術語學是知識技術的前提
邱碧華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北京 100717)
引言
在科技領域中,知識以及作為知識單位的概念日益增加。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人們更好地進行知識描述和進行有效的知識傳遞提供了更多的啟發,也加速了信息流的進程,在空間上使信息得到了擴展。就信息而言,根本問題不是存在的信息太多了,而是對信息流秩序的研究太少了[1]。
梳理知識,是在所有領域中進行規范化知識傳遞的基礎,實際上也是在所有領域里開展合作的根本前提。梳理知識并不直接涉及知識的內容,而是與儲存和管理知識密切相關。
在文獻學、圖書館學、語言學、信息學等學科中,術語學和知識技術處于中心地位,這兩門學科的結合構成了所謂“知識和技術的智力基礎設施”[2]。盡管術語學最初是一門與計算機科學和信息技術相脫離的、獨立發展的學科,知識技術也是從人們對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誕生的(知識工程),但這兩門學科在實踐中相互補償、吸收、適應和逐漸一體化,促使人們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術語學的發展,已經從以語言學或者符號學為導向的靜態理念,發展到了以認知理論和科學理論為導向的認識階段,更多強調動態的特色。術語學和知識技術這兩個領域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完成梳理知識的工作。通過這種工作,知識在積累過程中才可能井然有序,并且具有流動性[2]。
一 受控制的概念動力學產生的必然性
每一個知識領域都是由概念組成的,這些概念都是依照嚴格確定的規則而相互聯系成一個系統。主觀上,概念是“思想要素”,也是“精神結構”(mentale Konstrukte),它們是主體間為了進行交流而借助語言符號或者非語言符號得以描述的。概念的每一種描述,都思味著某種概念的確定或者標準化;某個確定的符號或者符號復合體,也由此對應到一個與某些確定的對象客體、過程或者事實情況(事態)有關的精神結構上了。在自然的標準語言中,一個詞的含義是受語境或者上下文的制約而得以標準化的。歐根·維斯特把這樣由約定俗成的語言習慣確定的對應關系稱為“是-對應關系”(Ist-Zuordnung)[3]。一個可確定界限的系統化知識領域,無論是在科學理論領域還是實踐領域,或者技術領域,都需要標準化術語的存在。所謂的“標準化”,就是不斷要在“狀態”和“準則”之間進行區分,也就是要在“是-對應關系”(Ist-Zuordnung)和“應該-對應關系”(Soll-Zuordnung)之間進行區分。術語標準化的工作,不是限制人們只是做確定“什么是”(Was ist)的工作,而是它要將概念和概念系統在國家和國際水平上進行協調統一,要在命名系統中對名稱進行確定。這個命名系統要代表一個特定專業學科的獨立概念系統。
在術語學發展史上,存在過兩種術語學研究方向:
1.基于專業學科(如:化學、醫學、物理、科學技術等)的術語學研究(概念處于這種研究方法的核心地位);
2.基于語言學的術語學研究(名稱處于這種研究方法的核心地位)。
這兩種研究方向都有其時代局限性。術語學實踐表明,二者需要相互結合。
從歐根·維斯特創立的普通術語學誕生起,就強調在國際水平上開展工作,注重國際化的理念[4]。基于這種理念,建立與具體專業領域相關,又配有多種語言的術語數據庫是必然的。在術語數據庫中,每一種語言都既可以作為起始語言,也可以作為目標語言。歐洲認知科學等研究成果表明,維斯特把概念作為“思想單位”的理念是正確的;但是,他的四部分詞語模型已不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需要進一步轉換成一個動態的動力學概念模型,才可能更好地對概念進行描述;維斯特所強調的對概念進行“共時性”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拓展成“歷時性”的研究方法,過去人們對術語靜態的、只考慮暫時情況的研究,需要轉變成一種“受控制的概念動力學”的動態、長久的研究方法[5]。
二 維斯特概念模型的動力學轉型
在基于語言學的術語學研究中,人們偏愛使用三部分詞語模型,維斯特適應術語學理論發展的需要,將其發展成了四部分詞語模型[3]。
20 世紀70 年代在歐洲出現的C.A.彼得里(C.A.Petri)的普通網絡學理論[6],主張對現實世界中的系統和過程進行描述、分析和綜合。主張在信息系統中,首先要對在時空中存在的系統內的信息流進行描述、計劃和組織,而先不考慮這些信息流與人類或者機器是否相關。這種理論與維斯特的普通術語學很適合,因為從實踐中得來的科學概念體系,運用C.A.彼得里的普通網絡學理論中最基本的觀點,是可以描述其過程的動態特點的。
維斯特的“名稱”和“含義”這兩個標識,可以作為運用彼得里的普通網絡學理論的載體要素。在共時性的普通術語學研究中,人們只是在一個靜態的時間點上確定概念的名稱,而就歷時性的普通術語學研究方法而言,需要人們把對概念名稱進行標準化過程,與隨著科技發展而變化著的含義進行動態對應。如果在維斯特的四部分詞語模型中,加上作為表示流動關系的線性箭頭,這就得到了維斯特概念模型的動力學轉型,過去所有靜止的關系都分解成了動態的過程,這是從彼得里普通網絡學理論的基本系統模型(條件/事件系統)中得到的啟發。
把維斯特四部分詞語模型的各部分標上數字,不違背維斯特的初衷,得到圖1 所示的過程順序:

圖1 維斯特概念模型的動力學轉型
區域1:某確定知識領域的可能對象客體世界;它本身只是重復描述無限宇宙的一個片段。但是在表面上,這些對象客體僅僅作為“精神結構”,在可覺察的事件里出現。
區域2:概念的世界;在其中,特征給抽象濃縮成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單位。
區域3:理想符號世界;作為概念的思想單位與之對應。
區域4:理想符號的現實世界;它給分解成若干種可能性,在技術系統中,運用人類使用的會話符號和書寫符號,描述其存在的現實性。
這四部分的過程是可重復的。在現實當中,這個過程也是經常重復的,這就得到了一個受控制的概念動力學過程,它允許知識的增長和概念的變化遵循一定的規律。在實踐中,概念的發展是自由的;但在此基礎上,是可以為對術語進行標準化,找到一個合適的時間點的[5]。受控的概念動力學不是限制了術語學工作的開展,而是挖掘了術語學的潛力,因為靜止的永久性的對應關系是不存在的。
三 術語學和知識技術的一體化
如前所述,術語學和知識技術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兩個領域,但是,它們一直呈現出相互靠近和會聚的趨勢。普通術語學是受具體專業制約的,術語學和知識技術一體化成一個統一和實用的體系具有其必然性。
知識庫的建立是以概念為基礎的,而概念若要表述得清晰,則必須通過術語的協調工作才能實現;術語是所有知識技術發展和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使從組織變化所具有的內在邏輯性上看,術語學也是規范化的知識產生、知識獲取、知識代表和知識傳遞過程啟動的前提。知識技術的每一個領域,也是和系統化術語工作的某一領域相對應的(見圖2):

圖2 術語學和知識技術的一體化模型
概念的建立是獲取知識的前提;
術語規范的知識領域,是借助專家系統獲取知識的前提;
立足于概念關系系統的知識領域,其分類方法和方法論,是進行知識代表過程和理順知識秩序的前提;
為協調術語工作而制定的國家、國際化的普遍性基本原則,是知識傳遞的前提。
術語學和知識技術一體化的模型不具有靜態的層級關系,它創立的是一種相互作用的依賴關系。正如術語學界有一句名言所說:沒有直觀形象(或者觀念)的概念是空泛的,沒有概念的直觀形象(或者觀念)是盲目的。我們也可以說:沒有知識技術的術語學是空泛的,而沒有術語的知識技術是盲目的。
四 結語
術語學的發展是科學技術進步的必然前提。近年來,中國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誕生了很多相關著作,比如馮志偉先生的《現代術語學引論(增訂本)》[7],以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術語學建設書系。同時,已經建立了一些基于術語的本體知識系統,利用這樣的本體知識系統來控制知識工程的開發。術語標準化工作如果不為實際的知識技術服務,它就會成為豪無思義的“緊身衣”而束縛知識的發展。只有借助現代的信息技術手段,才可能為改善人類的知識交流提供科學便捷的幫助。
筆者將在隨后的幾篇文章中,對當今世界術語學發展情況做一粗淺的比較性介紹,以期為了解和發展術語學理論提供一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