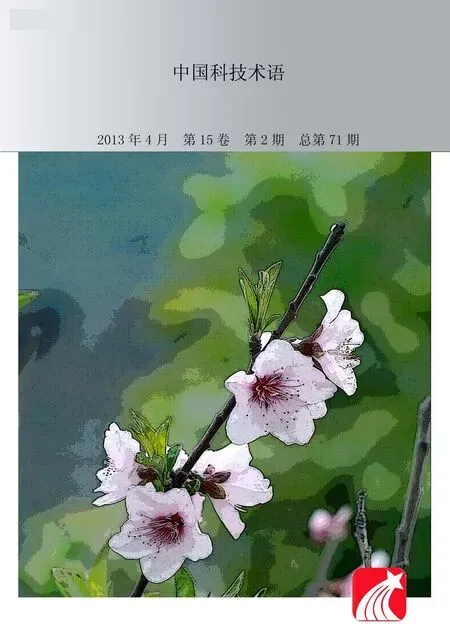中醫藥名詞英文翻譯與規范原則關系的探討
洪 梅 朱建平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北京 100700)
引言
隨著中國國力日漸強盛,中醫藥名詞的國際標準化工作引起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重視,ISO/TC249 中醫技術委員會秘書處落戶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掛靠于我國上海市中醫藥研究院。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疾病分類第11 版(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ICD-11)的制定將中醫藥內容納人計劃。此外,還有WHO西太平洋地區(WHO Western Pacific Region,WHOWPR)組織編寫的《傳統醫學名詞國際標準》,而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WFCMS)組織編寫的《中醫基本名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國家標準委組織編寫了GB/T 20348—2006 中醫基礎理論術語、GB/T 12346—2006 腧穴名稱與定位等國家標準術語。這些中醫藥名詞的規范工作成為中醫藥走向世界的橋梁之一。
中醫藥名詞中英雙語的規范工作,離不開術語學工作原則的指導。由于中醫藥名詞規范工作的時間較短,有關經驗不足,理論探討更嫌薄弱,目前還沒有區分中醫藥名詞英譯原則和英文名的規范原則的討論。規范原則是隨著術語英譯的逐漸成熟和術語規范工作的開展升華而得。本文思在討論適合中醫藥名詞英文名規范的通則框架,并將之與中醫藥名詞英文翻譯原則區分。
一 中國中醫藥名詞規范工作介紹
(一)組織機構及指導文件
國家層面的中醫藥名詞規范工作,目前主要由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簡稱全國科技名詞委)和國家標準委兩個單位執行。兩個單位各有一套指導進行術語規范工作的文件,主要內容大致相同。全國科技名詞委起源于民國時期的“科學名詞審查會”,1985 年“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成立,1996 年更名為“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所制定“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原則及方法”規范符合中國國情,強調了制定術語時要注思定名時的“民族性”[1]。國家標準委文件多根據ISO術語工作相關標準翻譯并結合中國國情略做修改,與術語規范工作相關文件主要有:GB/T 20001.1—2001標準編寫規則 第1 部分:術語;GB/T 10112—1999術語工作 原則與方法;GB/T 15237—2000 術語工作 詞匯 第1 部分:理論與應用;GB/T 16785—1997 術語工作 概念與術語的協調。中醫藥名詞雙語規范原則主要在術語學理論與方法指導下,根據以上工作文件,并綜合分析中醫藥名詞特點的基礎上進行制定。
(二)中醫藥雙語術語規范工作
中醫藥學名詞(TCM terms)是中醫藥領域中中醫藥概念的語言指稱,即中醫藥概念在漢語或其他語言中的名稱。中醫藥名詞規范工作就是根據預先確定的命名規則,系統建成規范的中醫藥系統術語集(TCM nomenclature)。中醫藥中英雙語術語工作就是利用等義現象(equivalence)在英語中尋找到中文中醫藥名詞的等義術語(equivalent term)。
中醫藥名詞的英譯與其他自然科學術語不同,漢語是源語言,英語是目的語,翻譯方向是從中文向英文。很多名詞都具有悠久的歷史,深具人文性[2],其含義有著復雜的演變過程,在英文中找不到對等詞。中醫藥名詞需要通過翻譯創造對等詞。這項工作已經有很多人進行嘗試,由于個人理解和方法論的差異,一個術語存在多種英譯。目前,中醫藥雙語術語規范工作是在中文術語規范工作的基礎上對中文術語已有的英文名進行規范。
隨著中醫藥國際影響力增加,中醫翻譯由零星的個別實踐到出版社組織的大規模翻譯,翻譯隊伍從以國外為主到以國內為主,又到國內外平分秋色。翻譯情況從各說各話到激烈的學術爭論,從拉丁化到推崇普通用詞,從混亂開始邁向統一。多年來,對于術語英譯原則,學術界觀點既有趨同,也存在爭議。
二 關于中醫藥名詞英譯原則的討論
(一)譯者因素
中醫藥名詞的翻譯、翻譯原則的制定受譯者的主觀因素影響較大,與譯者的知識背景、文化背景、職業背景有關。這就導致術語英譯指導思想,所制定翻譯原則、所使用的翻譯方法的多樣化。目前主要是以西方語言學家魏迺杰(Nigel Wiseman)、文樹德(Paul U.Unschuld)為代表的“以原文為導向”的異化法和以醫藥學專家謝竹藩、班康德(Daniel Bensky)“以讀者為導向”的歸化法并存的情況。二者各有優劣之處。翻譯方法不同導致所譯出術語差異極大,使用混亂,難以統一。
(二)英譯原則之爭
2000 年進人術語標準編制階段,科技部《中醫藥基本名詞規范化研究》項目成果《中醫藥學名詞》(2004)應用的中醫藥名詞英譯原則共有六條:對應性、系統性、簡潔性、同一性、回譯性、約定俗成。并提出中醫藥名詞的英譯既要反映中醫的本思,又要符合英語國家的語言習慣[3]。這些原則成為其他中醫藥名詞英譯標準制定的參考。世界中醫藥學聯合會《中醫基本名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的英譯原則在制定過程中,經多次會議探討,反對回譯性原則,強調對應性原則,共四條:對應性、簡潔性、同一性及約定俗成等原則[4]。認為直譯是手段不是原則。
魏迺杰認為中醫名詞英譯最基本的問題在于是否需要固定的英文對應詞。在英譯方法的選擇上,最根本的爭論在于是否需要系統化的英譯原則。制定專有名詞最有效率的方法是先決定一套適用于所有名詞的英譯原則,亦決定每一類名詞所使用的翻譯方法。他強調回譯性原則及直譯法[5]。
一直以來,馬萬里(Maciocia)、班康德及其同事認為中醫術語多為一般中國人所了解,不能視之為“專有名詞”。因此,根據不同語境可采用不同的英譯詞。他們認為許多中醫名詞具多義性,難以翻譯,而且不同翻譯人員所采用不同的譯詞能使讀者理解術語不同方面的概念。強調翻譯的“清晰性與可讀性”[6],反對字對字的直譯法。
(三)國際標準英文名規范原則
目前WFCMS 的標準和WHOWPR的標準分別組織公布了自己的中醫藥名詞國際標準。
WFCMS 直接提出了術語英譯原則:
(1)對應性:英譯詞義盡量與其中文學術內涵相對應,是最重要的原則;
(2)簡潔性:在不影響清晰度的前提下,譯名越簡單越好,避免辭典式釋義;
(3)同一性:同一概念的名詞只用同一詞對譯;
(4)約定俗成:目前已通行的譯名,與上述原則雖然不完全符合,仍可考慮采用。[5]
在分類英譯中,穴位名、中藥名、方名的英譯將拉丁化漢語拼音作為第一標準。在原則中沒有概括這一做法的根據。
WHOWPR沒有強調英譯原則,而是提出了篩選英文名的原則:
(1)準確反映中文術語的原始概念。這一點同中醫藥名詞委和WFCMS 的英譯原則“對應性”原則本質是相同的。
(2)不創造新的英文詞匯。強調從已有字典中選取英譯,不另行創造新的英譯,但可在語法層面改譯。
(3)避免使用拼音。這一點與WFCMS 的標準有著明顯的分歧。
(4)與WHOWPR針灸術語標準保持一致。強調了術語的延續性,一些明顯的學術錯誤,如將“臟腑”譯為“viscera and bowels”,也被繼承了下來[7]。
(四)現有術語英譯原則缺點
WFCMS 雖然提到了專有名詞用漢語拼音作為第一標準,并在翻譯方法中提到了用雙譯法、三譯法處理相關類型的術語,但是沒有提到所依據的原則是民族性。從表1 瘤類疾病的翻譯看,WHOWPR的選擇照顧了中醫術語的系統性,但是,也沒有在原則中體現出來,而且,由于其與西醫疾病一對一的關系沒有體現出來,不便于臨床使用,沒有全面傳遞其醫學內容。WHOWPR及WFCMS 對規范術語學工作及中醫藥名詞原則多考慮語言層面,民族文化層面考慮不足。
三 術語翻譯與術語規范的關系
一定翻譯原則指導下的術語翻譯是術語規范的工作基礎。中醫藥名詞英文名的規范原則需要將翻譯原則考慮進去,并制約、指導翻譯原則的選擇和使用。
一般情況下,術語包括英文術語的規范應該是在收集到已有的英文術語中,由權威機構組織領域內專家,按照規范術語工作方法選出規范術語。規范過程一般不需要再創新術語,也同樣不需要重新英譯術語。
但是,中醫藥名詞與西醫及其他自然科學技術術語不同在于,她是中國本土科學的外傳,很多術語在英語中根本沒有對應詞,只能采用一定的翻譯手段進行仿造。這導致中醫藥名詞規范必然涉及翻譯的問題。在規范過程中,雖然可以使用已有的翻譯,但是,由于翻譯方法的不同,一個術語可以有多達10 余種譯法。那么哪一種能作為標準呢?
這就需要綜合各種因素,制定用來篩選或改譯中醫藥名詞英文名的規范原則。此原則還將指導沒有英譯中醫藥名詞的翻譯。
四 中醫藥名詞英文名規范原則的制定
中醫藥名詞英譯的規范原則既要考慮到規范術語學工作的基本原則,還要照顧中醫藥名詞自身的特點及需要翻譯介人的特殊性。
(一)需要照顧術語規范的原則
1.對應性
術語的譯名詞義與中文相對應。即譯名要符合中醫術語的原思,所選英文術語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中醫術語內涵。這是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制約著其他原則。
2.系統性
保證中醫藥學科概念體系的完整性。術語是概念的指稱。中醫藥理論自成體系,在翻譯的時候,除了照顧中西醫術語的對應關系,還要照顧到中醫藥學術體系本身的系統性。相同系列的上位概念術語和下位概念術語應該有母子關系。例如疾病名稱的翻譯,必要時采用雙譯法,中醫特色譯名在前,西醫病名在后,以同時達到傳達中醫文化和醫學科學內容(見表1)。

表1 外科術語“瘤”及其下位概念術語的英譯
3.同一性
同一概念的名詞只用同一詞對譯。由于中醫藥名詞的民族性,文化承載詞及病名可以采用多譯法。理想的話,同一概念中文術語只用一個英文術語表達,即達到一詞一義的單義性,事實上很難達到。因為源語言是漢語的傳統中醫藥名詞要找到英文功能對等詞往往是很困難的,所以,很多需要采用雙譯法和多譯法來實現雙語信息的準確傳達。例如基礎名詞“髓海”(marrow of sea;brain),病名“氣瘤”(qi tumor;subcutaneous neurofibroma),采用中醫傳統術語直譯在前、西醫譯名思譯在后的雙譯法來傳達中醫術語和西醫術語的對應。
4.簡潔性
譯名要簡潔,不是辭典釋義,用詞不能太長。早期很多術語的音譯采用解釋性翻譯,借用西醫術語表達中醫概念,以幫助英文讀者理解中醫術語的內涵。如“十二經脈vascular system consists of 12 Pairs of main vessels”[8]。這是一個階段性的現象。隨著中醫藥的國際化,術語的英譯逐漸由繁復向簡約過渡,由歸化為主轉向異化為主,如“十二經脈twelve channels/meridians”。
5.約定俗成
目前已通行的譯名,與前述原則雖然不完全符合,仍可考慮采用。對于存在明顯學術錯誤的不予采納,如臟腑viscera and bowels的翻譯。
(二)需要照顧英譯的原則
回譯性:譯名結構在形式上與中文一致或相近。
名詞定語和連接符“hyPhen”的使用,使中醫藥名詞的英譯越來越簡潔,回譯性也越來越強。面對國際中醫藥領域雙向交流的需要,保證其他原則的前提下,回譯性可以使所得譯名形神兼顧,不可忽略。例如“肝腎陰虛”早期多譯為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現在多譯為liver-kidney yin deficiency。
(三)照顧文化承載詞
民族性:選擇規范譯名時,應考慮中醫藥名詞的中國文化特色。
既要保證中醫藥術語作為醫學科學術語的準確性,又要照顧其社會人文科學的歷史性、人文性。因此,我們采取的策略有二:一是專有名詞采用拉丁化拼音作為第一標準。如方劑及中成藥名稱、中藥名及針灸腧穴名稱采用音譯作為第一標準。還有人名、書名、地名、部分基礎名詞及病名也采用音譯。二是為了盡量反映中醫藥名詞的人文特色,不少術語采用雙譯法或多譯法。例如,氣瘤(qi tumor;subcutaneous neurofibroma),髓海(marrow sea;brain)。
總之,目的是力求既方便雙向的信息交流,又能較為準確傳達中醫藥原思,盡量達到功能對等,使外國人能從自然科學和社會人文科學全方位地了解和學習中醫藥學。
(四)與國際/國家標準的統一
由于中醫藥術語國際規范工作時間尚短,理論指導欠缺,所選術語也在試用階段,需要在使用中不斷修訂,對于國際標準WHOWPR的術語標準,針灸命名標準中很多不合理的英譯因照顧延續性而被延續下來,如五臟five viscus、六腑six bowls,這種翻譯一直不被多數學者接受。新的學術觀點傾向于使用“漢語拼音+思譯″,如五臟five zang organs/viscera、六腑six fu organs/viscera。對于國際標準,正確的自當接受,錯誤的理當摒棄。
對于國家標準委組織公布的國家標準GB/T 20348—2006 中醫基礎理論術語等雙語標準,處理原則是,先參考國際標準,然后是國家標準,加以比較,在術語工作基本原則指導下,擇優選用。
中藥名、中成藥名須參考2010 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拉丁中藥名稱已經向國際藥典接軌,植物藥用藥部位后置,以便檢索。但其中成藥名稱用漢語拼音加劑型的方式,不為外國人接受。目前國際上傾向于用漢語拼音作為第一標準(建議拼音不要連寫,以方便外國人拼讀),后面應該附英譯名,以完整傳達方名、中成藥名信息。
五 中醫藥術語英譯的規范原則基本內容及順序
根據其重要性,7 條中醫藥名詞英譯規范原則的基本內容及順序是:
對應性:譯名詞義與中文相對應。這是最重要的原則,居諸原則之首。
系統性:保證中醫藥學科概念體系的完整性。
簡潔性:譯名要簡潔,不是辭典釋義,用詞不能太長。
同一性:同一概念的術語只用同一詞對譯。
回譯性:譯名結構在形式上與中文一致或相近。
民族性:定名時應考慮我國文化特色和中醫藥名詞特性,翻譯時盡量保留中醫文化特色。
約定俗成:目前已通行的譯名,與前述原則雖然不完全符合,仍可考慮采用。
以上諸原則,除了對應性為優先原則之外,其他原則的順序有時還需綜合考慮。
六 結論
中醫藥名詞的英譯關鍵在于對中文術語概念的準確把握,必要時需要對中文術語進行考證,準確把握術語的本體。一些專有名詞在原始出處可能找到它命名的原因。按照術語學的系統性工作原則,需要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建立完整的中醫藥概念體系,在術語之間建立關聯。中文術語間的系統性,決定英文術語的系統性。中文術語規范原則也是英文術語規范時應該遵循的。中醫藥名詞英文翻譯原則只是術語英文名規范原則的基礎之一,首先是對應性原則優先于其他原則,旨在達到等義的目的;系統性原則次之,建立概念術語之間的聯系,在選擇英文譯名時要顧及上位概念術語和下位概念術語之間的關系。其次,必須考慮翻譯的因素,回譯性原則雖然爭議較大,形式上的統一對于中英雙語雙向的學術交流也是非常有思義的。由于文化承載詞、專有名詞的大量存在,民族性是必須考慮的原則。雙譯法、多譯法的使用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重要方法之一。另外,專有名詞拉丁化將漢語拼音作為第一標準已經被國內外學者提到日程上來。
總之,中醫藥名詞英文名的規范原則高于英譯原則,綜合了術語學和中醫藥名詞的民族特點,對中醫藥名詞英譯的規范工作具有實際的指導作用。